故宫学院中国画研究院学者、《崔如琢评传》作者王旭谈陕西画坛(腾讯网)
 2020-03-19
2020-03-19

学者王旭说画史:谈长安画派、黄土画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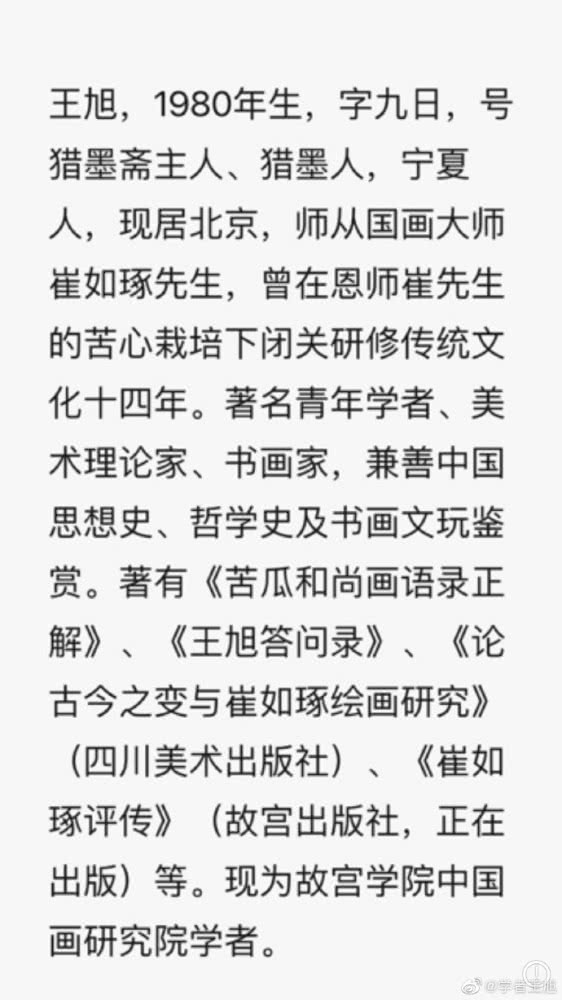
文脉与优势:
陕西是中国最具历史文化优势的省份,从西周至唐代,它拥有中华民族最辉煌、最骄傲的近3000年文明史。毫无疑问,中国人的精神价值、道德礼义、信仰习俗、生活美学、文艺情趣、家国情怀都由这里生成。所以,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都与陕西有关。
说起陕西画史,其成就虽不及诗歌、书法(唐代),但李思训、吴道子、韦偃、王维、张璪、王墨、阎立本、闫立德、韩干、韩晃、张萱、周昉、张彦远等足以堪称山水、人物、动物画之启蒙及人文精神之鼻祖。尤其至北宋关仝、李成、范宽、许道宁,陕西绘画走向巅峰,并随即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今天的江浙一带绘画。不过,北宋陕西绘画留给后世的冷峻高大、雄浑苍朴从面目上形成了派系-“北派”(董其昌提出),从内涵上形成了古朴的道释儒价值情趣,影响后世至今。尤其是“浙派”,经历了明代戴进、吴伟、蓝瑛,再到潘天寿,其绘画都有北宋陕西绘画遗韵。
事实上,陕西绘画影响中国画史不至于此,“南派”(董其昌提出)之董源、巨然,其青绿与水墨写意出自陕西画坛名家王维、王墨等。故,陕西绘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无处不在。说到此,董其昌之“南北派”之说很难自圆其说,如现代画家黄宾虹先生在其《古画微》里否定此说法。认为绘画不存在派系,源头上是一致的。
源头是什么?即上述提到的3000年文明史!
现状与劣势
北宋后陕西绘画失去了生机,用衰败一词并不为过,画坛主流形势一直被南方画家把持,直到20世纪,陕西画坛出现了两个画派: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这两个画派的殊途同归之处在于弘扬革命文艺精神,前者成立于二十世纪初期,笔法、态度中和,由赵望云及其弟子黄胄、石鲁等创立。后者成立于改革开放后,创立者主要以刘文西老先生及其弟子为主,画法、理念较为激进,乃至这个派系代表性画家在装束上都强调自己的“文艺战士”身份,在画风上强调自己的阶级文艺立场。
长安画派并非长安文脉,它的一大亮点恰是新中国绘画及新中国文艺的一道灵光,黄胄、石鲁既代表了长安画派的学术实力,又代表了新中国绘画的高度。自两位老先生去世后,这个画派宣告消亡!
 石鲁作品
石鲁作品
现在看来,黄胄在绘画内容上多体现的是新疆民俗,不属于陕西特质,但思想上实属“延安文艺”一脉。真正意义上,长安画派起始于赵望云,大成于石鲁,也终于石鲁。赵石二人又受五四文艺影响很重,画法传统折中现代,新中有古,不流俗于时弊。缺点是他们不擅长书法,加之他们英年早逝,留下了些许遗憾,要不,长安画派会带领新中国美术更向前一步!
20世纪新中国画坛有一个十分残酷的现象是极具代表性的画家多英年早逝,赵望云71岁,黄胄72岁、石鲁61岁,周思聪55岁,李老十只有39岁,而且是自杀。这不得不让人思考王国维(24岁)、老舍(61岁)、傅雷(58岁)等现代文人的现实处境、抑郁心理与后世的关系。大概,这是一个世纪的文化困境!
黄土画派与长安画派并没有多少关联,前者在文艺表达上,属于纯正的革命文艺,精神上践行了文艺为人民的服务主旨。一方面解说伟人意志、塑造伟人形象、宣传时代主体思想,一方面考虑了目不识丁群体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能力。如把西北最具民族风情、最具欢愉气息、革命宣传气息的“大秧歌儿”融入绘画,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让文艺走近了乡村基层,拉近了知识分子与老百姓的距离。总之,他们为新中国文艺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缺憾在于,兼顾世俗价值的同时,牺牲了个人的创作天性,忽视了文化之本体精神。事实上,大秧歌儿的“样板戏”风潮,让传统京剧以及本就奄奄一息的传统文艺或多或少失去了文化性。
 刘文西作品
刘文西作品
相比陕西文坛,黄土画派在固守价值、固守革命文艺初心时,有些与时代格格不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在歌颂时代、展望时代时发扬了现代文脉,有自己的文化思考、文化反思在里面。他们的进取心、叛逆性、书写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如对命运、生活、爱情、性爱的理解,是五四文脉的一大延续。事实上,这几个问题,是历代思想之变的主要问题,连同绘画皆如此,尤其人物画。比如陈老莲的、黄慎、任伯年的人物画(见我对这几家的评述)。而黄土画派缺乏诸如此类的人文思考,在身份上、精神上都没随时代转变。
与其说长安画派不善书法,那黄土画派在绘画作品中难见传统书写影子,尽管大小精微之刻画是其长处,但难掩文化缺失!当刘文西先生仙逝后,这个画派也名存实亡。因为刘老之后接旗之人暂不明朗。总而言之,陕西绘画如何续写传奇,创作更多的经典作品?留给当代陕西同道一个不小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