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散文将被写进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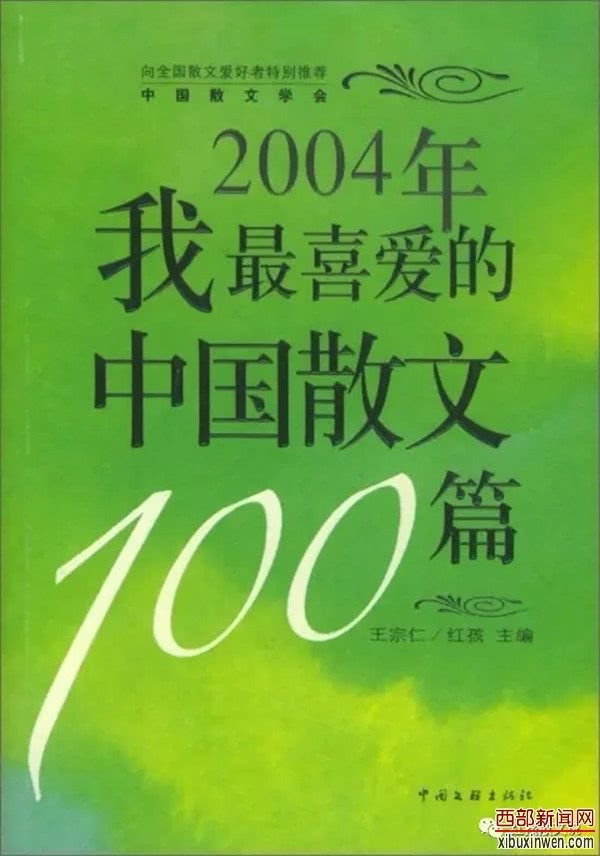
红孩谈散文之二
谁的散文将被写进历史
——《2004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序言
红孩
进入新世纪已经第五个年头了。大概离过去的世纪太近的缘故,人们在议论历史的时候,口头上还总爱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如何,那感觉仿佛故事就发生在昨天。或许是从多少个世纪以后考虑,现在的新闻出版规范中有个规定,即在50年代、60年代前一定要加上20世纪。否则,几千年过去了,谁知道你说的那个50年代、60年代是属于那个世纪的。
我很佩服现代人的史志意识。尽管很多人连同他们的作品非常速朽。最近,我有幸参加一本《中国当代散文史》的出版研讨活动。据我所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类似这样的史志性的散文书籍能有六七本,如果再加上”百年百篇”一类的选本,估计至少在十五六本以上。我总以为,大凡写史、编史之人,他们一定会有超人之处。细想之,有两点必须具备,一是勇气,二是智慧。所谓勇气,一要坚持客观性,二要坚持独立性。客观是对历史的客观,独立是自己人格的独立。智慧,是写作技术的选择问题,一是能充分调动自己资料的积累,包括感情和思想的积累,另一是怎样引领读者认识、接受你的问题。接受有两种,一是接受你所叙述的那个曾经发生的历史,再一个是接受你对那个过去的历史的态度。这就给人们提出两个问题,即:历史是否真实;写作者评价历史是否公正。
20世纪的白话文学无疑是绚丽多彩的。任何文学史家大书特书都不为过。总的来说,写现代史的较多,写当代史的较少。时下,给领导、名人、大款写传记、报告文学的很多,大多是歌功颂德、胡乱吹捧的东西。就散文而言,关于古代、现代的部分让人看上去还基本信服,当代的诸如“百年经典”“20世纪散文十大家”“建国五十年散文经典”一类的东西就很难令人服气,起码我不服气。因为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选家的个人意志,同时还兼有市场的操作问题。当然,不管怎样说,有人有组织能干这种事,总不是坏事,大不了可以做个参照物。
话又说回来,像搞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包括中国当代散文史研究,不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谁搞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你要写的对象,大部分还活着,有的甚至很活跃。特别是散文,近二十年更是热闹非凡,各种风格流派层出不穷。本来,评论作家作品的得失,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者最为正常的工作,然而,在文艺批评近乎失语的今天,谁要是发出一点独立的声音,很快就会遭到作家的不满。唯一的理解就是,当前的文学已经市场化,文学与市场、官场的接轨变得自然且密切,你一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人家的进步。多少年来,散文界的理论建设一直十分薄弱,其关键就是批评的声音太少(对余秋雨的批评倒是不少,只可惜大多与散文无关),相反,吹捧、造神之声却十分鼎盛。
看一部文学史,散文史,抑或是什么经典选本,一定要考虑编选之人的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此,我通常把批评史、文学史、选本看成是一个人的批评,一个人的排行榜,一个人的史记,也当然包括一个人的当代散文史。过去,就有人曾经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想来这话非常深刻。我在看一部文学史、散文史的时候,总要看看史家们的评述里有多少公共话语,有多少自己的语言。我以为,当下多出几本散文史,散文选本不是什么乱事,出得多了,不是权威没了,而是更丰富了人们的视野。本来谁也不是谁的权威嘛!
作为散文的创作者,能有作品入选“某某散文史”“某某散文经典”固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也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你入选的那个“典”充其量不过是某个人设置的,这个“典”能否成为“史”还有待于时间的淘洗。同样,作为一般的读者,散文爱好者,也应该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否则,你就不能客观准确地去把握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史。
本文的题目是——“谁的散文将被选进历史”,这话听起来挺庄严神圣的。其实你也不必就此被吓住。我在《2003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的序言《散文应该这样》中曾说,在语言平白朴素达美的前提下,散文无外乎有三种成分:第一,提供多少情感含量;第二,提供多少文化思考含量;第三,提供多少知识含量。今天,我把以上三点认识具体化,即散文创作可分三种类型:生活积累型、艺术感觉型和文化思考型。在此平台上,散文创作的题材越宽泛越好。不论是哪种类型,只要写好了,都不失为一篇好散文。只有好散文,才有可能被写进中国散文史。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将今年所编选的《2004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在题材的大致分类上,分为“美文之美”“苍生之情”等十个部分。为鼓励对散文形式的探索,我们还有意安排了一个“实验之坊”,希望读者能对此发表高见。
好了,这些毕竟都将属于过去的2004年。其个中甘苦,还是由每个人自己去品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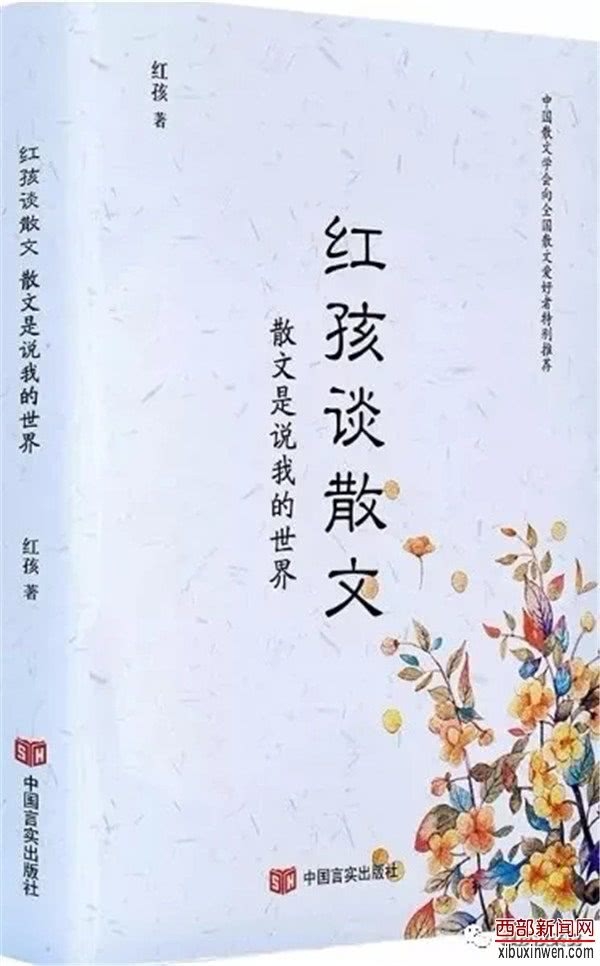
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他是散文的创作者、编辑者、研究者,也是散文活动的组织者、推介者、信息发布者,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你也可以了解到红孩对于散文的最新发声。红孩说: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