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马进:《龙泉司法档案》及其价值
 2020-05-27
2020-05-27

2019年8月27日,杭州召开了一次龙泉司法档案研读会。此次研读会由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组织。与大多数研读会不同的是,此次会上几乎只选择了记录有一件诉讼案件的档案,由20人左右的研究者花费一整天时间进行讨论。本文作者夫马进,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也是此次研读会的受邀人和发言人。会后,夫马教授撰文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的相关情况,并围绕这一具体案例展开讨论。文章原题《〈龙泉司法档案〉与龙泉司法档案研读会——围绕民国初年教育界与商业界弹劾警察案件的讨论》,发表于日本《东方学》第139辑,2020年1月。经授权,中译文首发于澎湃新闻,限于篇幅,对原文略有改动,并分作两篇,此为上篇。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全五辑)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一部可贵的史料集
首先想就原始资料《龙泉司法档案》以及基于原始资料而编辑出版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已于2019年出版完结),进行一些简单的说明。根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一辑 晚清时期》(包伟民主编,本辑主编吴铮强、杜正贞,中华书局,2012年)所载包伟民“《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总序”的说明,《龙泉司法档案》是由时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包伟民先生于2007年11月前往浙江省内的龙泉市档案馆时“发现”的。当然,直至当时为止,该档案一直由龙泉市档案馆收藏和管理,并且加上了编目可供公开阅览,所以才在“发现”上加了引号。不过正是由于此次“发现”,《龙泉司法档案》才在真正意义上为众所知,所以,毫无疑问可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
《龙泉司法档案》原来是由龙泉县法院所保管的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龙泉地方政府对其进行了全面接收,从而保存至今。《巴县档案》原本是由清代衙门保管的档案,所以覆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全部范围的案件,其中包含大量与内政、军政、教育等相关的行政文书。而与此不同,《龙泉司法档案》仅限于司法相关的档案,其中主要都是诉讼档案。这也是其被称为《龙泉司法档案》的原因。
《龙泉司法档案》的宝贵之处在于,除了一部分清末的档案外,其实际上是由自1912年(民国元年)开始,至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的档案构成。在目前所知的中国地方档案中,它是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最完备的一部地方档案。我们现在可以对《龙泉司法档案》进行不同领域的划分,活用于诸如法制史、社会史、地方政治史、文化史、生活史、女性史等研究领域中。而且在这各个领域的内部,可以详细地探讨在民国38年间的变迁。不过,在我看来,《龙泉司法档案》之所以是极宝贵的史料,是由于依据这一史料,研究者可以通过对龙泉县这一地区的探讨,窥视到中国整体的变动。同时,研究者也可以经由自己的眼睛通观整个民国史的变迁。并非北京和上海,而是在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县域中,可以对民国史进行定点观测。在我看来,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能抓住包含有时代之变化、停滞、或者后退的大势,特别是如何直接从资料中体会到时代的氛围。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中收录了在民国延续的38年中,在同一地区所发生的大量诉讼案件,最适合据此追寻时代的变迁。虽说龙泉县位于浙江省内陆的偏远地区,但是从各份档案中可以明晰地看到龙泉与温州、杭州、甚至上海之间,都有着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便是以上述《龙泉司法档案》为基础而编纂的史料集。首先,《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一辑 晚清时期》全二册,于2012年出版。其中收录了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档案中的全部案件,一共二十八件。由于这些诉讼案件持续到了民国初年,所以其中自然也包括民国时期的档案。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一辑 晚清时期》
其次出版的是《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二辑 1912-1927》(本辑主编傅俊,本辑编纂傅俊、吴铮强、杜正贞、陈明华、张志伟,中华书局,2014年)全四十册。此辑收录了180个案件。《第三辑 1928-1937》于2018年出版,全30册,收录了82个案件。《第四辑 1938—1945》全16册,收录39个案件,《第五辑 1946-1949》全四册,收录14个案件。后两辑都于2019年出版。至此,《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出版正式结束。
在民国时期的档案中应该选择怎样的案件进入《选编》呢?对于这一问题,据编者介绍,是考虑到案件的类型和诉讼过程的典型性,选择了档案保存状况完整、资料价值较高的案件。不过,对于地方档案的研究者而言,很有必要了解现存该档案的全貌。自然,对于编辑者的辛劳工作,我想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然而,如果未选择部分的案件没有经过整理的话,确实也会给档案利用带来困难。在《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工作中,由于完全没有记载其他还有怎样的案件,亦没有记载未收录案件的情况,所以在我个人看来还是稍有遗憾。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
《龙泉司法档案》研读会之缘起
这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关心中国史中的诉讼与社会问题,也收集和研读了好几种中国的地方档案。我从1992年开始研读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太湖厅档案(同治 光绪期)》(太湖理民府文件),其后对台湾大学藏《淡新档案》、南京博物院藏《太湖厅档案(嘉庆 咸丰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天府档案》、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乾隆 同治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徽州千年文书》等资料都进行了调查、收集和阅读。《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一辑 晚清时期》这册档案,是我于2012年出版之后直接购入且进行了粗略阅读。而对于《太湖厅档案(同治 光绪期)》与《巴县档案(乾隆 同治期)》,则是召集了10至20人左右的研究者,举行了轮读会。
以上所述的都是明清时代的地方档案,特别是记载了在县衙门,或者与之相当的初级衙门中诉讼裁判案件的档案。在写完了《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夫马进编《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中译本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之后,我自己希望开始阅读民国期的诉讼档案,而不再是清代的诉讼档案。因为我想知道诉讼和裁判的方式在清代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所以非常想了解其后的时代。或者说,因为我很想通过实际的民国档案来确证自己在清代档案中无法加以确证的推测。不过,我对于民国史研究完全是外行,甚至连哪些是基础的文献都不太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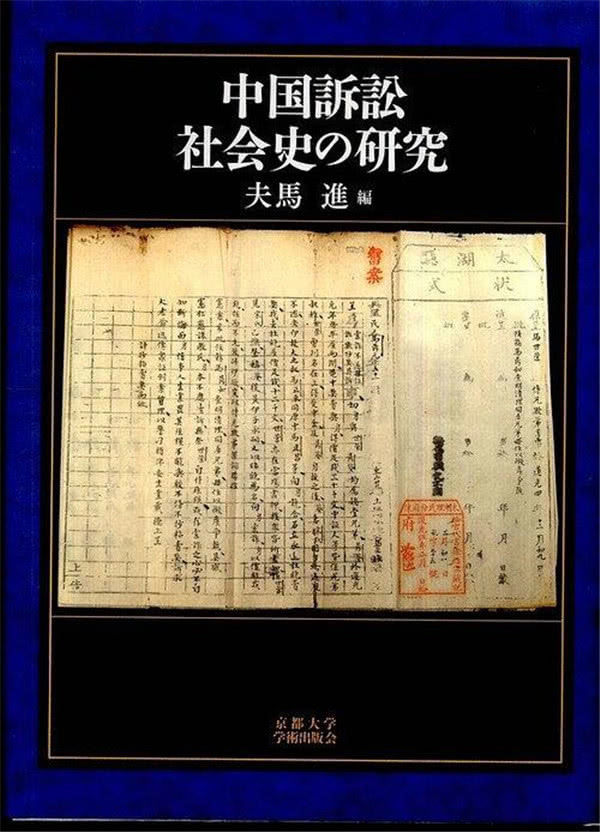
《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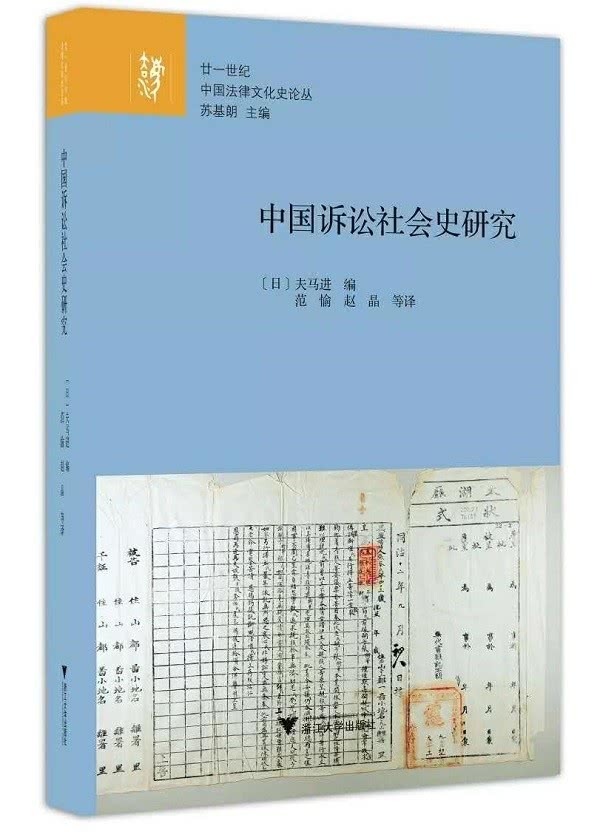
《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中译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我开始接触民国档案,即《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二辑 1912-1927》(2014,全44册),是到了退休之后的2016年。该年的三月份,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赵晶先生来到京都,我向他询问有没有便于阅读的民国时期诉讼档案,他向我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二辑 1912-1927》。幸运的是,京都大学法学部图书馆正好购买了该书。《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二辑 1912-1927》与《第一辑 晚清时期》相同,全书都是用上乘的纸张印刷,因此对于我这位老人而言非常沉重。高兴的是,凌鹏(当时京都大学研究科博士在读,现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看到我的窘状,自愿帮我复印了这些材料。
2016年8月份,我与伍跃(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两人开始阅读《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二辑 1912-1927》。由于伍跃也很关心《顺天府档案》中法律词讼问题,所以我们将这两个史料交叉着进行阅读。后来,凌鹏与铃木秀光(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也加入阅读。在凌鹏回北京之后,久保茉莉子(成蹊大学文学部助教)也加入了。
在我阅读《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二辑 1912-1927》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想去曾经的龙泉县(即现在龙泉市)的想法,而且特别想去后文提及的八都镇。我对于选编中所收的《民国二年 李兴唐等控卓识等纵警仇学案》(第二辑、第三册,500页-567页)与《民国三年 曾林裕控程作祺等诈欺取财案》(第七册,612页—686页)两案,以及李镜蓉这一人物很感兴趣。这两个案件,都是以八都镇为舞台,而李镜蓉正是当地的人物。同时,我也很想阅读在《龙泉县志》(龙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龙泉县历代修志纪略”中提到一次的《民国龙泉县新志稿》(1948年序)。我觉得其中可能会有对李镜蓉等人的记载。不过如前所述,我对于民国史完全是外行,对于《龙泉司法档案》也完全是外行。当时便想着去龙泉的途中一定要顺道去杭州拜访《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编纂者,因为有很多问题想向他们请教。

夫马进教授考察龙泉市李氏宗祠
我首先联系的是杜正贞先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不过可惜的是,在我预定前往杭州、龙泉旅行的八月下旬,她恰巧不在杭州。随后,又通过赵晶先生的介绍,与吴铮强先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取得了联络。吴铮强先生通过邮件询问我在龙泉的活动安排,我很直率地将我对于前述两案的兴趣,以及打算去八都的想法告诉了他。其后,吴铮强先生在回信中提到,如果可能的话能否就《龙泉司法档案》开一次小的工作坊,张小也先生(深圳大学教授)也会参加。随后吴先生又发出提案,首先由夫马率领参与者一同阅读档案,随后由数名参与者报告与这两个案件有关的小研究。我想,如果单单只是自己向别人请教,确实有点不好意思。而且想到,也许我自己所抱有的兴趣,也能够同年轻的中国研究者们分享。因此,我认为这无论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中国学界,都是一件好事,便同意了吴铮强先生的提案。吴铮强先生一开始只打算召集5、6人的研究者,但最终包括我与担任翻译的凌鹏在内一共19人,除了杭州的研究者外,从北京、上海、武汉、南京、镇江、深圳等处也有研究者赶来参加。
《龙泉司法档案》所见近代中国的诉讼
研读会上,首先是我以“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几个问题”为题进行报告,在一起阅读数段档案原文的同时,根据这些材料说明我的关心点是什么,以及从中能够读取出什么信息。档案的原文由凌鹏代读。其后的讨论,最终是围绕着我说明的诸个问题为主而交叉进行。在此,我想就我所关心一些内容进行若干详细说明。
自从我开始阅读《龙泉司法档案选编》1912年(民国元年)的案件,第一个感觉便是,像龙泉县如此偏僻的地方,也非常的健讼、好讼和缠讼。我认为在清代,县级层面的诉讼可以大致区分为巴县型和太湖厅型两类,而如果依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二辑》中收录的案件进行判断,可以说民国初年的龙泉县属于巴县型。

研读会现场照片
在龙泉的诉状中,依然可以看到将诉讼的对手称做“讼棍”的夸张的污蔑表达,而在辩明自己并没有健讼、好讼、缠讼这一点上,也与清代相同。根据我的推测,书写这些诉状的人,大部分应该就是在清代被称为“讼师”、“讼棍”的人物。
在民国,手持召唤状(信票)前往召唤的警察,被称为“司法警察”,略称为“法警”。不过,如果看到前往召唤时所携带的信票,会发现其中写有“司法警察某”,“某”即携带者本人的名字。这与前清时期的信票上写有“总役某”“差役某”的样式完全相同。可以说最合理的推测是,曾经的差役就照原样平移成为了司法警察。说到司法警察,虽然名称听起来很不错,也不知道在民国初年是不是会穿制服,但大概可以将其实际情况看做是差役吧。简单而言,只是将清代的差役改称作司法警察而已。
这样,一方面可以看到,民国初年的诉讼与裁判的形式,很可能大部分是从清代继承而来的。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在档案中展现出来的“新”现象。第一,在诉状中点缀着新的用语。可见在这样偏远的地方,很可能也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影响。在民国元年提出的诉状中,已经使用了“野蛮手段”、“此新政之所必惩”、“私有产业”、“农夫生活”、“自由主义”等词语。此外,可能是认为使用“法律”二字对自己有利,所以到处都可看到这两个字。虽然旧表达的数量依然很多,但是到了民国二年、三年,新词汇的使用貌似更获得了显著进展。如果假定这些诉状是由过去的“讼师”“讼棍”写成的话,大概他们当时正在急速地学习新的诉讼用语和司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