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罗新对谈《失落的卫星》:旅行的目的是遇见人

2010年,作家刘子超站在霍尔果斯口岸,眼前是通往中亚的卡车队列,以及远方壮阔的天山,他不禁想: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天山底下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为了探访我们神秘的邻居,刘子超在九年里数次深入亚洲腹地,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展开一场寻觅之旅,写就了中亚游记《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的旅程》。
 刘子超携新书《失落的卫星》与罗新对谈
刘子超携新书《失落的卫星》与罗新对谈7月17日晚上8点,刘子超携其新书《失落的卫星》做客单向空间,与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罗新畅谈,分享各自深入亚洲腹地的旅程。作为资深的旅行爱好者和写作者,两人谈论了各自对旅行和旅行文学的想法,分享旅行的意义和写作的秘密,讲述旅行何以成为一种诱惑,一种生活,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刘子超学习了俄语、乌兹别克语,在九年间去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
刘子超学习了俄语、乌兹别克语,在九年间去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深入失落大陆,寻找被遗忘的声音
在去中亚前,刘子超读过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写的纪行,历史课上也学过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之地等相关历史知识,那些充满想象的地名,从此在心中生根。同样的浪漫,也体现在罗新教授身上。当被问到为何着迷于中亚时,罗新将其分为两方面,一是跟学术有关,二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读大量苏俄文学,尤其是像艾特玛托夫等名家的作品,在心中培养了对中亚的浪漫想象。
这种浪漫在旅行中逐渐变成更为复杂的感受。2011年,刘子超第一次抵达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他在首都塔什干看不同的人种,面对着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中亚之旅伴随着震撼,但回到家后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为了真正了解这个神秘的邻居,刘子超学习了俄语、乌兹别克语,在九年间去到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沿着国境线飞驰,绕过散落的飞地,驰骋于帕米尔无人区,在苏联的核爆试验场抛锚,他以探险者的精神见证隔绝之地;踏上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徜徉于血腥战场和帝国宫殿,凝视最古老的圣书,抚摸玄奘笔下的佛塔,他试图寻回古人的目光。
一路上,刘子超还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收集了大量中亚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在塔吉克斯坦,他结识了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青年,聆听他为何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他遇见被流放至此的朝鲜人后裔,他们不再会说母语,卖着已经变味的泡菜;在干枯的咸海边,他遇见困守咸海七年的中国人,聆听活在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的感受;在乌兹别克的酒吧里,他听见把酒言欢的商人指着撒向空中的钞票大喊:“你之前看到的全是假象,这才是现实!”
在这片处于全球化边缘和大国夹缝间的土地,一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寻觅之旅就此展开,一个个徘徊在希冀与失意、自由与迷失之间的沉默者浮出水面。这片失落大陆的被遗忘的声音,就被记录在《失落的卫星》一书里。
 刘子超笔下的中亚故事获评全球真实故事奖
刘子超笔下的中亚故事获评全球真实故事奖获评全球真实故事奖,为中国旅行写作树立标杆
在正式出版前,刘子超笔下的中亚故事就已经颇受关注,个别篇幅在媒体刊登后不仅迎来读者的青睐,也为受到国内名家、媒体乃至国际大奖的高度赞许。
2018年,经评委西川、陈嘉映、董国强、姚晨、许知远、阿乙筛选,刘子超便从近500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单向街公益基金会“水手计划”的五位入围创作者之一。
作家许知远盛赞刘子超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则认为,在近代中亚游记中,《失落的卫星》是第一部高质量的原创中文作品,“为今后的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
在当晚的沙龙中,罗新也谈及自己初读《失落的卫星》的感受,表示自己非常吃惊,想不到中国人会写出这样的旅行文学作品。罗新教授指出,中国人外出看世界的现象在以往并不多见,但到了今天,哪怕再偏僻、再困难的地方都有中国人,年轻人发表的旅行记录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新的、好的形势,《失落的卫星》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刘子超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越来越多中国商人凭着悟性和开拓精神出海,中国作家也开始有机会和能力用中国人的视角打量世界。
早在2019年,经评委梁鸿、李海鹏、吴琦推荐,《失落的卫星》中的乌兹别克篇章便入围了由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的“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这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甄选、由29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参与的非虚构特稿大奖。最终,刘子超的作品评获该奖的特别关注作品。
《纽约客》资深记者Jon Lee Anderson称赞其富含“简洁、直接的散文风格,以及独特的幽默感、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全球真实故事奖”评委Margrit Sprecher则认为,读完刘子超的作品,“你对这片土地的了解比读一百篇政治类文章还要多”。
 罗新教授指出,正是在偏见泛滥的年代,旅行的意义才更为重要。
罗新教授指出,正是在偏见泛滥的年代,旅行的意义才更为重要。在疫情时代,旅行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失落的卫星》之前,刘子超曾出版两本游记,游历过欧亚多个地方,从一个全职的媒体记者转变为专门旅行、写作的自由人,2016年后决定深入中亚,为这片土地写一本书。罗新教授也曾数次抵达欧洲、中亚等地做研究、考察及学术交流,除了长期关注中国之外的土地,常年坚持长距离行走,并创作出《从大都到上都》这样的行走游记。对于两人来说,旅行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刘子超认为,旅行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自己去实践、去行走、去发现。对此,刘子超借用“新游牧”(Modern Nomad)的说法:“游牧者是有方向的,比如从夏牧场到冬牧场,而不是漫无目的。他的随身物品很少,经过断舍离后,没法带上路的东西就不要了。我现在正是这个状态,在生活中做减法,断舍离后带上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做有目的的旅行。”
罗新则认为,旅行是接触到全新的世界,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看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在跟生活在异地的他人深入接触之后,才能发现他们跟我们是差不多一样的人。这种确认就是写作的过程、旅行的过程。在今天,在这个时代,这种确认很宝贵。
在西方,旅行文学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早在十九、二十世纪,欧洲就涌现大量游记作家。这种对中国读者来说还算新颖的文体,涉及许多历史和文化知识,那么在这两位资深读者看来,什么才算好的旅行文学作品呢?
刘子超认为,好的旅行文学应该充满人的故事,比如奈保尔写的《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奈保尔曾说自己想让这本书充满人的故事——呈现出一个地方的人心,就是旅行文学到达最好水平的一个标志。
对此,罗新教授表示认同:“凡是好的、成功的旅行文学大概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写了大量的人。” 他认为,刘子超不同于普通游客,而是带着一种真正旅行者的视角,“他是去街巷跟人接触,记录真实的人的故事,这是西方旅行文学非常优秀的传统。”
刘子超也认为,在这本书里,旅行慢慢变成一种方法。旅行退后了,人浮现出来了。旅行目的就是遇见人,寻找具有某种时代感的故事。这本书是一个尝试,是一个努力去找人的过程。
在不便出门的疫情时代,旅行似乎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一本游记的出版更像是一种逆向行为。对此,罗新教授指出,正是在偏见泛滥的年代,旅行的意义才更为重要,正如马克·吐温所说:“旅行是偏见的天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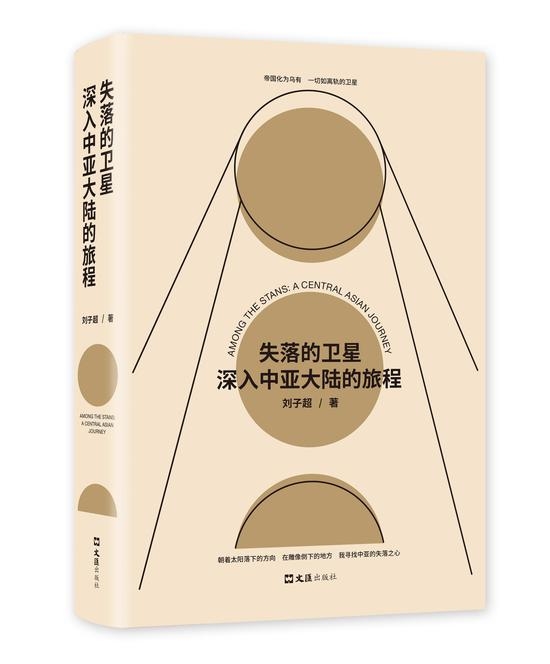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刘子超 著 文汇出版社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刘子超 著 文汇出版社曾经庞大的帝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踏上未知废墟,如游牧者般寻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