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书评|叶梓《陇味儿》:所有的木耳,都是他倾听故乡的心跳
 2020-10-24
2020-10-24

一想到甘肃,你脑海里跳出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兰州拉面?油炒粉?黄焖羊肉?
娜夜有一首著名的诗《想兰州》:想我们年轻时的酒量 热血 高原之上/那被时间之光擦亮的 庄重的欢乐……入城的羊群/低矮的灯火/那颗让我写出了生活的黑糖球……
酒,羊群,灯火,黑糖球,还有一群甘肃诗人,构成了她诗中的甘肃画面。
甘肃作家叶梓,远离故乡多年,在江苏苏州发展,他念念不忘的甘肃画面,则是由一道道陇味儿美食组成的。
周末读什么好书?今日红星新闻《红星书评》推荐叶梓和他的美食之书《陇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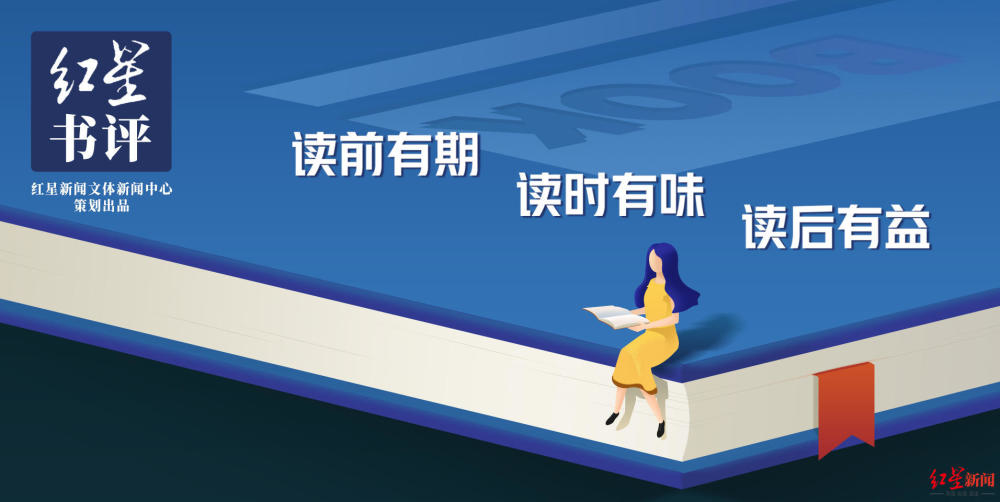
纸上返乡:以美食的方式抵达
◎杜怀超
叶梓的美食之书《陇味儿》,不只是一本文化美食之书。正如他在前言中写道,这是一本“怀乡之作”,是居于南方的他“一次纸上返乡”,是他一个人的“追忆逝水年华”。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有故乡天水的风情风俗,有他的故交亲朋与芸芸众生,有他异乡天空下或悲或喜的记忆,也有他生命里“无处安放的那抹乡愁”。
写美食:是一个游子抵达故乡的最佳路径
写美食,是一个游子抵达故乡的最佳方式。故乡,活在异乡人的胃里。作家叶梓的美食,与其他写美食的作家有着一定的异质性,不是宽泛地介绍美食,从食材到做法,再到色香味,按照内在逻辑,层层剥开或者深藏,完成文本。在他的美食之味里,凝结着入骨的乡情。
他这样介绍康县的木耳:“康县木耳,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吃厌过。康县的木耳,依其种类,通常有“毛木耳”和“光木耳”之分——背面密披白绒毛者,曰“毛木耳”;两面光滑干爽者,曰“光木耳”。木耳在当地的别名也有很多,生于腐木之上,形似人耳,名“木耳”;丛生于椴木上,如蛾蝶玉立,又名“木蛾”;重瓣如浮云,镶嵌于树上,则又称“云耳”。(《康县的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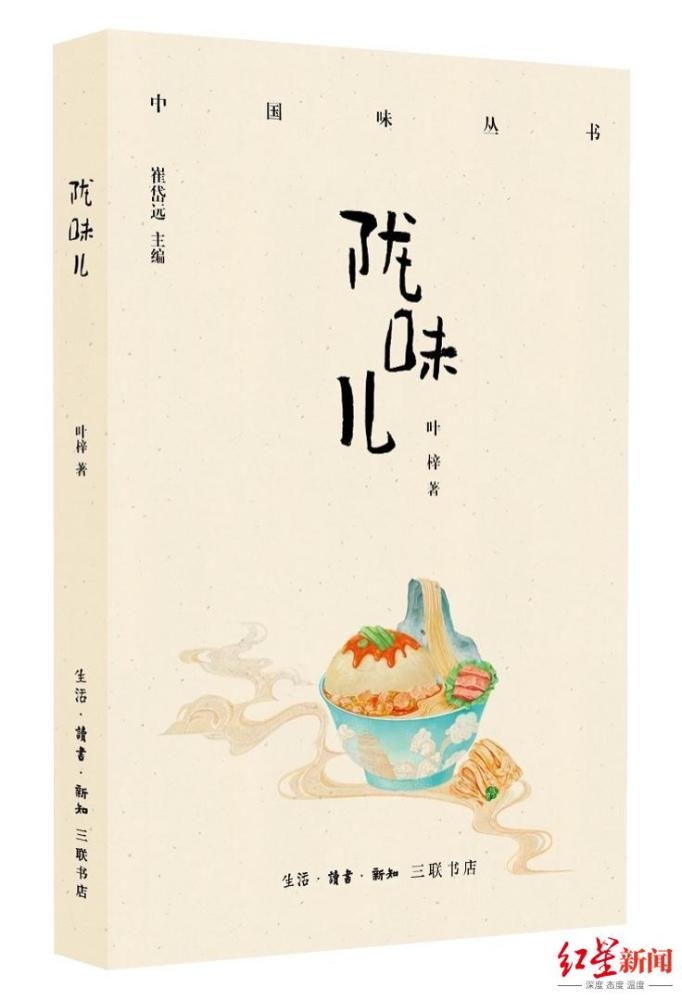
开头一句,一下子就把属于文人的情怀呈现出来,没有吃厌的,不仅指的是木耳,也是那思不够恋不够想不够的故乡。再远游的人,心上始终站在故乡的模样。这只“木耳”,就是作家谛听故乡一草一木、亲朋好友的天线。季节的风声、人事的沧桑全部收拢于耳畔。
尤其传神的是,从木耳到木蛾,再到云耳,这三者之间极其形象洗练的描绘,工整俨然的句式,道尽木耳的风流和高光。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出于对老家甘肃大地的深情,怎么会把木耳写得如此细腻?举重若轻的字词,如重瓣如浮云,在我看来,那浮云的背后,是西部故园高低婉转的唤归声。人在江南水乡,心随着木耳早已抵达故乡的枕畔。
我以为,所有的木耳,都是作家倾听故乡的心跳。
写性情:文化美食之外的又一道追光
当下文坛,写吃的文章者众多,但要写出个性,写出作家的自我,则寥若星辰。就美食写美食,是庸常之作。如果能从美食之中,读到文化,读到作家自己,读到诗意的生活,读到精神层面的东西,美食就走进了纵深,走出一片广阔的世界。
叶梓的许多篇什中,随处可见这样的高光。例如《浆水面》一文,吃浆水面成为在外游子的情结,正如叶梓在文中呼之、爆发的那句“真想吃一碗浆水面”。浆水面,不再是一碗面,而是思念的堆积,乡愁的象征以及回家的企盼。也许,回家后,吃到肚子里的,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浆水面,也不是自己魂牵梦绕的浆水面。真正的浆水面,永远留在美好的记忆里。
令人震撼的是,天水的浆水面,竟然与一个人的自我救赎有关。一个犯事的人,想吃一碗家乡的浆水面,“两碗下肚,可能是觉着心满意足的缘故吧,一下子就把犯事的过程和盘托出……”警察不解,问他为什么能如此坦荡、心情愉悦?那人的理由竟然如此不可思议:“一碗浆水面,吃得人心里舒坦啊。”浪子回头,一碗浆水面,完成了他对自己的拯救。这里面,功劳属于浆水面,也是食文化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深深积淀。这碗浆水面,已经走到人的精神层面。
写地域:江南水榭里雄浑的华章
在外行走多年后,叶梓落脚江南。江南之秀丽,与西北之雄浑,两者走到一起,山水相连,是婉约与豪放的最佳搭档,大漠、驼铃还有塞外,与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有机组合,打开我们七彩世界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在作家的笔下,我们看到了美食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在美食的内外,是人文、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呈现和表达。

作家叶梓
关于天水小吃《麻食》的细腻抒写:“一位衣着朴素的妇人,将和好的面揉得光光的,复又搓成细细的长条,再掐成一小截一小截,拿起,在一个新新的草帽檐檐上,用大拇指使劲一搓,一个长短约一厘米、带有草编花纹的海螺状的小面卷,就脱手而出……”
西北的美食,一旦走进江南的胃,其中不只是属于西北的辽远和无垠,还有一部分属于江南水乡的柔情。定居于江南的叶梓写道:“麻食的风行天水,让我看到了深藏于这方大地上人心里的温婉与灵秀……西北人吹着呼呼风沙的心里,也有着小桥流水般的温婉与灵秀。”
在这本书里,我更愿意读到叶梓关乎西北风情的、带着沧桑的表达,如他在写《凉州“三套车”》时,把武威的三套车小吃,当作是“西出阳关无故人啊,请珍重加衣,请吃饱穿暖。”这一暖色调的句子。站在阳关烽火台上,面对着远处无尽的苍茫,眼前浮现的一定是这样的词汇:河西走廊、壮士、葡萄美酒、夜光杯、沙场和莫高窟……
写卑微:对美食之物的体恤与悲悯
美食需要细品,叶梓的美食之文,同样需要逐字逐句地体会。文学大家汪曾祺老先生,在北京寓所吃到从家乡捎来的江南“慈姑”时,眼角潮湿。他说,慈姑性苦,但却是有“格”的。一个“格”字,令慈姑的境界丝毫毕现。
这种“格”,我在叶梓的《苜蓿面》中同样读到。“苜蓿,是西北大地极普通的一种草。在西北,却是穷人的草,贫寒人家拿它做菜。儿时的我经常吃。”普通的草,总是与穷人捆绑在一起。这些大地上的美食,早就成为我们胃里的常客,不管时空如何变化,那种刻骨铭心的温暖与烙印,始终不会变色。
吃过了江南金菜花、草头的叶梓,他说如果在遥远的大西北,吃到一碗苜蓿面,像一首苍凉的边塞诗。我以为,吃这种面,必须要在河西走廊一带,或者“泾川的窑洞里”:“这是一户贫寒人家,很多人早都搬离了窑洞,他们家却没有。男主人膝下有三个小孩,两男一女。说起梦想,男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让他们以后读点书,离开这窑洞,在大城市里落下脚,哪怕扫马路也行。”
有人说过,每道美食的后面,都站着一个“佛”。苜蓿面,对这一家来说,就是他们的佛。同样也是作家叶梓的佛,“我是乡村长大的孩子,懂得他们的苦。”这里已经不只是共情,而是上升到对吃苜蓿面人的未来与命运的关注。书中的叶梓沉默不语,一边吃苜蓿面,一边望着窑洞外面连绵的沟壑。黄土塬上星星点点的窑洞里,一定居住着一位我们永远看不到的神,他教会人类学会一个词:隐忍。
一卷《陇味儿》,美味无穷。叶梓说,这些文字,是他的一次纸上返乡之旅,是对家乡风土人情与日常生活的真诚记录,以游子心态对甘肃大地的一次深情回望。而我则以为,这本书,更是现居江南的他在小酒微醺之际,一个人在书桌前的望乡,或是在睡梦中的呓语。
此时,杯盘狼藉,我已深醉其中,不能自语。
(作者系江苏省徐州市文学院专业作家 )
【作家简介】
叶梓,本名王玉国,甘肃天水人。中国作协会员。近年来创作的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中国作家》《散文》《山花》《美文》等重要文学期刊。获甘肃黄河文学奖、孙犁散文奖、鲁藜诗歌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文学奖项若干。出版有诗集《馈赠》,散文集《穿过》、《流浪的诗圣》《天水八拍》《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等9部,现供职于苏州市吴中区文化馆,从事专业创作。
编辑 乔雪阳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