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丨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苏东坡的通俗故事
 2020-11-10
2020-11-10

本文作者:半岛都市报记者 刘宜庆
天才如何利用时间是一个谜。五十卷的《张炜文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堪称煌煌巨制,这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一个精神的高原,更是文学创作的一座高峰。从有限人生创造无限的可能。张炜之于我们这个时代,是思想的标杆,是文学的纯粹。
近年来,张炜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一个诗学专著系列,解读历史上伟大的诗人,赏析永恒的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解读苏轼的诗学专著《斑斓志》,本报记者专访张炜先生,请他谈一谈创作的历程,苏轼带给今人怎样的人生智慧。张炜透露,他一直坚持在方格稿子上笔耕不辍。拂去灰尘一样的喧嚣,走进诗人苏轼的精神世界,走进作家张炜的文学版图。

关于《斑斓志》
一场热烈的讲授形成了文字,需要冷却的时刻
记者:您的诗学专著已经出版了《也说李白和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以及今年夏天出版的解读苏轼的这部《斑斓志》,您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诗学专著的创作?
张炜: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在最能阅读的时候,读了大量翻译作品。特别是小说作者,就尤其是如此。将世界文学的窗口打得更开,直到现在来说仍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当一个写作者认识到民族文学的源头力量以及这种迫切需要时,一般都是年过四十以后。这几十年里我一直在为自己补课,虽然自小就读过一些传统经典,但真正深入下去,能够系统地读,还要静下心来,拿出大量的时间。
因为这些年要在书院和一些大学里讲课,所以谈古诗人比较多。这是个好好学习和讨论的过程。我选择这些内容主要还不是因为讲课的需要,而是读的古诗多了,体会多了,有话想说。这是阅读古典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单纯的“备课”式的阅读,在我这里是不多的。我沉浸在中国传统经典中的时间越来越多,心里的感慨不由自主地就积累了许多。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写作,尤其是诗的写作。
记者:去年夏天,在鲁东大学贝壳儿童文学周,我有幸听您的讲座,近距离感受您演讲的风采:才情如大地喷泉,喷薄而出,妙语连珠汇成江河,汪洋恣肆。让我想起古代高僧讲佛法,顽石点头。我看后记介绍,这本《斑斓志》是根据您讲苏轼的系列讲座而成,从讲座的语言,到书稿文本,这样的转换是否会把讲座的现场感丢失?在转换为书稿文本时,增加了什么内容?
张炜:现场讲出的内容,特别是进入讨论之后的思想焕发,是安静的个人工作中难以出现的。但一场热烈的讲授形成了文字,还要有一个冷却的时刻。在讲的时候或者会遗漏一些重要的东西,少了点严密的学术性,甚至是表述的错误。如篇章中的一些细部勾连、一些更准确的表述,都要好好斟酌一番。有些引用的诗句,也要在后来找好的版本加以确定和补充。
人在讨论中,在深入的言说中,思维容易被激活,所以落到文字上往往是活泼和外向的。书面阅读的要求则有些不同,其特征恰好是要有更多的内向性,是细细地贴紧文本咀嚼。文本一旦喧哗了是不好的,这和现场听讲互动的效果有所区别。所以有时候现场效果极好,落实到文字上反而不好,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演讲稿、讲课稿,一旦形成电子稿放到案头上,就要将其当成一本书一篇文章,以这种心态去对待它要求它。要好好研究自己在热情交流时,在面对一场听众时,都说了些什么、怎样说的。即便如此,口中吐出的文字和一支笔写下的文字,气息还是大有不同。二者的长处结合起来是最好的。我不知自己做到了没有。
我察觉到,自己尽管在讲授时并没有居高临下,而是平等探讨,但这时的口气和伏案工作时仍旧不同。教导他人的姿态会排拒读者,这也是事后检查文字时应该注意的。让听者的热情感染自己,这是极大的帮助。没有热情的听众,或者他们精神涣散,一场讲授将没有深度和神采。但订正录音稿时,却要尽可能地冷静,旁若无人。

记者:每一讲中的小标题,都很吸引人,具有文学的趣味,是诗意的表达。这些小标题就是全书的脉络,是您妙手偶得、灵光一现的产物,还是深思熟虑、仔细斟酌出来的?
张炜:成文之因只是讲下去,围绕一个方面,讲清楚了再移向另一个方面。平时阅读经典也会有些手记。读和讲、最后订正,都有可能拟出标题,它们的作用是条理化,将漫开的思绪归拢起来。这就使讲述能够层层推进,并呈现出这种层次感。它们之间似乎是分离的,实际上却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有感性和理性的逻辑。这些标题携手一起,合成了一种内在的推动力。
如果不是因为表达对象的复杂难言,尽可能不要意象式的标题去统领。标题实一些更好,贴切,具体,突破了平均化和概念化的习见,就会显出诗与人的本来面目。诗学研究面对的任务,主要是进入诗的内部,而不仅是外部的考证和索隐。当然这也是必须的,是基础。不过在这方面用力太猛,就会出现过度诠释的问题。审美诗学,这在研究中始终应该是个大方向。但是做好这个工作需要的条件比较多,因为远不是资料的分捡归拢就可以办到的。
关于苏东坡
这个生命太有趣了,全部文字都通向了他这个人
记者:《斑斓志》全书分为七讲一百二十余题,每题都有洞见和卓识,比如,在谈到乌台诗案时,您认为正是它的炼狱之火成就了诗人:“这一场文字狱、一场旷世冤案之后,这位天才人物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在这里,他攀上了诗与思的最高处,那是穷尽一生才能达到的高度。”我感觉您解读苏轼,调动了您的生命阅历和体验,站在人性的高峰,观照苏东坡,更加懂他了?
张炜:有关苏轼的文字太多了。现当代这方面的文字,从林语堂的那本传记出来以后,苏东坡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他,包括学术上的大致走向,也就在某个层面上形成了。苏东坡作为一个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是相当固化的。当然,许多出色的苏东坡研究也出现了。我不是,也不想写一部苏东坡的传记文字,更不是写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文字。一个当代写作者对一个古代写作者的全面接触,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及其他,都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读作品最终还是读人,苏东坡的全部文字都通向了他这个人。就文学来讲,古人的写作和今天有许多相同与不同。相同的地方很多,比如诗意的生发和表达,手与心的距离,生活与想象的关系,词语的使用调度,都有写作学的基本规律存在。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好谈了。但时代环境变了,表达形式变了,现代主义诗学的观照下,视角也将有改变。抽离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因素,也就走向了另一种刻板和肤浅。这是我必须理解的。事实上,关于苏东坡的文字再多,也会发现留给后来者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诗学和写作学方面,思想方面,现代价值观与儒学证伪、传统仕人的兼独道路,等等。我们不能过于满足苏东坡的一些通俗故事,其实他的真实面目,诗与思的面目,却常常被这些东西所遮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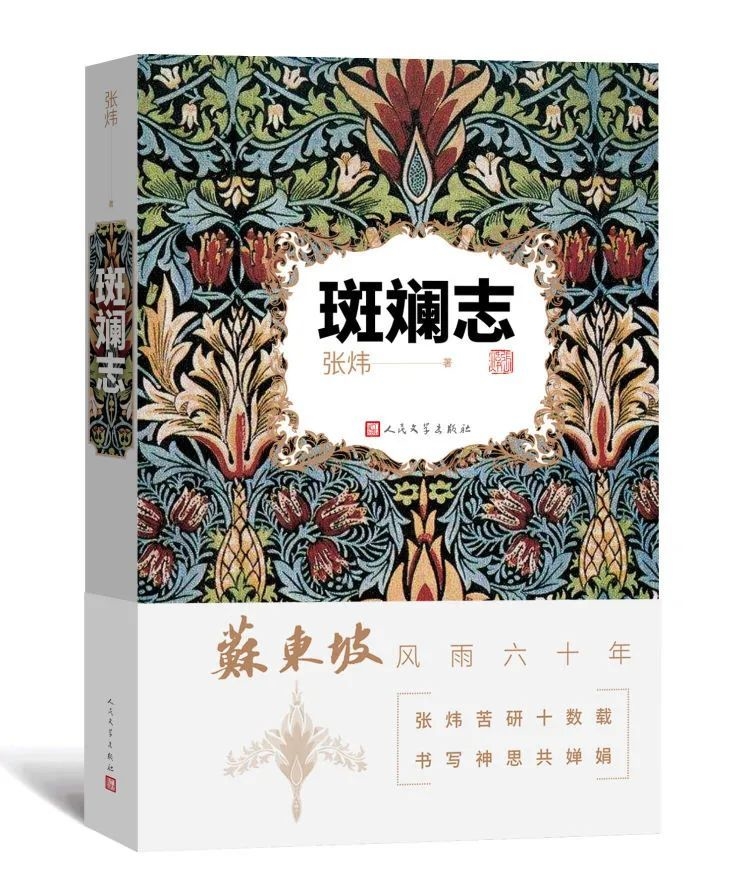
张炜《斑斓志》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记者:《斑斓志》不仅打通古今,也有中西文化视野的关照。一本书,熔铸诗学、写作学、文学批评、作品鉴赏、历史钩沉等,呈现斑斓之美。您给读者介绍一下好吗,为什么起名《斑斓志》,是象征苏轼的渊博吗?
张炜:这是其中一章的题目而已。“斑斓”这个比喻其实很直接,因为苏东坡的人生,比其他诗人更加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特征。他和一般人的确是大不一样的。看看他一生做下的事情、达到的水准、踏入的方向,都会有这样的感叹。这个人太丰富太有趣了,绝不贫瘠。有的诗人或艺术家,或生活中的其他人,也很专注很深入,但就多彩多姿这一点来说,还远不足以使用“斑斓”二字。有人可能觉得这个词用到其他人身上也勉强可以;不,用到苏东坡身上才最为贴切。如果强化这种感受,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阅读苏东坡,读他所有的文字。千万不要止于有人连缀给我们的那些通俗故事,它们看起来生动,其实有许多是表面化概念化的,而且不求甚解。真实的生活与人性,更有苏东坡这样的特异人物,并不是那样的夸张趣味。他是深邃难言的“平易”,是一桩“个案”。有人以自己的理想和志趣来解释苏东坡,好像也不对榫。有一些通常的做法,就是利用古人写出自己,这是不太好的习惯。
记者:苏轼通达于儒释道,纵浪大化,他的生命智慧对于今人有什么启示?
张炜:他一生恪守儒学,对释和道既不特别深入,也不信服。他只是像对待学问和知识一样去关注它们,只有那样的兴趣,但并不作为信仰。他对佛和道这两界中的朋友来往不少,友谊深厚,那是因为觉得他们有色彩有格调。他对所有个性人物都很好奇很亲近,而佛道二界中有一些人疏离于生活,往往更独立更有真趣。他和他们的友谊、与佛道原理的接近,都是这样的意义。在唐代,白居易兼收并蓄儒释道,韩愈则不然,后者与释和道界的人物都有交往,但一生都是一个坚拒佛道的人。苏东坡和韩愈差不多。苏东坡因为坚守儒家的入世精神,并不轻信佛道,所以坎坷很多,一生有这么多劫难。说到底,这是由他的儒家世界观决定的:兼治和独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较其他人,如白居易,吃了亏则能通融,然后儒释道并用,所以后半生就顺利了许多。苏东坡作为一个古代大政治家和文学家,强烈的入世治世责任,对真理的追求,对劳民的关切,是最让人感动的方面。
关于创作
我在方格稿纸上写作,反复修改
记者:您在演讲中说过,天才们怎样使用时间是一个谜。去年在万松浦书院参观,走进您的书房,看到书橱里陈列的一排一排您的著作,了解这句话的涵义。同时也很好奇,您是怎样支配时间的?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写作,他认为在早晨才能使人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福楼拜夜里通宵写作,书房里不眠的灯,甚至成为塞纳河上船夫的航标。巴尔扎克写作时喝咖啡;海明威用一只脚站着写。您在什么时间段写作,有没有什么写作习惯?
张炜:我如果有写作的冲动,就会在白天写三个小时左右。晚上不写。写的时间太长了不行,思维的力度和新鲜感都会降低。平时占最多时间的是阅读。读书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尤其是现在。要拂去灰尘一样的喧嚣。我不太看网络荧屏上的东西,它们耗人且得不偿失。写作当然要依赖冲动,没有冲动而写是没有必要的。
我发现国内外从古到今,非专业写作者写得更好。这是因为他们保证了创造动机的纯粹性。我学习他们,尽量找一些日常的职业化的工作去做,有了写作欲望才闭门造车。在电子传播时代,纸质书变得更加可爱了。它们印得越是讲究,就越是可爱。贮存许多好书,这是一种梦想的高尚生活。一部分人的梦想,就是过高尚的生活。有人从小追求这种生活。但到现在为止,我的存书还是不够多。平庸的书太多,不能存。设法存很多好书,这是非常困难的。就因为好书不像想象的那么多,所以任何人要过上一种高尚的生活,并不容易。我在方格稿纸上写作,反复修改,如果改得太乱就抄清再改,一般要经历四五遍。最后再变成电子稿,保存和邮寄就方便了。

记者:郭沫若著有《李白与杜甫》,林语堂著有《苏东坡传》,称得上才情与学识兼具的经典。您的诗学专著中有《也说李白和杜甫》,也有解读苏轼的这本《斑斓志》,在写作上,是不是可以看作超越前贤的尝试?
张炜:每个写作者都会有自己的局限,如果在学习中看到了他人的局限,既要谅解,也要在工作中避免。这样,写出的文字才会谦虚诚恳,会有意义。通过努力学习,找出自己的不足,这就是谦虚;也正因为谦虚才能有所发现。没有发现就没有事业上的递进,工作是无意义的。这只是一种认识,要做到并不容易。当我发现他人因为过分的社会性和现实性,或者因为努力写出自己,甚至为了追求小说的通俗性和生动性,为这诸种原因造成了偏颇和失误时,就变得十分谨慎了。
我不是为了和前人不同才要出版这些新著,而是想写出贴近诗人的著作。我的局限也会被他人发现,那时候他们的工作就有了自己的意义。有一颗平静朴实的心,才能从事研究的学术的工作,因为一使性子,事情就会办砸。写作者要经受许多诱惑,战胜它们并非易事。因为求真和深入而沉迷到一个世界里,不在乎世俗的脸色和口味,既困难,又是起码的工作态度。比如苏东坡,哪里仅仅是什么有趣和好玩?又哪里仅仅是什么有才和乐天派?他经历的爱欲洗礼,他在苦海里的浸泡,他的韧顽和软弱,我们作为读者还需做好全面接受的准备。
记者:您近年的文学创作,是不是偏重于儿童文学和诗学专著?
张炜:我一直在写儿童文学,基本上没有停止。古典文学特别是诗学,也一直在学习和探究。各个阶段的计划安排会有不同,做完一些计划,再着手干别的。总之,写作仍旧是有无冲动的问题,这种劳动需要冲动,有了冲动才会做好。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会在某个时候写诗、小说或散文,或与爱好者一起讨论问题。这是不同的需求和劳作。
我其实一直用心的是直接写诗,而不是诗学研究。这是从启步时纠缠的心念。我的代表作,也许会是诗。我明白这是较为纯粹的求索,并无什么功利来扰乱自己。儿童文学同样是因为它的纯粹性吸引了我,而不是其他。好的写作者一般都向往好的儿童文学。
关于《张炜文集》
这是一个难得的自我检察和总结的时刻
记者:五十卷的《张炜文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堪称煌煌巨制,这已经超越了著作等身,堪称一座高峰,宛如泰山孤拔。请您为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这套文集吧。
张炜:写作的数量很重要,但这只对一小部分写作者来说是这样,对大多数写作者并不重要。因为文学创造从来重质不重量。我希望数量对我是重要的。我这里的意思是,只有写得足够好的人,数量对他们才重要,不然就越多越坏。我常问自己:这一次写得足够好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会立刻停止写作,该干什么干什么。写作是极有分寸感的一种工作,是很自尊的一种工作。这种感受一旦丧失,写作就该终止。

《张炜文集》丨漓江出版社
我写得不算多。因为这套文集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我在教学中形成的文字。我一直将这种职业色彩较重的工作,当成现实生活中的所谓“分工”。坐在斗室里的创作,比如小说之类只占了一半多点。我主张以非专业作家的心态去努力写作,并取得专业作家的技能,而不是反过来。反过来的情形并不少见,我会避免。
每个写作时间较长的人,都希望有机会集中印出自己的作品,我当然也不例外。这是一个难得的自我检查和总结的时刻。
张炜简介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新作《我的原野盛宴》反响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