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评门罗:女人这个身份一直在和她的创作打架

艾丽斯·门罗是加拿大女作家,2013年以“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成就,成为第一位加拿大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她没有出席颁奖典礼,而是通过录像奉上答谢词。
张悦然在文学评论集《顿悟的时刻》中这样猜想在家中观看颁奖典礼的门罗:
她既在这份荣誉的中央,也在这份荣誉之外,她在参与,也在旁观,喜悦之余总有一份清醒。这份清醒,源自女性身份的羁绊,而此时它又是一种恩惠。毕竟我们见过很多志得意满、觉得那份荣誉理所应当是自己囊中之物的男性艺术家。对世界的贡献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完美地重叠在一起,显得如此正义,如此无可反驳。正因为如此,门罗这份不彻底的快乐才显得极为珍贵。
其实无论是门罗,还是刚刚去世的大法官金斯伯格,我们都能看到那个年代成功女性身上的清醒与克制。毕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是人们一直以来不假思索的惯习。她们的成功是遵从了男权社会的丛林法则,进而以女性的身份,发起挑战。所以她们的快乐才会“不彻底”。
2020年,社交媒体中的多次论战,包括触及底线的“卫生巾”问题,使得中国的女性们获得了多次“顿悟的时刻”。面对被隐匿、被贬损、被曲解的命运,女性们终于被刺痛了,开始了对于女性问题的反思。
可是当女性问题真正被思考时,又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就如金斯伯格也会引发激进女权的不满、papi孩子随夫姓会被骂“婚驴”等等。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难免面临割裂的境况。
门罗在小说《幸福过了头》中就借女主角之口表达了这种纠结,下文节选自张悦然对于此篇小说的解读。

艾丽丝·门罗
通常我们会说短篇小说是一个生活的截面,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人物遭遇了一些事并做出选择。也许那是一种对过往的终结,或是改变了未来——但是过往和未来没有出现在小说里,那些留白要靠我们的想象去填补。作为读者,我们有一种共识,就是短篇小说的作者不必对人物的一生负责。一生太长了,时间会消解戏剧的张力,冲淡甚至颠覆传奇。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抗时间的。它是一次爆破、一场暴动。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艾丽丝·门罗就是一个总想对人物一生负责的短篇小说作家。她很难撇弃时间来施展她的魔法。相反,她邀请时间加入,在她的小说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她曾把她的短篇小说比喻成一座房子,拥有很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一个时空,她在其中自由踱步,从一间走到另一间。有时忽然想起落下了什么东西,就跑回到另一个房间去取。
所以她的小说从表面来看,有一种较为松散的结构,像是在时空中徜徉。她对笔下人物了解得似乎比大多短篇小说作者更多,他们就像她的同学或邻居,她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们,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去了哪里。也因为这样,她的人物显得更真实,他们不是舞台聚光灯底下声嘶力竭念诵台词的演员,而是更像我们周围的人。
《幸福过了头》是门罗晚期的重要作品。这篇小说没有很大的时间跨度,但是门罗所做的是用女主人公的最后几个月去展示她的一生。可以说,这是一部独特的传记。
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是一名俄国数学家。为了逃离封闭的国家,她和不爱的人结了婚。在自由的法国她见证了革命,也曾张开双臂拥抱生活,但生活似乎并不值得她这样去做。丈夫因为生意失败而自杀,最艰难的时刻陪伴她的只有数学。她终于找到一个她深爱的男人,然而她所获得的荣誉使对方望而却步。
时间来到1891年,我们跟随她去看望了去世姐姐的孩子,拜访了数学领域的恩师,最后前往斯德哥尔摩去做演讲。在漫长、颠簸的旅途中她追忆着过往的晦暗与荣光,被疾病入侵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直至走向生命的终点。
这篇小说的现实时空里,没有发生太多事,只是索菲娅与故人逐个见面,并逐个告别。尽管她对未来仍有憧憬,但是看起来她想要了却的心愿更多,一次谢幕似的巡礼演出。而伴随着这场巡礼的,是旅途中索菲娅头脑中飘忽的思绪。
可以说,索菲娅在一座回忆的宅邸里散步,由一个房间来到另一个。每个房间里都陈列着她不同时期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主题和人物。姐姐与青春、丈夫与婚姻、恩师与事业。她掸去落在回忆上的尘埃,在那些重要的时刻驻足,并在它们之中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局限。
在这篇小说里,门罗同样用许多个被时间分隔又被情感连通的房间,为索菲娅建造了一座个人博物馆。索菲娅是这座博物馆的访客,也是我们的向导,她用私密的个人情感,为我们奉上了一条特别的导览路线。
我们很难忽略的是,门罗是在罹患癌症决定封笔的时候写下这篇小说的。这也是唯一一次她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来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类似的小说卡佛也写过一篇,叫《差事》,讲的是契诃夫去世的那天所发生的故事。两篇小说都写得平静克制,同时显露出荒凉萧索的底色。
这一类小说取材于历史人物,根植于已有的传记和资料,人物的性格不能更改,命运的走向也是固定的,所以创作的空间非常有限。作家为什么还会选取这种受到极大限制的题材呢?或许是因为作家在这个真实的人物身上找到了极大的共鸣。因为强烈的认同感,作者把自己完全代入那个真实人物,用他(她)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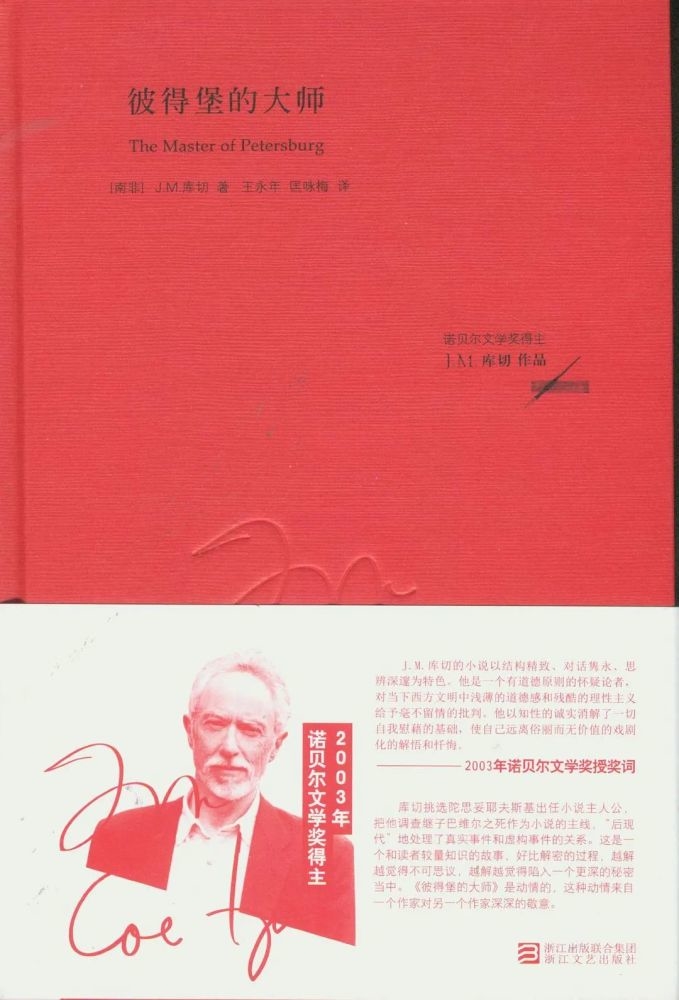
《彼得堡的大师》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对这个人物的了解,不需要像传记作家那样面面俱到,但他们的灵魂是打通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原型的,主要探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承受的丧子之痛。而库切唯一的儿子正是坠楼身亡的,所以他特别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彼时的痛苦,将自己代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他的经历来抒发自己郁结在心里的那份情感。
那么,为什么门罗选择索菲娅呢?
我们或许需要从门罗的童年找到答案。她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并不富裕的乡下家庭,因为母亲多病,小时候她就要承担很多家务和农活。20岁那年,大学没有读完她就嫁了人,迫切地渴望组织起自己的小家庭,以为这样就能获得更多的自由。她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每天只能在孩子去上学的时候,用两三个小时来写作。家里没有人把她当作作家,直到37岁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41岁那年她和丈夫离了婚,结束了长达21年的婚姻。
她离开了丈夫门罗,沿用了他的姓氏,成了作家门罗。在过往的经历里,女人这个身份一直在和她的创作打架,或者说二者在争夺她的时间和灵魂。门罗第一本小说出版于1968年,当时正值加拿大女权运动的高峰,她正是那些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中的一员。
而生活在19世纪末的索菲娅,离开俄国来到法国,在那里她获得了自由的启蒙,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那个为了摆脱束缚、义无反顾投奔婚姻的少女索菲娅,和早年的门罗极其相似。后来索菲娅事业虽然大获成功,却依然受到女性身份的制约,她无法得到一份体面的教职,也无法得到一份完整和平等的爱情。她的才华像一种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而荣誉则像牢笼,将她隔绝其中。
门罗借索菲娅丈夫弗拉基米尔之口,说出了一种在男性当中极为普遍的看法:你给我举个例子,有哪个女人真的重要到改变世界了?那些勾引男人、谋杀男人的除外。女人先天落后,还自我中心,但凡她们有点想法,有个像样的目标可以投入进去,她们就会变得歇斯底里起来,用自己的自大把事情全给毁了。
这些话适用于索菲娅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于门罗的时代。它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离间着婚姻和爱情。到头来,索菲娅发现自己因为心底对丈夫的鄙视,根本不可能爱上他。
在火车上,索菲娅看到一个女人带着脸上包着纱布的儿子,当这个女人展开披肩,把一部分盖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机械的母性。因为儿子出了事故,“她得更体贴一些,仅此而已。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她,说不准肚子里还有一个”。
随即索菲娅想:多可怕啊,女人的命运多么可怕。如果索菲娅告诉这位妇女,告诉她新兴的斗争,女性要争取投票权,争取大学里的职位,这个女人会说什么?她也许会说,这可不是上帝的意思。要是索菲娅说,那就抛弃这个上帝,解放她的思想。她会不会看着她——索菲娅——带着筋疲力尽的神情,以固执的怜悯口吻说,没有上帝,那我们要怎么过这一辈子呢?
在这里,索菲娅意识到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不仅仅来自男人,同样也来自女性对自己的认知。她们不假思索地领受了命运的安排,而且这带给她们安全感,那个男权社会所塑造的上帝,成了她们的庇护所。而她自己呢,这个看起来强大到抛弃了那个上帝的女人,却抛弃不了女人的天性,她依然着迷于那种具有男子气概、确信自己可以保护女人的男人,虽然她明知道那种保护是一份古老的规则和契约,“有时候能让女人受益,有时候则不能”。
所以这样的爱情,必然包含着束缚,包含着她努力反抗和挣脱的东西。这些思考事实上是属于门罗的,她选择了用索菲娅来承载它们。或者说,她相信这些思考也曾属于索菲娅,她只是把索菲娅想过的事再想一遍,把索菲娅没能记下来的事物记下来。门罗在小说里几次提醒我们,索菲娅还有一个身份是作家,她也写过小说。故事的最后,弥留之际,索菲娅从昏迷中醒来,看着自己的女儿,只说了几个字:幸福过了头。

《幸福过了头》译林出版社
“幸福过了头”也是这篇小说的名字,在这里的意味显得相当复杂,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幸福,我们看到的都是生命里的创痛,一次次的悲伤和打击。虽然索菲娅作为欧洲第一位女数学博士,获得了荣耀和世人的尊敬,在传记作家那里,这些价值可能会被放得很大,但是在门罗的小说里,它却显得微不足道。我们感觉到的是巨大的遗憾。在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女人身上未能完成的爱情,未能完成的事业,未能完成的自由……
这一切都是时代的原因吗?如果把索菲娅看作19世纪女性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20世纪的索菲娅真的会比19世纪的索菲娅更幸福吗?说到底,究竟什么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呢?婚姻还是事业,抑或二者都不能?对幸福的追求是否终究是虚妄的呢?
这篇小说也许并不是门罗最好的小说,受到原型人物的制约,门罗没法充分施展虚构的拳脚。一些史料的使用,看到的是考据的热情,却缺乏叙事的温度。数学,作为索菲娅的信仰,没有渗透到文本更深的肌理中,也没有影响和塑造索菲娅的思考。然而,《幸福过了头》却是门罗非常重要的作品。
在2013年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再来看,这个小说仿佛是一篇提早写好的谢幕词。借助索菲娅的眼睛,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得奖之后的门罗。由于健康的原因,门罗没有出席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只能通过录像奉上答谢词。我们不禁想象,门罗是否会在家中观看颁奖典礼,看着那个出现在会场屏幕上的自己念诵答谢词。
她既在这份荣誉的中央,也在这份荣誉之外,她在参与,也在旁观,喜悦之余总有一份清醒。这份清醒,源自女性身份的羁绊,而此时它又是一种恩惠。毕竟我们见过很多志得意满、觉得那份荣誉理所应当是自己囊中之物的男性艺术家。对世界的贡献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完美地重叠在一起,显得如此正义,如此无可反驳。
正因为如此,门罗这份不彻底的快乐才显得极为珍贵。当听到在病床上索菲娅怀着自嘲,用“幸福过了头”来总结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省察自己所依赖的那份幸福呢?它可靠吗,它真实吗?
在门罗的多数小说里,不管女主人公的遭遇多么悲惨,最终还是有一份慰藉在那里。哪怕那些女人仍旧困囿于她们的人生,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她们充分了解了自己的处境,并且这种了解一定不会没有用,它总是可以适当地改变女人们的人生,我们这样期待着。可是在索菲娅这里,门罗没有再给予我们什么期待了。人生的大幕已经落下,那些荣誉只是身外之物了。这篇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门罗这样写道:
人们用索菲娅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是啊,索菲娅所获得的荣誉就像月亮上的那座环形山。月亮距我们的生活有多远呢?在那个没有生命迹象的星球上,纵使那是一座壮阔无比、美轮美奂的环形山,它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我们是叫它索菲娅,还是玛丽或者朱迪,它都在那里矗立着,而且毫不介意。说到底,荣誉和人生一样,也许都是一场幻影。
本文节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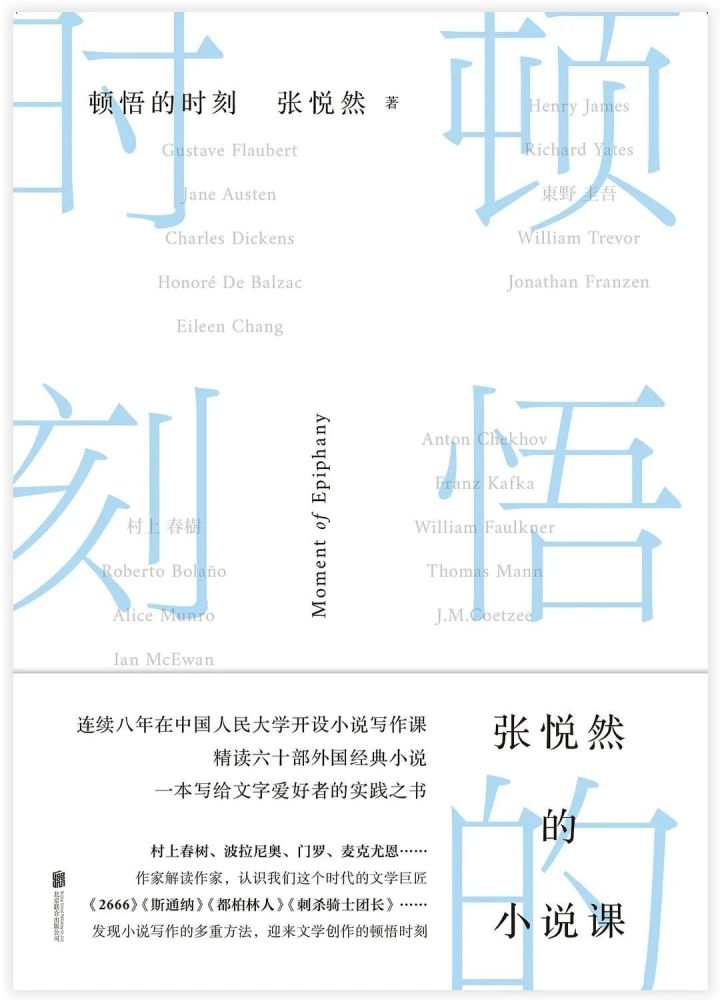
《顿悟的时刻》
作者: 张悦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磨铁图书
出版年: 2020-6-1
文字丨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凤凰网文化”,选自《顿悟的时刻》
图片丨网络
编辑丨周郎顾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