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我们为何迷恋作家的写作“周边”

对于喜欢的作家的写作“周边”——书信、笔记、随感、访谈等等,我们常常趋之若鹜,有趣的是,作家本人对这种迷恋,总是与我们站在相反的立场。海明威在被《巴黎评论》的记者问起从文学工程切换到另一项工程是否容易时回答:“我正在打断自己严肃的工作来回答这些问题,已经证明了我有多愚蠢。”如果我们想要更多地了解作家本人,没有哪位作家会承认他保留了一部分真实,不写入作品中。让写下来的东西永生,是海明威写作的唯一理由,因此小说中虚构所创造的,是要比真实更鲜活的东西。也许我们会申辩需要阿里阿德涅之线,海明威会反驳“多读几遍肯定比头一次读得到的东西多”。他既不想承担带读者探求作品中更难理解的部分的义务,因为“写书和故事已经够难了”,也强烈保护着还未完成的作品的私密和孤独。不过,与他的观点契合,收集到一些作家们作品以外的声音,尤其是产生冲突的对话,对没有多读几遍的人来说,是一条“从自己的认知中将人物塑造出来”的捷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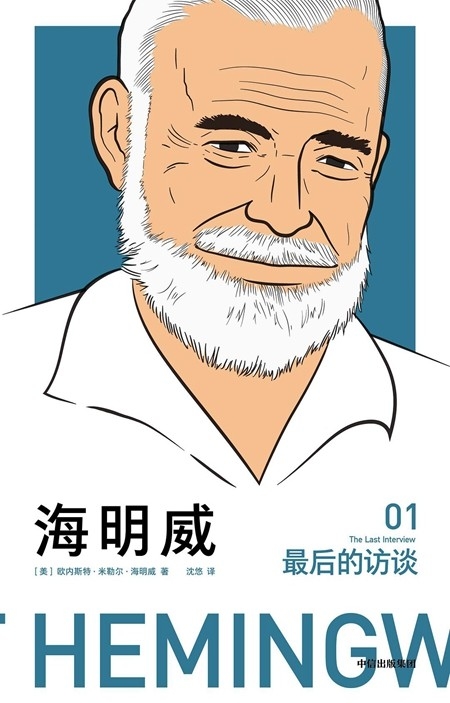
读《海明威:最后的访谈》,起初他的骄傲甚至冒犯,加深了我对他的偏见,读完则好像一起喝了几顿酒的亲切。《大西洋月刊》的采访者发表过一篇“把福克纳切成了碎片、碎片”的文章,海明威勉强同意他的采访时说:“你是过来把我切成碎片,然后喂给威廉·福克纳的。”当时海明威五十五岁,身上有两百多个弹片疤痕,膝盖骨、腹沟股、椎骨、手脚、头部受过或正受着断裂、压缩等轻重不一的伤,还有一个仍在试图修补的肾。见面后,因为采访者爽快答应了喝酒的邀请,海明威顿时高兴许多,还向他吐槽了一个他遇到过的“全世界最冷酷的人”,因为他和海明威一起工作了三天,滴酒未沾。
海明威绝不是唯一在关于写作的访谈表态不想谈论写作的,但是在费兰特以匿名发表小说,并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后,我才惊讶地意识到作家们在作品先行和作品放生上达成的默契和某种共济。
故事开头,费兰特就让天才女友失踪了。自我注销,这个企图一直诱惑着费兰特,后来,一个人清除自己在世界上留下的痕迹,加入了另一个人的见证,成了“那不勒斯四部曲”。她说自己小说中的女性,生活里都找不到一段完整的时刻,而现实中,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平静下来。总有人会在消极饱和时说出“我不在场”。费兰特认为这句话非常有力,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讲述。按她的说法,莉拉的人物自有原型,但我总是猜度,她的失踪多少也寄托了费兰特的自我理想。并且是她匿名发表小说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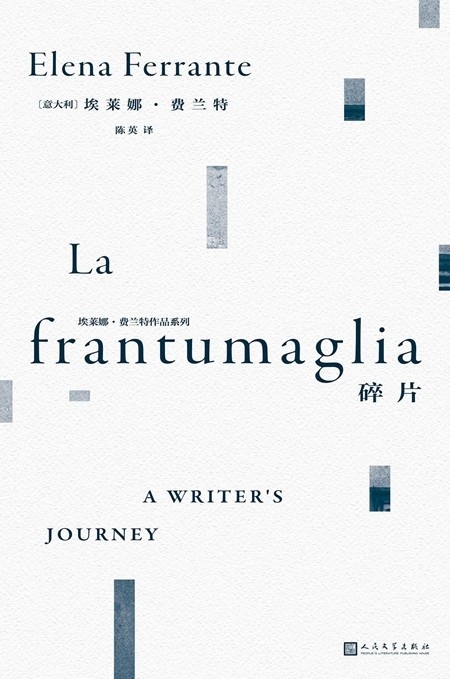
作者的身份生于写作,也在作品完成时消失。《碎片》这部费兰特与编辑、导演、记者、读者等来往的书信集中,她花费不少篇幅重申——因为匿名是每家媒体必提的问题——自己脱离作品就是个普通人。你是谁?埃莱娜·费兰特,十三个字母,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一个作家,出版了六部作品,这还不够吗?费兰特的准确和犀利被她的谨慎和礼节包裹,是屋外车灯的光,穿过厚厚的窗帘仍然晃眼。她的创作远大于她的发表——她的抽屉对此最为了解。对访谈认真做好的答复,也有不少没有寄出,第一次发表于《碎片》中。看到她详尽地解释、举例,甚至大段摘抄因为顾虑而删去的片段,生动地回忆母亲的裁缝世界和出门时光彩照人的样子,不回避试图把妹妹关进阁楼、借住在里面的“野兽”杀人的童年,也不难理解她为何不轻易接受访谈——每一次回复都耗费了她巨大的精力。最终它们还可能因为不够真实和不够真实的小说稿一起,一直躺在抽屉里。
费兰特形容埃莱娜是莉拉的“一个非常精彩的附庸”。我和天才女友之间互存情谊也互相洗劫,把“女性的敌意、抵触和愤怒展示出来,和慷慨仁义的情感放在一起”,正是费兰特的用意。她要做一个冷静的人,维系自己的安全感和秩序感,写出任何人、任何关系都矛盾复杂的内部,写出席卷它们的“碎片”。
“碎片”是费兰特母亲留给她的那不勒斯方言词汇,每次想起这个词,费兰特就想起无缘无故的哭泣,她称之为“ ‘碎片’的眼泪”。 她已无从打听准确的含义,只知道“碎片”神秘,会引起无缘无故的痛苦。费兰特崇尚爱和激情,但这些不乏歌颂。她的决心是和“碎片”拉得足够近,打破神秘,把感受到的说出来。对一个赞赏“不在场”的人来说,主动逼近确实是一种冒险。并且要在不体面里找到养分,在漩涡里重新建立起——哪怕是勉强的、临时的——一种平衡,在过去的碎片里找到那些等待救赎的部分。小说要面对的,是一笔私人旧帐。正因为如此,它要传递出对她来说必须的、依靠她的价值判断、对她来说正确的东西,不受约束地把感受“如实”而非“逼真”地讲述出来,她和过去才能得到“清算”——费兰特在《碎片》里好几次提到这个词——而非“和解”。
马尔克斯的小说也必须经得起冷遇,酝酿十多年写下《百年孤独》,也是要给童年一个交代。他在故事和人物中藏了许多密码,只有深谙他经历的人才能破译。这大概也是写作的一种乐趣和对评论家的挑衅。作为一个拉美人,魔幻在成为他的风格之前,就已经是他的日常。外祖母讲给马尔克斯听的那些故事,白天让他沉浸,晚上把他吓得不轻,尤其是她总用沉静的语气,显得更惊悚。《百年孤独》模仿了她的语气。外祖父对马尔克斯的影响很深,他曾让人打开了一箱冰冻鲷鱼,把没看过冰块的马尔克斯的手按进了冰块里,这个意象成了《百年孤独》开头的缘起。

“优秀的小说是现实的诗意再现。”马尔克斯坚持自己讲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跟读者的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百年孤独》里美人儿蕾梅黛丝飞上了天空,但要怎么让她飞上天,马克尔斯想了很久,直到他看到自己院子里的床单,因为风太大,怎么也晾不成,总要被风吹走,才愉快地回到打字机前,这下谁也拦不住蕾梅黛丝上天啦。写《族长的秋天》时,马尔克斯因为无法清晰描绘族长独裁者的品格特征而反复重写、反复搁置。两年后他在描写非洲狩猎生活的书里读到大象的内容时,找到了继续写族长的方法,把大象的习性嫁接到独裁者的品格上。
艺术家的人生经验和艺术作品对此的反映之间存在一种关联,加谬在他的手记中作了绝妙的比喻。“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从整个经验中切削下来的一小块,像钻石的一个切面,内蕴的光芒将无穷扩散。”这是“沃土般的作品”,而说出全部经验的,则是“超载的文学”。 我们总在关心作家如何写成了这部小说,关心这些成形的字与现实之间发生过什么,想由此找到加缪所说的“经验和因而产生的意识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
但作家周边不是小说药方,就算读懂了也还是写不出来。不过我们总是能从中受益,作家们大多数不神话所谓的灵感,他们互通自己的感官世界,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取材,而是受到启迪(我们则从中受到二手启迪)。灵感以许多形式向他们发送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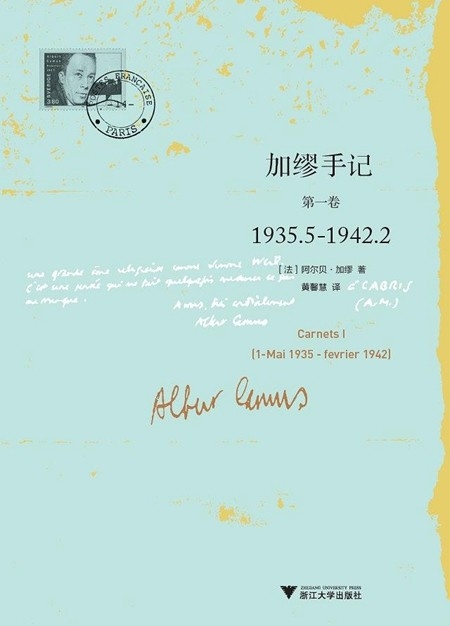
《加谬手记》也是一部碎片集,充满了热忱、质疑、剖白、“有价值的冲突”,以及连自己也不太明白,但还是很有必要记下来的东西,还原了他身上不可阻挡的夏天。自始至终都对大爱同时抱着欲望和绝望,读第一卷时,那种俨然只属于年轻人的狂热一直持续到最后:读《西方的没落》,被古希腊多立克柱的木头用材打动,相比用石头做柱子的“焦虑”的埃及文化,“古希腊之魂借此(木头)表达出对时间的敌意”;完成《西西弗斯》后感到自由开始了;闻到了9月角豆树在阿尔及利亚散播的爱的气息;注意到了火车上一对都不好看的情侣,男人被并不引以为傲的女人在大庭广众下爱着而感到尴尬;“书写,就是不问世事,从某种程度上隐居在艺术里”。
这与匿名的费兰特喜欢“在大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小角落”形成了暗合,文学不仅完整清楚地说出了我们难以名状的感受,更让我们经历了没有经历过的体验。费兰特喜欢在康拉德的文本里占座,因为好故事是可以居住的,有很多场所,可以催生出其他看不见的故事。或许,更好地刺激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迷恋作家们写作“周边”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