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相对精善”的《红楼梦》评注本:《蔡义江新评红楼梦》
 2021-01-28
2021-01-28

蔡义江评注《蔡义江新评红楼梦》由龙门书局于2010年7月出版,据《新评》“前言”称:“此书所依据的版本文字与注释,是在1993年10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红楼梦校注》和2007年1月作家出版社重版《增评校注红楼梦》基础上,再经精心修订调整后形成的,其完善程度,比之于前两版来,又有极大地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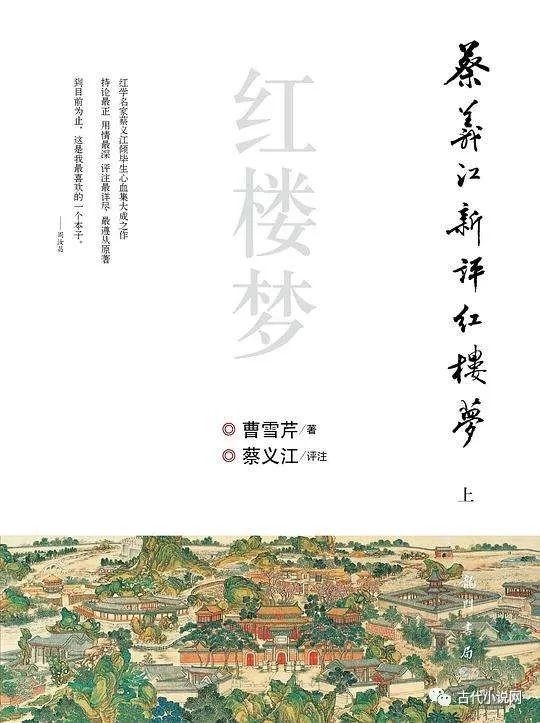
《蔡义江新评红楼梦》
如此说来,《新评》本是一个精心校评的本子。周汝昌先生曾做如此评价:红学名家蔡义江倾毕生心血集大成之作。持论最正,用情最深,评注最详尽,最遵从原著,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本子。周汝昌先生的这段评语见《新评》封面题词,其意甚明,其情款款!
笔者2010年8月初参加北京西山实创科技培训中心召开的“纪念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议休息期间,龙门书局的编辑于培训中心现场签售《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于是,便购得一部蔡先生的签名本,并当即表示:“回去将认真拜读!”蔡先生则郑重其事地说:“我倒是期望能有人撰写批评文章!”笔者脱出而出:“学生愿为!”
此后不久,《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一文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该文乃笔者彼时所做“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课题的首篇,此后结集出版的《红学学案》(新华出版社1013年3月年版)这部红学史新著的首章。
不过,这一承诺所催生出的《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一文并非一篇书评,为了兑现承诺,《“相对精善”的评注本:》匆匆构思,前后正好时隔了10年的光阴。
倘若概观近几十年来的《红楼梦》校注本、校评本以及评点本,大抵或在学术价值方面或在传播价值方面或在“一家之言”个人著述价值方面各有长短,至于能将此三个方面很好地兼美者实在寥寥。《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便做到了三者很好地兼美了,这也是笔者时隔10年仍愿意为这部《新评》本写一篇书评文章的内在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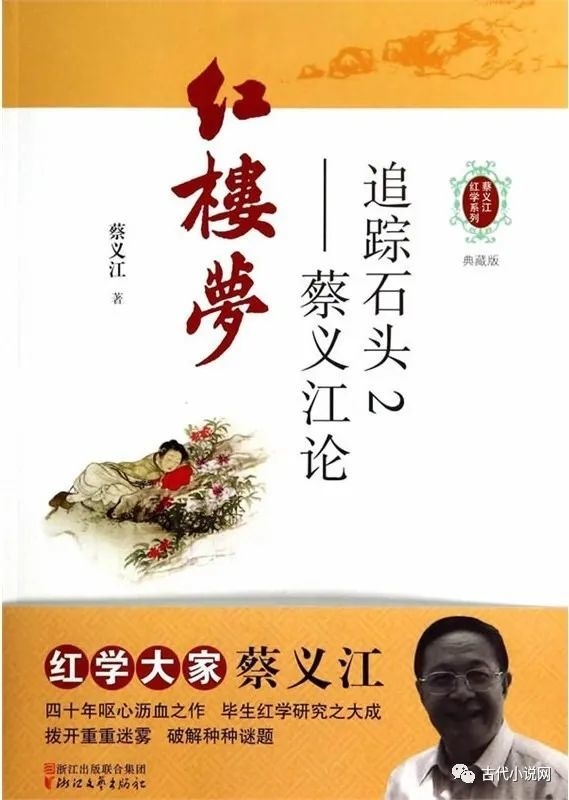
《追踪石头2——蔡义江论红楼梦》
蔡义江著《追踪石头2——蔡义江论红楼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这部文集收录了两篇很有分量的书评,一篇是周汝昌撰写的《新版红楼定假真——简评蔡义江评注》(发表于《人民日报》1994年10月8日、15日星期六第八版)一文,另一篇是杨传容撰写的《一种有特色的新版本》(发表于《红楼》1996年第4期,作者“杨传容”即“杨传镛”)一文,两篇书评都很好地肯定了蔡义江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校注》。
由于《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是《红楼梦校注》的精心修订本,这两篇书评的评价显然有助于读者更充分地了解《新评》本的特色和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
笔者曾撰写过一篇题为《当代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一——以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为例》的文章,该文刊发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笔者称:“当代《红楼梦》评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等‘四家评’,他们的评点成果不仅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途径、逐步实现传统小说评点尤其《红楼梦》评点理论品格的自我提升,并且有益于当代文艺鉴赏学的建设。”
笔者至今认为,“四家评”中能够很好地兼顾学术价值、传播价值以及“一家之言”个人著述价值者以《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为首选,谓予不信,读者诸君不妨通观当代《红楼梦》注评本之后再做月旦可矣!

《红学丛稿新编》
实话实说,若仅就传播价值而言,至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校注本了。这个校注本于2008年7月出版了第3版,堪称当今海内外最流行的《红楼梦》普及本无疑。
据《红楼梦》韩文译本译者崔溶澈教授说:“这个校注本《红楼梦》是以庚辰本为底本的,要比程高本更接近曹雪芹的本意,而且,这个校注本流行很广,影响很大,在韩国有很大影响。我们在海外的红学家只能利用中国红学专家或专门机构所做的版本来进行翻译而已,不太可能自己做出新的版本来加以翻译。”
崔溶澈教授于2015年8月18日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说的这番话颇具有代表性,由此可见红研所校注本的影响力之广泛,这个校注本的世界影响无疑是其他校注本难以企及的。
笔者当时回应了崔教授的这番话:
您的说法我能理解,这就必然需要中国的红学专家或专门机构能够提供一种“最精善”的校注本,不过,这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这是因为由于《红楼梦》版本的复杂性,能够提供“相对精善”的校注本都很不容易了。
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红学家唐德刚教授就曾说过,《红楼梦》是个无底洞,希望将来有大批专家通力合作,把各种版本集合在一起,来逐字逐句做过总校再做出最精辟的诠释来,那就是我们读者之福了。
唐德刚教授的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的确需要大批专家通力合作来完成,不过,肯定不能一蹴而就。今天看来,再像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那样集合大批专家通力合作,似乎很难做到了,尽管这个校本并不是大家都满意的“最精善”的校注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
笔者与崔溶澈教授所谈的意见至今未变:由于《红楼梦》版本的复杂性,能够提供“相对精善”的校注本已经难得,而红研所校注本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精善”的校注本。
至于唐德刚教授的意见至今则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的这个意见出自唐德刚著《史学与红学》一书中《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以经解经”读之一》一文注释(第243页),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颇有意味的是,蔡义江是红研所校注本的参与者,但是,他并不满意这个流行很广校注本,于是下决心独立完成一个比红研所校注本更加精善的校评本。
蔡义江在《红楼梦答客问》一书中假借“客”之问“根据脂评本整理出版的本子,你认为哪种最好?”,如此回答道:
如果我说,不久前龙门书局出版的《蔡义江新评好了吗(原拟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批注》,后遵书局意见改)一书最好,它没有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的“先天不足”的毛病,且评注详尽,接近原著,最易阅读,等等。一定会有人骂:“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问你,难道已销售数百万册的某校注本反不如你,你这不是自吹自擂吗?”
我很难辩说不是自夸。如果我不提自己的评注本,而另指某本最好,恐怕也会有人说:“你这人说话就是不老实、不坦率。既然你以为某校注本比你的好,你又何必花那么多气力去另搞一套呢?这不是浪费精力和资源吗?”
可见是违心的话,非由衷之言。我将也无言以答。所以这个问题最好是留给广大读者、研究者自己去阅读、比较、评说,我自己是不宜当裁判员而应避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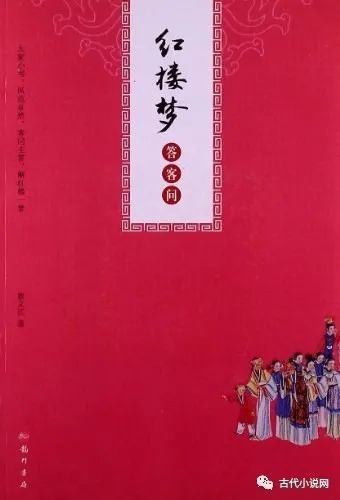
《红楼梦答客问》
由以上“答客问”可知,蔡义江之所以毅然决然地做成一部自己认为最满意的评注本,主要原因在于红研所校注本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红楼梦》的这个“先天不足”的毛病无法更正。
庚辰本是否的确“先天不足”呢?据蔡义江说:“数月前,法国的陈庆浩兄来北大讲课,他邀请我前往。于是我们有聚谈、讨论的机会。他谈起庚辰本来,比我的评价还低,以为是一个相当糟糕的本子,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以它为底本。他一语道破地说,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本,就是‘先天不足’。”
陈庆浩关于庚辰本的评价令蔡义江精神振奋,其实,这类意见不止陈庆浩一家之言而已,下文仍将举例谈及这个问话题。总之,蔡义江决计做成一部“更加精善”的《红楼梦》校注本所表现出的立场、自信以及勇力的确令笔者钦佩。
读者若问:为什么红研所校注本虽已销售数百万册竟不如这部《新评》本呢?蔡义江如此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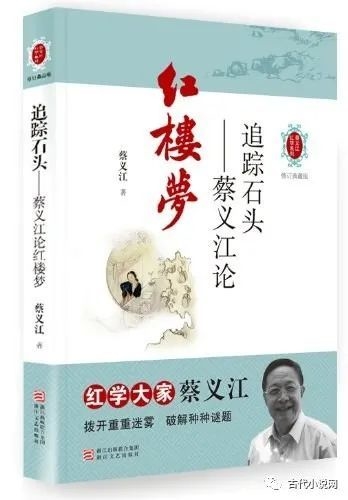
《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
目前,影响最大、销量最多的倒是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注本。这并不奇怪。我说过,国人多崇拜权威。这个校注本领头人是大牌专家,署名校注的是研究单位,出版的又是大牌出版社。它在众多出版的《红楼梦》本子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是必然的。
参加该书校注的同志都是我的朋友,我很尊重他们出色的工作和劳绩。书有所不足,不是他们的责任。我只是以为以庚辰本为底本的决策欠妥、不科学,故提出了上述的一些看法。
在蔡义江看来,销售量多寡并非衡量一个校注本好坏的根本标准,归根结底,影响最大、销量最多归根结底改变不了“决策欠妥”且“不科学”的事实。
其实,关于庚辰本“是一个相当糟糕的本子”之类的评价并非仅止于蔡义江以及他的二三同志。譬如台湾学者刘广定曾在《庚辰本七十一至八十回之版本研究》一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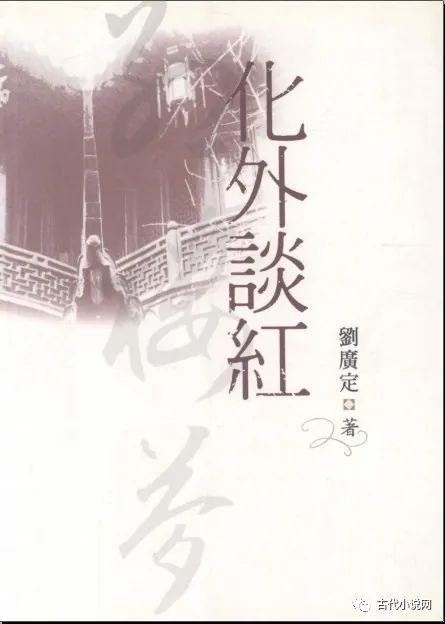
《化外谈红》
一般红学研究者多认为“庚辰(北大)本”较他本为佳且可信。例如俞平伯先生1954年初写《读红楼梦随笔》时,曾比较“庚辰(北大)本”与“己卯本”第九回闹学堂后段,认为前者的“改笔”写得好。冯其庸先生更以之为现存《红楼梦》抄本中最好的一种。
但是在其影印本问世不久,苏雪林先生即于1960-61年发表专文指出其中许多误谬不通的文句,因此认为曹雪芹“只有歪才并无实学”,“原本《红楼梦》只是一件并未成熟的文艺品”。此论虽嫌过激,然甚有启发意。
惜她受了胡适之先生的影响,“决定不写《红楼梦》的文章”。以致没做更深入的研究。“庚辰(北大)本”大约是抄错处最多,但红学家研究也最多的版本。笔者寡闻,似除苏雪林先生外少有指出或考究其中误谬原因者,甚多红学家常就此从事校勘、进行研究而无所疑。
《庚辰本七十一至八十回之版本研究》一文附有“结集后记”道:“本文之目的在证明‘庚辰本’是经多人过录而成,音误与形误字极多,且有近代人的改笔,不宜视为最接近‘原作’的‘真本’,但未推论到其他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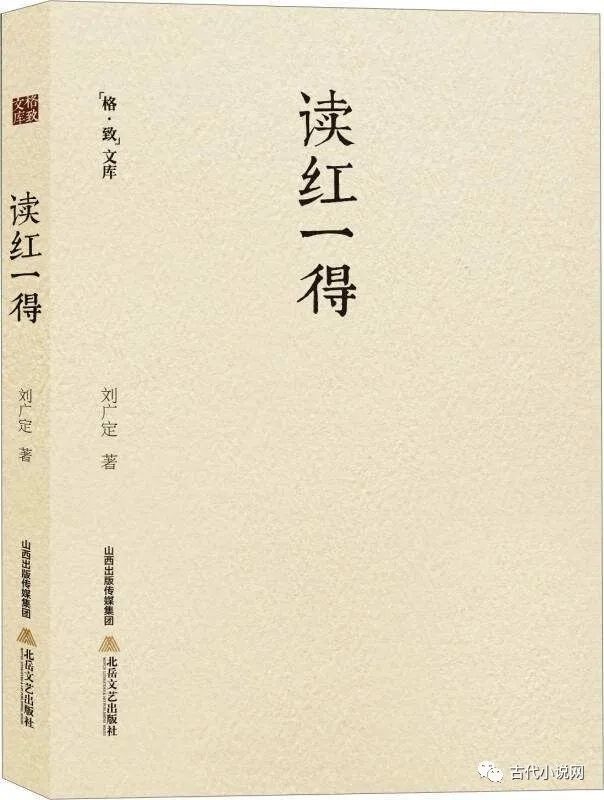
《读红一得》
刘广定的“笔者寡闻”是否属实呢?这个疑问并非本篇书评所必须考究的问题。刘广定所谓庚辰本“不宜视为最接近‘原作’的‘真本’”的断语耐人寻味,如果他的判断是成立的,正可以验证蔡义江重起炉灶校注新版《红楼梦》的方向的正确性。
既然以庚辰本为底本的做法“决策欠妥”且“不科学”,那么,可取的做法应该如何呢?杨传镛在《红楼梦版本辨源》一书中说:
不难想象,当乾隆年间《红楼梦》以抄本流传起,一直往后,其数量一定是很可观的,应以千万计。时至今日,已发现的只有11种,真应了“存什一于千百”这句老话。由于传播链条失去了绝大部分的环节,要一一弄清楚各本畸变的原委,是很困难的,有一些问题的解决,还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得其大概。
而为了校订《红楼梦》,化脂本为普及本,有了这个“大概”,也还是可以找出一个办法的。我的想法是,凡甲戌本存在的,都用作底本;甲戌本缺的,先用己卯本,乙卯本缺,再用庚辰本。不论哪个底本有欠缺之处,则汇集所有本子,从众,从善予以厘定,务求存真。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不管你说它是“混合本”也罢,“杂烩本”也罢,为了尽量存真,只有这样才能够以最佳的形态接近曹雪芹的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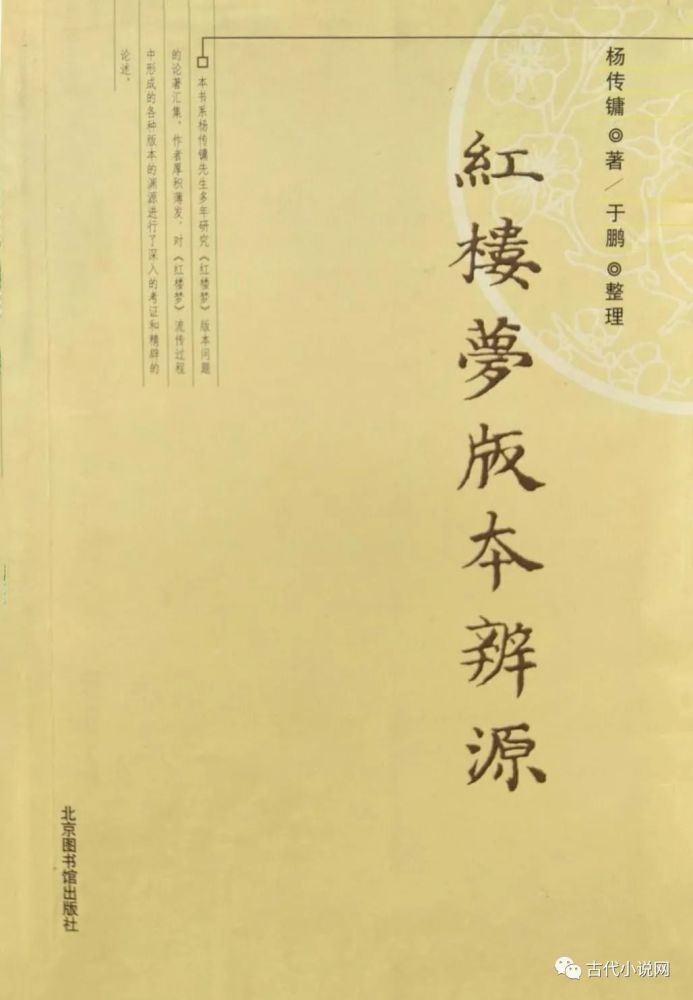
《红楼梦版本辨源》
杨传镛提出的“从善”以“存真”的校订思路与蔡义江所坚持的《红楼梦》校订原则有着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这从《红楼梦答客问》一书中可见看出:
整理《红楼梦》的工作,与校订其他古籍有很大的不同。校订某集,通常选择一部最优(最早、最全或文字最可信)的版本为底本,再参以别本来校订。可是《红楼梦》由于它流传状况的特殊性,你找不出一部适合做底本的本子。所以我整理出一部最接近曹雪芹原意的《红楼梦》来,唯一的办法,只有遵循“择善而从”的原则,将凡有长处的抄本的优点都集中起来。【11】
杨传镛与蔡义江都赞同首选甲戌本为底本的做法,这是他们的最基本的共识,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杨传镛充分地褒扬了《蔡义江新评红楼梦》的前身即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他说:
理想的本子应该是兼具二者(笔者按:脂本和程高本两种)之长而去其短。也就是说,需要经过汇校,化脂本为普及本。然而,这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好的。
首创这个工作的是俞平伯先生。50年代末,他校订了一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当时,因条件的限制,用了戚蓼生序本做底本;戚序本曾经人整订过,这就先天不足。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完成一部新校注本,与俞本不同,前八十回的底本是庚辰本,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大步;却因过分倚重庚辰本,也有不少偏颇的毛病。
新近,我得读了一种新出的脂本普及本,此本由蔡义江先生校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读后以为,这是一部新颖、别致,特色鲜明的《红楼梦》新版本。……如果说,在化脂本为普及本的征途上,俞平伯先生开辟了道路,红研所又向前跨了大步的话,那么,蔡义江先生则是梳理了第三块里程碑。
然而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相信,一定还会有更为完美的脂本普及本接踵而至。【12】

《增评校注红楼梦》
杨传镛评价《新评》本不仅“新颖”“别致”,而且“特色鲜明”,譬如《新评》本注释方面简明扼要、别具机杼;融入大量脂批精华文字;诗词曲赋详解嘉惠读者。
尤为难得的是,在杨传镛看来,蔡义江的《红楼梦》校注本“后来居上”而堪称“第三块里程碑”,此可见杨传镛的期许非常地高了,这一期许实则基于蔡义江在“化脂本为普及本的征途上”走得更加稳妥的缘故。或者说,蔡义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这个“样板”将召唤“更为完美的脂本普及本接踵而至”。
蔡义江在《红楼梦答客问》一书中谈及自己“择善而从”的校注过程时说:
我特地为能整理出一个较完整的《红楼梦》本子,以‘择善而从’的原则,作过三次努力:第一次是1993年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第二次是2007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增评校注红楼梦》;第三次是2010年在龙门书局出版的《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每一次都有较大的完善。
其他出版的新校本,我比较欣赏的是刘世德的校注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和郑庆山的《脂本汇校石头记》(作家出版社)。他们都很尊重甲戌本,是按“择善而从”原则选择底本的。【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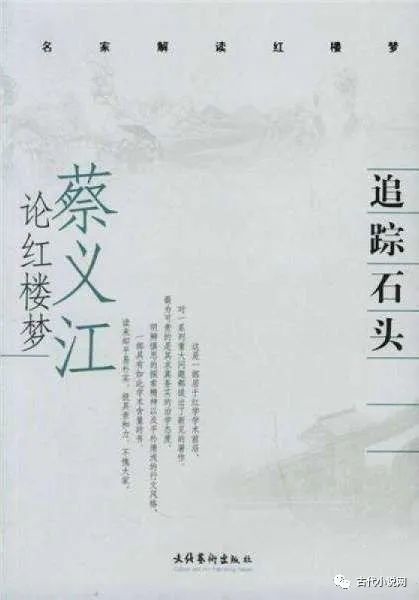
《蔡义江论红楼梦》
蔡义江选择“择善而从”原则自有他的考量,《新评》“前言”说:
关于版本文字,曾有一位熟知通常校订古籍惯例而对《红楼梦》版本形成的特殊情况缺乏了解的同志问我:你为什么不找一种最好的本子作底本,参其他本子来校订,而要用不固定一种本子为底本,用多种本子互校,择善而从的办法?这样你的本子岂不有点像“百衲本”了?
问得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我可以简单地把问题说清楚。正文文字最接近原作、最可信、因而也最好的本子是甲戌本。但它只存十六回,仅有所存八十回原作的五分之一;如果用它作底本,另外五分之四还得找其他本子(本书就是这样做)。
那么,如果改用保存回数较多且也属早期抄本比如庚辰本(它只缺两回,存七十八回)为底本怎么样?问题立刻就出现了:庚辰本与甲戌本所存的十六回相比较,差异处就不少,且可看出异文都非作者自己的改笔而出自旁人之手,改坏改错的地方比比皆是。……
我在《初版前言》中列举了不少例子,可以参看。这也就是本书不采用固定一种本子作底本的根本原因。【14】
应该说,蔡义江“择善而从”的理据正是基于学术上的实事求是,显然容易被读者接受。这一“择善而从”的原则并非始于蔡义江,俞平伯最先倡导这一校注原则,至今已经深入人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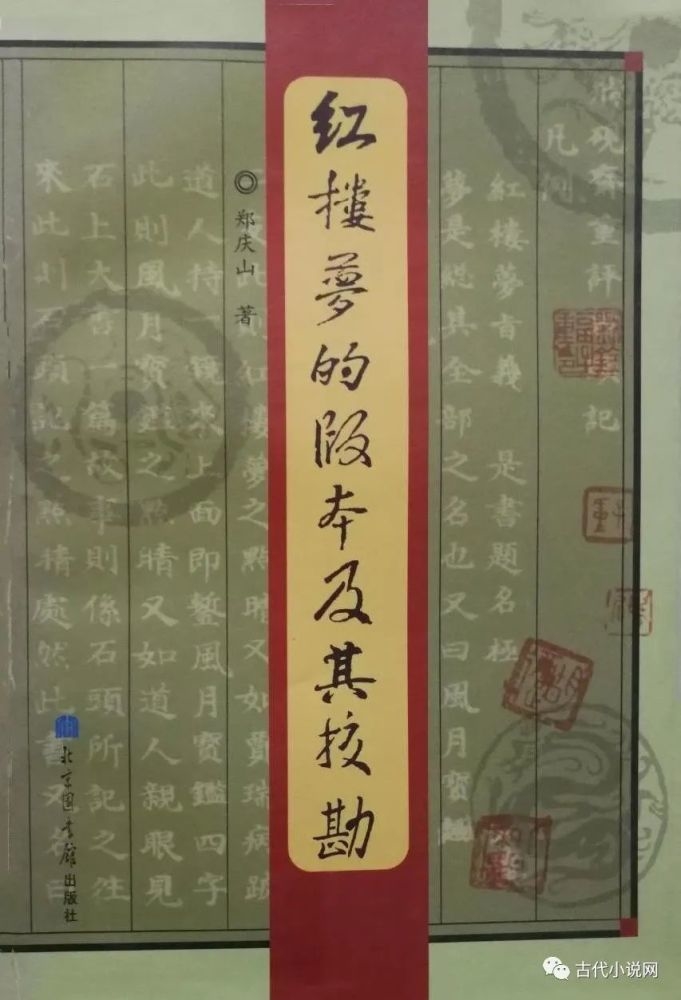
《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
郑庆山在《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一书“自序”中则说:
我们的目的是“存真”,孰真孰假,如何抉择?通常的做法是“择善”。广义的“择善”,应有正误、是否通顺和优劣三层含义。起码要改错,正误可勿论。据校勘家的意见,务求通顺是不正确的,择善而从更不是普遍性的原则;惟有分真假,辨是非是根本原则。
作者当初的用字只有一个,他们说的透辟极了。所以我曾说过,“《红楼梦》版本是真伪文字的对立统一体,校勘工作只集中在一点:去伪存真。”在这个校勘的原则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
文学家们虽然也认为校点本应该接近作者原著,但是面向今日读者,甚至走向世界,起码要改得文从字顺;能改得语言优美,何乐而不为?改就要改好,广大读者应该也是这种意见。我也这样想过。
红学家们你也是两种意见。一种是力求曹雪芹原笔,包括书写用字;但实际做法则兼采各本,个别通用字则加以变通,不求绝对化。一种是用各自本子互参互校,择善而从,在不悖情理和文理的前提下,尽量保持曹雪芹原作面貌。其校勘实践,以采取甲戌、己卯、庚辰三本文字为主。
有的还提出两个目的:一、尽可能接近曹雪芹本来面目。二、使它的文字情节能够比较的完善可读,可供相当范围的读者阅读。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把现存诸本异文和曹雪芹的五次增删联系起来了。【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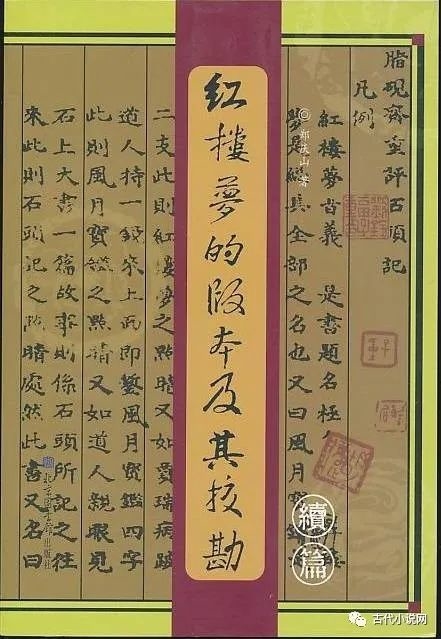
《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续编》
郑庆山强调“存真”原则的重要性,又出于“存真”原则尤其重视“三脂本”即甲戌、己卯、庚辰三种脂本。为什么特别要重视“三脂本”呢?他说:
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有人根据校勘通则来否定这种新拼凑本,为什么不用完善的本子做底本呢?我的回答是完而不善故也。正是为了用甲戌本和己卯本做底本,我才另起炉灶的。此无他,存真原则决定的必然选择。退一步说,即使用了那些完整的本子,也还不都是‘百衲本’?
总之,底本可贵,但是难免讹误脱漏和妄改,不经整理校勘还是不易读。这就必须使用那些难得保存下来的其他抄本以至于刻本了。“三脂本”以外的本子,虽然也都出于脂砚斋和畸笏叟的评点本,但都经过整理和修改,便只有做校本的资格。
在诸校本中,首先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蒙、戚、杨、列四种抄本,因为它们基本上属于己卯本系统。【16】
郑庆山重视“存真”,蔡义江重视“择善”,各自关注的侧重点虽有差异,但在选用甲戌本做底本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郑庆山强调“三脂本”的重要性,他坚持用甲戌本和己卯本做底本,这就与红研所的做法明显不同了,这一点正与蔡义江的立场不谋而合。
其实,无论是“存真”优先,还是“择善”优先,甚或“存真”“择善”兼美,如果能够兼顾校勘通则与《红楼梦》版本的特殊性加以考量,并以校理出一个更加接近曹雪芹原著本子为目的,各种“相对精善”的校注本都可以尝试。并且,能够在学术价值方面或在传播价值方面或在“一家之言”个人著述价值方面很好地兼美的校注本更值得格外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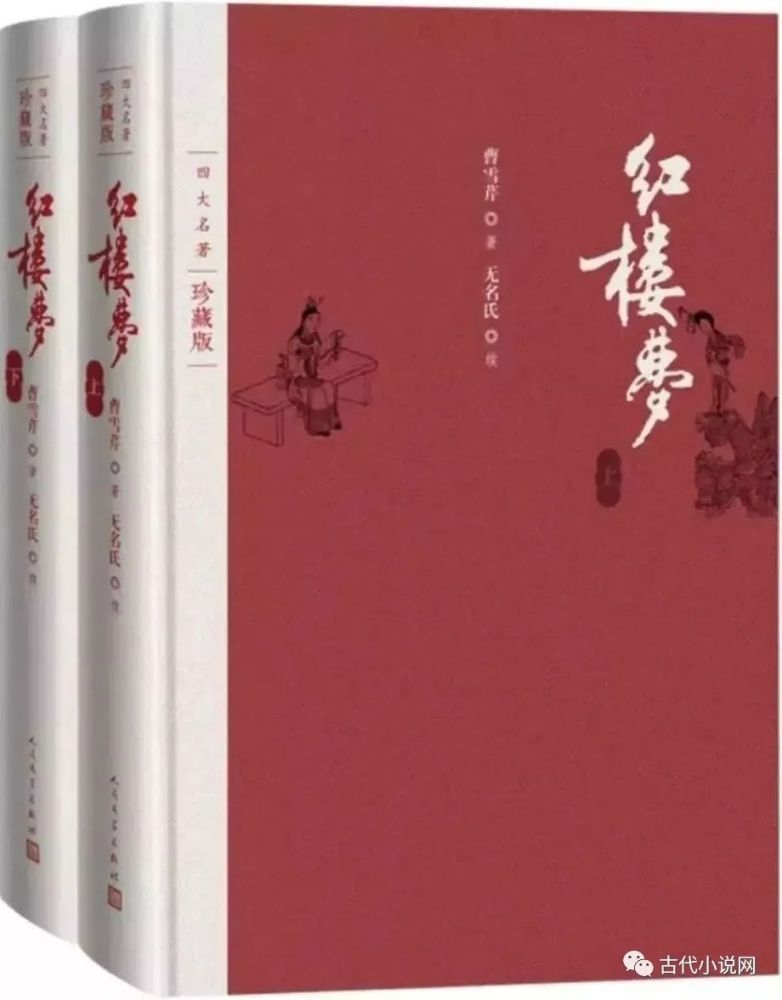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珍藏版《红楼梦》
据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三版序言称:
记得1973年校订开始之初,我们曾为选用底本,进行过热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乾隆二十五年的庚辰本(指底本的年代)为底本,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接受和认可这个本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时,对庚辰本的研究不断深入,而且1994年齐鲁书社又出版了同样以庚辰本为底本而又汇集脂评的校订本,到2006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一种庚辰本的校订本,这说明庚辰本的真正价值,日益为学术界所认识了。我们作为首次大胆采用庚辰本为底本来校订《红楼梦》的学人,当如是欢迎的。……
我们的校订本,距今已二十五年了,当时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这项任务。现在有的同志同样采用庚辰本作底本,大量采用我们的校文,这足以说明当时对底本的选择和校订文字的斟酌去取,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也为后来的校订者起了铺路的作用。【17】
由以上陈情可见,坚持以郑庆山所强调的“三脂本”之一的庚辰本作底本的校注者同样信誓旦旦地认为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做法也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见,倘若在《红楼梦》校注方面达成完全彻底的共识显然是不可能的。

《蔡义江解读红楼》
总之,蔡义江因不满于红研所校注本底本选择的不明智而重起炉灶,殚精竭虑地做成了被周汝昌称誉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本子”即《蔡义江新评红楼梦》。尽管这个《新评》本并非就是读者普遍接受的“最精善的本子”,却足以激发有志斯道者不断地精进,从而做出“更加精善”的《红楼梦》普及本,此乃读者之福无疑。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周汝昌在《新版红楼定假真——简评蔡义江评注》一文中对蔡义江的新版《红楼梦》校注本的表彰致敬令人羡慕。周汝昌说:
依我拙见,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本子,因此才敢向提问者推荐。……蔡校本的第一条好处,就是尽量考虑了各抄本的情况,在纷纭异文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写为一个可读的清本。这给读者一个极大的便利,而又为了照顾读者的一般性阅读,还列出繁复的异文校字记。……
另外,蔡本在异文校比选字上,也有他的独特见解,为避繁琐,不在这样简介中详列字例、句例。但我在此文中愿意强调赞扬的,更在于蔡本的评注。我对此十分欣赏,认为这才更是此本最大的特色与贡献。
评注有啥稀奇!有人会这么想、这么说,哪个本子没有助解?通行本上很多带注,而且还有不少专著,如《红楼梦小考》、《红楼梦识小录》等书,何以蔡本又称可贵?诚然,二百年来,从乾隆末的周春,清末的杨懋建,直到当代,很多学者都曾为‘红注’下过苦功夫,收获成就很巨大。近年还加上了新出几种红学辞典,更是‘注学’兴荣。
蔡注自然也要汲取已有的业绩,如何便算新奇?我说,问题不在于新奇与旧有。蔡教授不一定每条注都出自自创。但注释的事情,虽然需要学识广博,腹笥积富,但又不是仅仅靠这就能作出好注来的。清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尚、器用名色、语词礼数……
蔡教授今之人也,未必在这些上面胜过往哲前贤,但他为今日之读者作注,却有他的一面胜处,即他的文化素养好,文学识力高,而不在于“征文数典”的死知识、粗本领。说起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一般性个别问题了,而是一个中华文化的根本性大问题。……
文化小说,必须相当水平的“文化注者”方能胜任于他的职责,蔡教授应是一个良例。他的注里,还包括校勘取舍的理由,今不详举。他的注最奇的乃又包括着他的评议批点。
在这一项下,我深深感到他对脂批所透露的种种“信息”的重视与破译。他对高鹗后四十回的文字内容的批评与批判,都是最为可贵的组成部分——也才是他的注文的最大特色。【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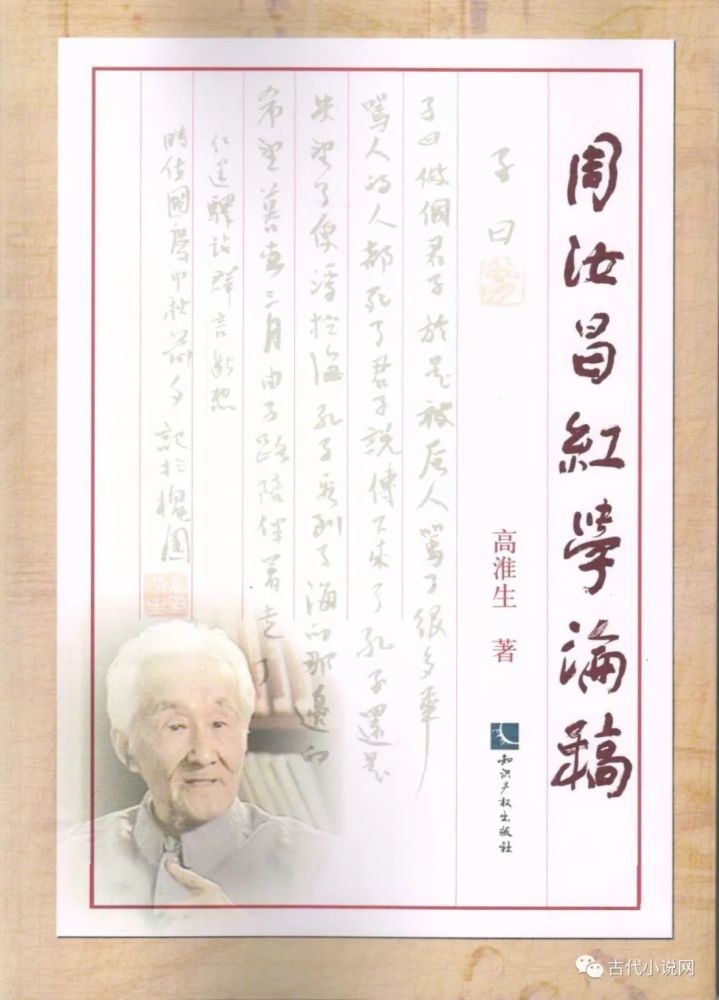
《周汝昌红学论稿》,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周汝昌又在《新版红楼定假真——简评蔡义江评注》一文文末加了两个注释,其注说:“蔡本之出,胜于1982年本,值得欢迎者在于版本史上有历史意义。”【19】周汝昌对蔡义江以及他的《红楼梦》校注本的“溢美之词”溢于言表,即便是完全基于学术立场的评价,仍不免因此受到某种质疑甚至某种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