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作为技艺与艺术的……历史研究
 2021-02-19
2021-0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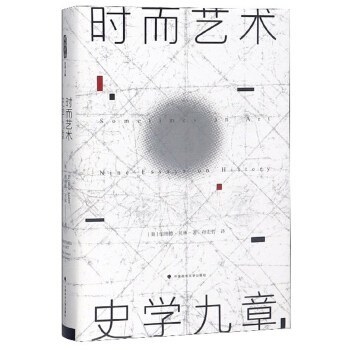
《时而艺术:史学九章》,[美]伯纳德·贝林著,孙宏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5月版,49.00元

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1922—2020)
最早阅读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1922-2020)的文章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他于1981年因卸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而发表的那篇题为《现代史学的挑战》的“告别演说”,由于中译本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就是以这个题目为书名(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所以马上挑出来读了。当时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关于计量史学的方法及其与“潜在事件”和明显事件的关系,另一个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那一段分析——一种强有力的融会贯通的体系和一旦被教条化之后产生的刻板与遮蔽。但是那时的知识准备既不足以理解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研究议题,同时也缺乏对贝林所谈论的史学研究三个趋势的敏感和直觉认识。
再下来就是在2008年读了贝林的名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American Revolution,涂永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译者序”对这位以研究早期美国史、美国革命以及美英工业革命前期史而扬名于西方史学界的历史学家有详细介绍,其中提到贝林对那些宁愿被人视为思想型而不愿做行动型的历史学者(those historians who would prefer to be viewed as intellectuals rather than working historians)的批评,这篇序言最后说人们应该不会怀疑贝林对美国革命人士“拒绝向任何独裁的权力屈从”的行为是满怀深情的。贝林为该书写的“增订版序言”的最后一句话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那种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使个人从国家权力中解脱出来的决心将会继续存在。贝林还说研究美国革命中的诸多思想意识主题给他带来极度兴奋和发现快感(the sense of discovery),“这些发现产生于对历史的一种深刻语境主义研究进路(a deeply contextualist approach to history)——沉浸在一个久远年代的详尽情节之中,并努力去探询那个革命领袖们曾经生活和经历过的世界,而非那个预见了未来的世界”。 (增订版序言)在那种语境中思想者和行动者关注的是英国殖民统治集团的腐败及其对殖民地人民自由权利的压迫,因此迫切要求改变那些统治他们的政治和宪法制度,这些思想意识的最终和巅峰表述就是美国宪法。在我的2008年阅读书目中,这部与我的研究专业无关的著作似乎在冥冥之中对我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
去年6月读到伯纳德·贝林的文集《时而艺术:史学九章》(原书名Sometimes an Art : Nine Essays on History,2015;孙宏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书前有贝林写的中文版序言,当时深感老先生不简单,九十多岁的高龄还有如此清晰的思路和准确的表述,没想到当我今天写这篇书记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于去年8月7日在波士顿郊区的家中去世。想到他九十七岁的高寿以及是因为心力衰竭而不是由于新冠传染,让人感到一点安慰。以我的寡闻,除了在微信上看到几条去年的报道,国内读书界对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去世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关注。这也不奇怪,李剑鸣教授说多年前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在国内出了中译本的时候,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即便在美国,就如《纽约时报·书评》去年发表的一篇悼念贝林的文章所说的,在美国贝林的名字可能也不会引起大批读者的注意,因为他们阅读的更多是历史的畅销书。该文认为,自二战以来很少有历史学家在这一研究领域留下可以与贝林教授媲美的印记。从一开始他的工作就很有创新性,他是最早用计算机从历史记录中挖掘统计数据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多个研究领域中以开创性的著述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因而获得了两项普利策历史图书奖(the Pulitzer Prize for History)和一项班克罗夫特奖(the Bancroft Prize,美国历史学界最负盛名的奖项)和2011年的国家人文奖;他在哈佛大学执教半个多世纪,培养的博士生中有杰克·N·拉克夫和戈登·S ·伍德这样的著名学者,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学生一起培养了美国许多顶尖大学的历史系。现任教于布朗大学的伍德教授说他改变了教育史,推翻了我们对革命的全部解释,改变了我们对移民的看法,“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y R. McLean and J. Schuessler, www.nytime.com/2020/08/07/books)伍德在他自己的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1970年获班克罗夫特奖)的“序言”中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他将美利坚早期史的研究转变成一个令人激动而且无比重要的研究领域,由衷感谢。”这话听来令人深有感慨,当教师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大、更好的对学生和对学术事业的贡献呢!
贝林在晚年仍然勤奋著书立说,出版了《开辟一个新世界:美国建国者们的天才与矛盾》(To Begin the World Anew: 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2003)、《大西洋历史:概念与轮廓》(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2005)、《野蛮年代:英属北美的人民:文明冲突》(The Barbarous Years: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The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1600–1675, 2012)和2015年的这部《时而艺术:史学九章》。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还出版了有学术生涯回忆性质的文集《照亮历史:70年回顾》(Illuminating History: A Retrospective of Seven Decades,2020),“在这些引人入胜的文章中,伯纳德·贝林揭示了他作为殖民地和革命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创造力的源泉”,他的学生杰克·拉克夫教授如是说。
贝林在《时而艺术:史学九章》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是一部关于历史和记忆的文集,涉及数世纪以来欧洲、美洲以及与西方智识生活相连结的全球共同体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之问题、可能性和局限。文集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有五篇文章,涉及历史的本质与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局限,涉及历史同记忆的复杂关系与限制历史的情境。该部分的两篇文章论述历史研究中的创新,包括新颖趋向和杰出成就。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论述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亦即早期英帝国边缘(包括北美、苏格兰和澳大利亚)的文化。……总的说来,这本书首先论述历史研究系统性的问题、可能性和成就,然后讨论伟大帝国塑造遥远边疆的人们生活的复杂方式。”这篇序言最后建议读者仔细阅读英文版第21-22页,“这是所有现代历史研究都应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正是在后面他说的:“从不是科学、时而是艺术的历史学本质上是一门手艺。”(中译本,20页)可以说,“手艺”是他对历史学研究的最终概括。
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经专门论述过“历史学家的技艺”,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就像“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他的“技艺”首先就是考证、分析和理解,但不是因此就可以忘却生活中的现实和历史学的精神价值。关于历史学的“技艺”,贝林主要在书中的第二、第三章进行论述,而在第一章“黑奴贸易的历史与记忆”中首先论述的是要认识和区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区别,贝林以“杜波依斯跨大西洋黑奴贸易数据库”为例,说明精确的、全面的数据统计有助研究者改变对过去的认识和提出新的问题,就如“我们从没像现在这样了解奴隶贸易细节,因此可以客观地、不带个人偏见地对待这个问题。但这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发现我们又会感性化。整个故事仍在活着的记忆之中。不仅对非洲人的后裔如此,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在道德层面与之相关。因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历史与记忆的关系。”(12页)于是他接着讨论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多卷本著作《记忆之场》(Lieux de me'moire) ,说明“记忆”与历史研究不同,它是我们对过去的体验和接纳,是鲜活的和有道德意涵的,在我们的意识中塑造着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进而他指出从历史资料数据库引发的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将某一历史现象既当作历史、又当作记忆加以理解。在这里,历史研究与记忆相互依存和制约,“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是谁,如果我们想明白我们如何变为现在的样子,我们就不能失去或削减任意一方。”(16页)贝林在论述中还提到犹太大屠杀如何折磨着人们的记忆,由此导致了以色列人《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杂志的创刊,还谈到皮埃尔·诺拉对于法国人的集体记忆消褪的担心。无庸赘言,历史研究中的禁区、遮蔽、扭曲必然导致集体记忆的消褪和扭曲,是对国民精神和道德品质的极大摧残。
贝林建议读者认真阅读的那些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指情境主义问题:“这个问题是恢复事件在其中发生的情境:布景、未言的预设、塑造了事件对于参与者的意义的感官世界。过去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试图以它真实的样子理解它。当然,在宽泛的意义上,一个人可以说,所有历史研究都是探寻过去的情境,因为历史学家总是深入过去的环境。”(21页)但是其中包含的问题很多,要解决谈而容易。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预设、态度、信仰与经历,无法以他们经历的方式去经历他们曾经历过的;我们可能不了解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司空见惯的,我们更难以复原他们所过的那些最平凡的生活情境;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而我们无法完整地体验他们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感。(22页)
由于情境主义问题的困难与复杂性,贝林围绕“那本现在看起来仍然了不起的小书,赫伯特·巴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展开了更深入的论述 。他指出巴特费尔德比之前任何人都更深入地探究了情境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第一位尝试详细阐述这些问题并指出其中所涉及的危险和价值的历史学家。巴特费尔德认为在研究过去时参考现在就会不可避免地篡改历史,“尤其是19世纪的辉格派历史学家,为了寻找他们赞同的现代进步的自由主义之根源,他们在描述关键转折时选择了他们眼中的预兆……”(24页)对原本复杂的历史情境的选择、简化不仅造成历史真相的模糊和扭曲,而且会被用来为现实政治服务,即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撰写历史,并且把历史人物分为推动进步的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并且通过必然性、目的论等概念使历史成为赞美现实、塑造权力合法性的工具。虽然我是在八年多前才读到巴特费尔德这本书的中译本(张岳明、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2月),但在九十年代初《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的一篇文章中就了解他的主要观点,成为个人思想经历中对辉格历史叙事的解毒剂。
然而,正如早就有学者指出的,巴特费尔德自己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也未能完全摆脱辉格式的写法,如他的《英国人及其历史》(1944年)和《近代科学的起源》(1949年)。这说明在观念上的正确与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往往不容易统一起来。贝林在他的书中还谈到两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一是1938年巴特费尔德在纳粹德国讲授史学史的时候仿佛颠覆了自己以前的观点,“我过去认为,辉格解释一直是理解历史的障碍,但结果,它曾经却是总体进步的首要阶段……是辉格党人乃至整个英国人政治传统甚至是政治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辉格历史仍是坏历史,但在战争年代的危机期间,巴特费尔德意识到,它起到了在国家意识中铭刻政治自由的积极作用,并在英国宪政的发展中创造了一种起到稳定作用的历史连续感。”(37-38页)另一个关于情境主义的道德问题的争论聚焦在爱尔兰史学中,辉格式的爱尔兰史是为民族解放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这是标准的爱尔兰历史的民族史观,而以巴特费尔德为精神导师的情境主义则力图消除爱尔兰史的民族主义叙事。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布伦丹·布拉德肖(Brendan Bradshaw) 对巴特费尔德和他情境主义观点的道德涵义进行猛烈抨击,认为巴特费尔德所要求的“以过去为中心的历史”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因为它要求历史学家撤回象牙塔,放弃特殊的社会功能。“通过情境分析将事物正常化(它倾向于剥离历史的道德性质)是专业问题的核心。”(40页)上述这两个问题似乎正反相对,实际上的焦点是一样的:在辉格历史与情境主义之间的历史叙事与道德涵义的关系。
引起比爱尔兰史学更为尖锐的争议的是A.J.P. 泰勒(A.J.P.Taylor),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61)中认为希特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外交政策是务实的欧洲扩张主义者的正常做法,这引起了长达数年的狂热抗议。但泰勒认为这是情境问题而非道德问题,并且坚称自己不做抽象的道德判断。贝林说“我们可以反驳泰勒的看法,它们也的确遭到了反驳,但我们不能忽视他的看法。他知道太多国际关系的细节,以至于他无法被忽视。他也可以令人信服地显示希特勒在对外事务上的机会主义侵略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相似性,正如其他人可以展示‘希特勒青年团’同罗斯福公民护林保土队的相似性一样。”(42页) 在我看来,情境、细节、相似性比较等都是历史学的“技艺”中的重要方法,本身并不涉及道德涵义。问题的复杂性是在不同的历史写作语境中,情境主义具有不同的道德涵义,比如在某些比新教徒和辉格党人更为极端的辉格式历史写作语境中,情境主义就因其重返历史情境而对辉格史学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功能;而辉格式历史写作的首要特征正是脱离和回避历史真实情境,在某些文本与观念之间“深耕细作”,从而继续为布拉德肖所说的“一种由意识形态驱使的神话”提供学术包装。贝林最后提出的看法是:“在我看来,这是最深层次的历史。它的种种问题是复杂的、微妙的,为历史学家提出了种种超乎寻常的要求:充分暂停他们当下的工作,进入不同世界,扩展对那些不仅遥远而且与他们自己不同的人的同情,敏感地应对导致未知的复杂情形的表面异常的现象,将后果和意图区分开,做这些事时还要保持道德判断能力,其道德判断能力又不能损害叙事和这个信念:改变、发展和衰亡——也就是瞬息万变——是历史的全部。”(46页)这里提到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而且是与保持道德判断相联系的技艺。
贝林在论述中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研究作为情境主义的突出例子,他认为斯金纳“实际上是一位激进的情境主义者”,虽然斯金纳看不起巴特费尔德的一些观点,但他也同样为“严格的历史性”辩护,认同巴特费尔德的中心论点:要想恢复一份文本的历史含义,关键“在于发掘作者在写作时的复杂意图”。(31页)我们知道斯金纳受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的影响,强调将人的思想意图和概念放到历史脉络中了解,他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提出“文本”“行为”和“阐释”这三个重要概念,强调从文本、行动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中以揭示作者的意图。贝林与斯金纳“剑桥学派”的区别主要在于所关注的历史语境不同,前者关注的主要还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更关注的是文本的、观念的思想语境;在方法论上也有历史学、人类学与哲学、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差异性。
第三章“现代历史的三个趋向”是对历史学作为一门技艺的发展趋势的认识和论述。首先是量化史学的创新在于能够更好地研究“隐性”历史,并且使隐性的历史与历史表面的显性事件结合起来,从中有可能产生出一种与我们过去所知的不同的总体史框架。(51页)其次是跨国的、跨领域的、从中心发展到边缘的研究视角,他以家庭史、近代早期英美史等研究领域的变化说明这种发展趋向。第三是“将内在的、主观的经历同外部事件的进程结合起来”,也就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内在意识及经验等更深层次的内在生活与其外部生活的变化发展结合起来,这当然是更为困难的任务,而且更容易引起争议。在这里贝林谈到了艺术形式与私人经验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联系,认为在十九世纪法国史和宗教史的情感研究这两个领域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创性。事实上这一章是在1981年发表的那篇《现代史学的挑战》演讲基础上压缩改写而成的,因此他所论述的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新的趋势,但是他对这些趋势的形成以及对在各种研究领域中选取例子的精辟分析对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他认为历史学家在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技术性的探索,而是如何用过去末能料到的复杂性和分析维度讲述全面的、复杂的和动态的人类故事。这当然仍然指向了历史学的今天与未来。
历史学永远作为一门技艺,这已经不难理解,那么何谓“时而艺术”?第四章“史学与创造性想象”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的问题是“历史研究中的创新性”,贝林认为他寻找的是“一种能够增益整个史学领域的能力。它能使史学从既定的路径中摆脱出来,转到从未得到探讨的新方向。由此,曾经模糊,或者整体而言未被认识的事物可以突然被人理解,获得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的可能性突然被揭示。”(72页)这种创新能力的获得与“艺术”有密切关系——对前所未见的世界与事物的整体性的想象力、浪漫的精神气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学想象。他以二十世纪四位著名历史学家的工作来诠释了史学研究的创新过程——“时而艺术”是如何实现的,他们是研究十七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和美国思想史的专家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十七至十八世纪的英美制度和行政关系专家查尔斯·麦克莱恩·安德鲁斯(Charles McLean Andrews)、重塑英国政治史结构的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和研究古代史和古典学的纳德·赛姆(Ronald Syme):“在我看来,这些精力充沛、技艺精湛的历史学家,他们创新的史学写作,其背后重要的天分,或者说关键的、必要的‘天才’(请允许我用这个的词),是一种文学想象:像一个小说家一样,可以构想一种不在了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但是在可证实的事实的限制之中。我很清楚事实和虚构的区别,但面对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整体上的历史准确性,我还是感到很震惊,就如同我为佩里·米勒的历史著作中的想象结构而感到惊讶一样。”(84页)这已经说得很清楚,再加上史学史上那个最著名和感人的例子:“吉本(Gibbon)坐在‘卡匹托尔山的废墟中’,‘此时赤脚修士正在[曾经的]朱庇特神庙中唱晚祷’。在这古怪异常的现象中,他形成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全部、广阔的构想。”(81页)这就是凝聚在历史学家“时而艺术”过程中的思想品质和想象品质,是鼓舞历史研究者继续前行的最有感召力的灵感。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别研究在美国革命期间站在不列颠一边的美国人效忠派和那些失败者(包括马萨诸塞最后一位王室总督托马斯·哈钦森),以及英格兰文化在苏格兰和美洲殖民地的影响、推动英帝国殖民事业的各种力量及模式、追求完美的大西洋理想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及意义等四个议题。这些议题充满了历史情境中的各种复杂因素,贝林只能把他所有相关研究中的基本认识和某些结论以随笔的形式表述出来。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理想主义和追求完美的辩护:它们并不是恐怖暴政之源头,而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奋斗之源泉;它们不是以赛亚·伯林所担心的“为喋血准备的方子”,因为它在任何地方都缺乏强迫人的终极能力。“纳粹政权的毁灭性权力、宗教极端主义的窒息性权力,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源于独特的历史情形,试图通过暴力实现劝说无法达到的目的。”他认为应该把理想主义和对完美的追求与那些“民粹主义的暴徒、狂热的权力垄断者”区分开来,在我看来这正是回应了他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的“增订版序言”中所说的,“18世纪革新的根本精神——是其理想主义,以及使所有个体从国家(即便是一个经过改造了的国家)权力中解脱出来的决心——这些精神将会继续存在,并依然存在。”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情境主义和道德理想之间的严肃思考及真诚信念,是他的历史研究的技艺与艺术所揭示的具有永恒感召力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