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炳正先生丨学术的枯竭在于原地踏步
 2021-03-11
2021-03-11

由于人们所研究的学科不同,所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经验体会,也往往因之而异。当然,有些原则性的问题也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使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仍然有其相通之处。但是,由于人们的治学经历或性格爱好各异,还是会带有个人的不同特色和个人独有的甘苦。这一点,也许对人们仍有参考意义。这就是我不揣浅陋,准备唠叨几句的原因。
我是喜欢搞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而且囿于见闻,所知有限。因此,讲起话来,可能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但“田夫献曝”,取其动机可耳。
(一)
语言文字之学,固然跟文史一样,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又是一切文史遗产共同的记载工具。我对文字、声韵、训诂,不过是一知半解,但即使如此,它已使我在治学过程中尝到了一些甜头。我的粗浅体会是:即使把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独立学科,而它的本身就蕴藏着祖国几千年来无限丰富的文化积淀。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结构中,往往可以发掘出许多有关文史的宝贵资料。在这一点上,前人已有所接触,但还有待于开拓。至于把语言文字作为记载文史的工具来看,则不通过对它的深刻理解,也就无法读通几千年来的文史典籍;不仅如此,作为文史研究者来说,往往会因语言文字上的新理解,带来文史理论上的新突破。尤其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讨,更是如此。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而中国的文学遗产,则是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独有的特征而创造出来的。如果不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独有的历史特征,就无法深入探索和评价中国文学遗产的诸多艺术现象,也无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
也许有人认为,研究先秦两汉的典籍,语言文字之学自然是不可缺少的;而读唐宋以下的书,似乎无此必要。但事实并非如此。语言文字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由于时地不同,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发展变化。我们今天读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又何尝没有语言文字上障碍。先秦两汉的典籍,固然有其独特的时代色彩,而诗、词、曲等,也同样有其独特的时代色彩,而为今人所不易理解。因而,作为语言文字这门学科,早已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开拓出新的领域。如张相、蒋礼鸿、郭在贻诸同志的著述,对人们研究唐宋以下的作品,就提供了不少方便,解决了不少疑难,对治学大有裨益。
道理很简单,从古代遗留下的大批文史遗产来讲,语言文字是“运载工具”,因而就我们研究古代文史遗产者来讲,则语言文字就成了不得不首先选择的“突破口”。当然,除专业的语言文字学家外,我在这里称它为“突破口”,显然认为它还不是“目的地”。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学术史上是有不少历史教训的。如汉学家长于文字训诂,而短于微言大义,故常常陷于烦琐;宋学家则长于微言大义,而短于文字训诂,故又常常陷于空疏。宋儒以理学家的程、朱为代表,鄙文字训诂为枝叶,尊经典义理为精髓。结果,往往在文字训释上闹出不少笑话;而所谓义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离题万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性的教训。
庄子有句名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如果把语言文字比做“筌”,把微言大义比做“鱼”,我认为作为治学过程,“得鱼而忘筌”,未尝不可;但是,不首先通过“筌”,则两手空空,又怎能得“鱼”呢?当然,治学各有所专,治语言文字者,不必专攻文史;治文史者,不一定专攻语言文字。但从不同学科应当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角度看问题,则那种过于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对学术发展是没有好处的。而且,这种流弊,也许早已被人们所发觉,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二)
真理是在不断地发展,同样,任何学科也是在不断地完善和进步。我们研究文史这一行的,也毫不例外。因此,搞文史研究,在继承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成绩之外,求“新”,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止不了。如果老是在前人的圈子里“原地踏步”,则这门学问就会得不到发展,以至陷于枯竭。
我在这里所谓的求“新”,不外,第一,在原有的问题之外,提出了新的问题;第二,在原有的结论之外,得出了新的结论。亦即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从近10年来的学术潮流来看,在求“新”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学术界思想大解放的标志,是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在学术领域的强烈反映,我们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学术上的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所谓“真”,首先是指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不以求“真”为目的,则不管结论如何新奇,也只是空中楼阁,对学术的发展并无好处。在中国学术史上,不乏里程碑式的论著,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的某些观点,固然是以“新”见称,但更重要是在于它的“真”。而学术史上那些只“新”不“真”的学说,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推动他的“维新”运动方面,也许起了一定作用。但“新”则“新”矣,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故盛行了一时之后,终于消歇。又如何天行的《楚辞作于汉代考》,“新”则“新”矣,却并不“真”,其不为人们所接受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论著新奇有余,而严肃不足。
其次,所谓求“真”,又是指的对真理有所丰富,有所发展。而所谓真理,我认为就是指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事物不分大小,都有它的发展规律,而学术研究的目的,也就在于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以推动社会的不断前进。由于前人的某些结论,往往不一定是真理之所在,也决不会是真理的终结。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就会出现与旧说不同的新观点。我认为,只要是以求“真”为目的,而不是用求“新”以自炫,则这些新观点的出现,纵然会有些惊世骇俗,而被人们所不能接受,乃至斥之为“标新立异”、“奇谈怪论”等等,那也无妨。古今中外,有不少科学界的先驱者,他们所做出的新结论,不是往往被旧势力所打击或扼杀吗?但我们相信,只要是以求“真”为目的,而所得到的“新”结论,又跟事物的客观规律相符合,则他们的学说,最后总会胜利的。
还应当注意的是:“新”不过是“真”的形式,而且不是惟一的形式。因为求“新”的目的既然在于求“真”,则那些符合历史真实和事物规律的结论,即使是旧了一点,仍然有它顽强的生命力。因而,新的论点未必皆“真”,而“真”的结论又往往以旧的形式出现,是旧传统中的精华。对此,我们应当辨证地对待。
我曾经对学生说过:“我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成就,只不过对探索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又曾说过:“一个人做学问,要能在人类真理的长河中添上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话似乎很谦虚,实际上未免有点自大。因为求“新”并不难,至于求“真”,则谈何容易。在这方面,我只有不断地努力,虚心向前辈和同行们学习。
(三)
人们常常把“精通”作为治学的要求,而在这里,我准备把它缩小到写论文或写专著的范围之内来谈谈;其次,“精通”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我在这里,又准备把它们分割开来讲讲。即在著书立说之时,我认为既要求其“通”,更要求其“精”。我的意思,所谓“通”,即通常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所谓“精”,则是指的阐述、剖析缜密精确。也就是说,文章的最佳境界,应当在“高度”、“广度”、“深度”之外,还要加上个“精度”。正如一架复杂的机器一样,如果整体结构的精密度不够,就会影响正常运转,失掉应有的效力。
所谓“精”,当然首先要求在论点上做到缜密精确,无懈可击;其次是要求在表达手段上做到缜密精确,天衣无缝。而人们往往重视论点的“精”,而忽视手段的“精”。殊不知手段的粗疏,往往会对论点的确立带来不良的后果。
在材料的搜集方面,有的学者要求“竭泽而渔”,这无疑是极端正确的;因为没有丰富的资料,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对资料的搜集要“齐”,而对资料的运用则要“精”。即必须下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功夫。因而,把伪书当真书用,把误句当正句用,以及不限时地拈来就用等等,自然谈不上“精”;即使对待正确的材料,若不肯在剪裁、提炼和融会贯通上下点苦功夫,同样达不到“精”的目的。当然,在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论点时,为了加强说服力,材料不妨多摆几条,但也决不能兼收并蓄,搞成了“獭祭鱼”。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现跟自己已得的结论互相矛盾的资料,哪怕是一条,或一句一字,也决不能轻易放过。必须紧紧抓住,深入钻研,直到彻底解决为止;如果解决不了,只有放弃论点,尊重资料。但我个人的体会,往往正是在解决这种矛盾时,使自己的论点不断深化,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新收获,增加了文章的精度。
在进行论证时,对论点的阐发,自然要由远及近,由浅入深,步步涉营,环环扣紧,充分发挥逻辑论证的威力。在材料充足的情况下,要尽量让材料本身讲话;而一般则是在材料之外,也要有作者的推理。但材料与推理之间的比重,要恰到好处。如果材料的比重太小,而推理的跨度又太大,那无疑会影响文章的精度。
有的同志认为我善于运用地下出土的新资料,故能得出前所未有的新结论。其实,这一点我做得并不理想。但我对此却有一点粗浅的体会:即新资料固然会给人们以新的启发,从而得出新的结论;而如果没有旧典籍的互相印证,则新资料就会“孤掌难鸣”,难于发生作用。而且对前人所习见的旧典籍,由于我们采取的角度不同,或对字句的解释有异,同样可以取得论点上的新突破。不过这一切,如果不从“精”字上下功夫,只是浮光掠影,则不管材料的新旧,都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我还有一点个人甘苦,提供同志们参考:那就是专著也好,论文也好,写成之后,自己必须细心修改。一挥而就,“文不加点”,是不妥当的。不过在自我修改的过程中,要做到精益求精,是不容易的;而严格的自我审阅,是首先要做到的。对此,最好先把稿子放一段时间,把脑筋冷一冷,再用第三者的眼光,跟自己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较客观地进行阅读,这样可能更易于发现问题。亦即在写稿时,要能钻进去;在阅稿时,要能跳出来。在写稿时,要“深信不疑”,在阅稿时,要“吹毛求疵”。甚至要把自己放到论敌的位置上,从鸡蛋里挑骨头,越“苛刻”越好。如果带着“自我欣赏”的情调审阅修改,那效果肯定是不会好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清明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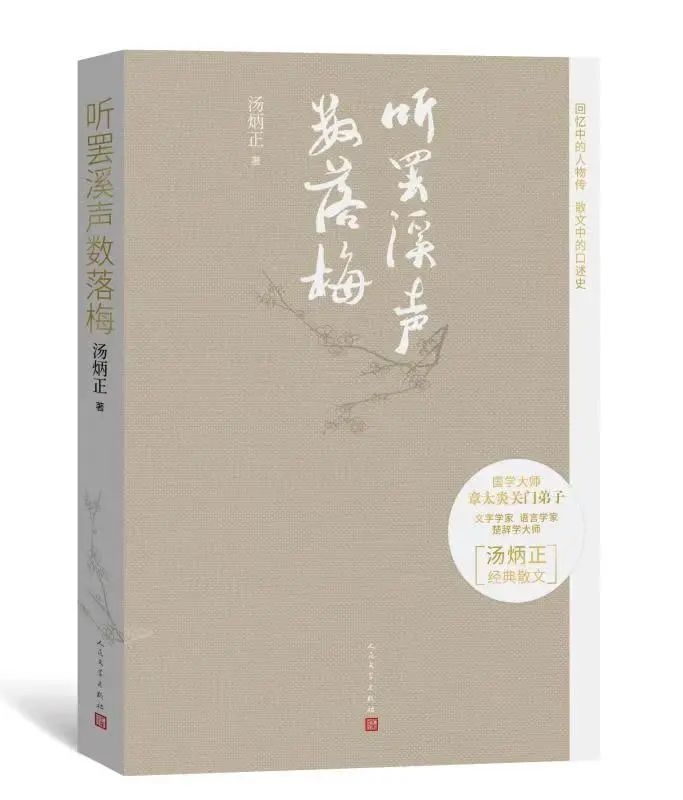
(本文章出自《听罢溪声数落梅》202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山东荣成人。被章太炎誉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曾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声韵学、文字学主讲。一九四六年起,先后任国立贵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著有《屈赋新探》《语言之起源》《剑南忆旧》等。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