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美好药店”,被这位外国导演定格在历史中
 2021-03-22
2021-03-22

种种原因,这部纪录片制作称不上精良,相反当下看来可以说是简陋,但它可以打破你对40多年前中国社会的许多认知,也再一次证明,现实世界,哪怕是已有定论的历史,也是复杂多面的,绝非一个单向二极管。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戏码,至于后人如何理解,有时候远超设计者所能把控。
撰稿|鲜 于
编辑|许 静
校对|张 帅
出品|Figure纪录片
关于1966-1976年的中国,影像资料上留下了诸多空白,特别是来自于外部人士观察视角的作品。
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1972年在中国待了22天,留下部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中国》,迄今都是东西方重视的珍贵史料——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大师交出的作品却被认为是诋毁社会主义光辉形象,于是引出了一场浩大的批判运动:「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但很少有人知道,也是在彼时,另一位外国导演,纪录片巨匠、「飞翔的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花了五年时间,在中国拍摄了一部成片长达12个小时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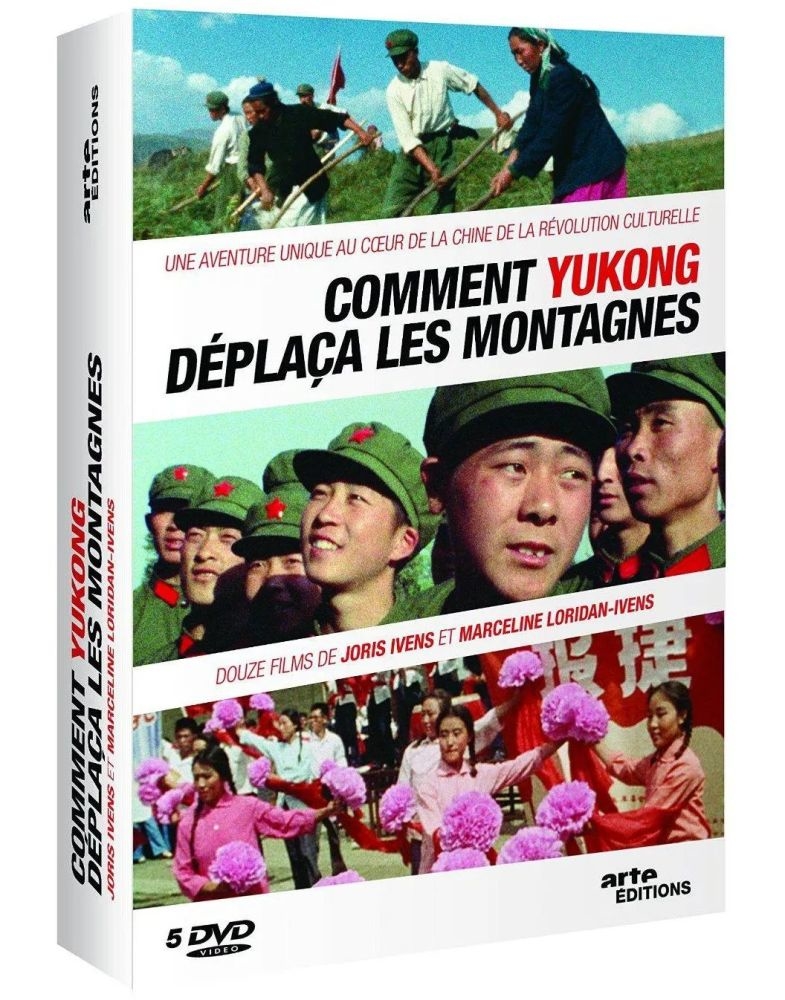
纪录片《愚公移山》DVD
片名出自毛泽东的一篇著名文章。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愚公移山》与《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被并称为「老三篇」。伊文思还在纪录片开头引用了毛的名句:「此愚公不是别人,正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纪录片每一集的主题表明:伊文思的视角中心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中国人,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庆油田》(84分钟),《上海第三医药商店》(75分钟),《上海电机厂》(131分钟),《一位妇女,一个家庭》(110分钟),《渔村》(104分钟),《一座军营》(56分钟),《球的故事》(19分钟),《秦教授(实为钱伟长教授)》(12分钟),《京剧排练》(30分钟),《北京杂技团练功》(18分钟),《手工艺艺人》(15分钟)以及《对上海的印象》(60分钟)。
1976年3月,《愚公移山》在巴黎公映,西方评价是:「伊文思帮助我们同中国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然而仅几个月后,「四人帮」被捕,《愚公移山》被打入另册;伊文思则被视为「荷兰的里芬斯塔尔」——后者是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导演。善良的人认为伊文思和女友玛斯琳被欺骗了,不友好的人则认为他们给那场运动涂脂抹粉,「帮助中国人欺骗西方」……
多年以后,《愚公移山》系列才渐次「散装」出现在大陆网络中,《上海第三医药商店》可能是其中最容易看到的一集。
「为人民服务」
《上海第三医药商店》的开场,细致地描述了1970年代的上海,这里有清晨繁忙的黄浦江,有书写着「毛主席万岁」大字的码头,有赶着坐轮渡去上班的工人,有江边广场上早锻炼的市民,有菜场,有早餐店……

清晨在江边广场练剑的两位姑娘
这种整体性展现,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解读,是俯视的、远景的,而伊文思接下来将镜头聚焦,走进现场,走进一个小小的药店,走进了时代,
上海很大,为什么选择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伊文思在自传中提到:「我们想到了一个大商店,但又害怕人多杂乱,不能集中拍摄,我们想到一个地方是人们更多地讲自己事情的,那就是一个药房。正巧那时我病了。我们就选定到那个药房去看病。那里的职员谈论着我的身体、影片和一些普通事情。我们开始拍片前,彼此就已经很熟悉。」

上海第三医药商店的顾客络绎不绝
这种熟悉,使得伊文思不仅得以细致记录这里的繁忙景象,还以同期声的方式融入现场——「我们也没有抗拒,时间长了,看到镜头也不紧张。」多年以后,当时在上海第三医药商店工作的店员回忆说。
来买两片阿司匹林的小孩,来咨询眼药的老人,气势汹汹来退哮喘喷雾剂的中年人……都在和店员的对话中展开情节。
小孩没有带药方,售货员详细向她询问,然后将用药方法写了张纸条给她一起带着,因为「担心小姑娘买错、吃错」;对于那位眼睛不好的老人,店员详细介绍了各类眼睛用药的用量,旁边诊所的医生也过来帮忙,还建议老人去眼科检查;来退货的中年人,因为母亲哮喘严重而心急如焚,工作人员耐心地检查喷雾剂,发现是砂轮的缘故,弄好后教他正确的使用方法,也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药店医生耐心为老人讲解眼部疾病
伊文思将这些细节,当做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具体体现。
这是1970年代的中国普通人,他们已经学会主动适应时代变革的波折,并积极去成为榜样。所以上海第三医药商店的工作人员总是聚在一起,商讨如何改进工作态度,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讨论的终点永远是「我们为谁服务」「我们如何服务」。
片中有段镜头,店员在停止营业后讨论是否该储备氧气袋,反对者的理由不难理解,病人需求少,卖不出去,容易挤压资金影响药店经营;而支持储备氧气袋一方则认为,病人需要氧气袋的时候,往往情况已经比较危急,人命关天。

药店工作会议中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
最后达成的共识是:继续储备,而且要多储备几袋,因为药店首先要考虑的是「为病人服务」,而不是药店的财务状况,不是利润。
这一点,药店过去的老板、收归国有之后的普通员工认识更加「深刻」。「我过去是资本家,经营药店总是有资本家的想法,比如有些销量好的药就想多进一些,这样不对。」他已经不参与关于药店经营的讨论了,虽然拿着比员工最高工资(82元/月)还高的工资(102元/月)——1978年全国平均工资大约51元/月。

曾经的药店老板变成普通员工后,不得不抛弃纯利益导向经营的想法
语言暴露思想,时代对个人的影响,体现在对话语体系的熟练使用上。
在接受个人采访镜头中,店员包涵非常自然地对着镜头做了一番「自我检讨」:「没有(考)上大学,到了单位以后,自己不安心,认为医生这个工作比较高尚,而这个(营业员的)工作好像是服侍人的工作,没劲。」
30岁出头的她已经在店里工作了六年。她说以前的自己只追求名利,但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认识到作为一个药店店员,就应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革命」。

包涵认为自己不再被旧时代的「三从四德」所约束,自己属于解放的妇女
伊文思接下来问她:「你觉得妇女解放在中国实现了吗?」对于这个问题,包涵可能有些准备不足,尴尬地笑笑,犹豫了几秒,回答说:「我觉得中国的妇女应该不是弱势群体了,但还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我自己基本上属于解放的妇女……」
伊文思对包涵的记录并不仅在于药店里,摄像机跟随着她走进自己的家。她的每月工资是40元,丈夫的工资是59元,两人每月给帮忙带孩子的母亲20元,10元交给药店的食堂;每到星期天,一家人会在家里,她织毛线丈夫带孩子,然后去孩子的奶奶家……
其中一个镜头是:回家后的包涵往沙发上一趟,闭上眼听收音机,然后镜头转到院子里,丈夫蹲在地上吭哧吭哧地洗着衣服——鲜活的场景中,或许是善于做家务的「上海好男人」形象第一次出口海外银幕。
这是伊文思镜头下的日常生活,甚至有些颠覆传统对于文化大革命时社会的印象,似乎也记录着一个熟知视野之外的陌生时代。
「我相信共产主义」
伊文思从1972到1975年的4年拍摄期间,那片红色海洋中最凶猛的浪潮已然过去,批斗特别是武斗再不多见,但运动带来的思想冲击已经烙印在思维中,社会生产生活恢复着表面秩序,普罗大众随波逐流。
但这些伊文思并没有在镜头中呈现,也许是他不想说?

街道上人们正在绘制巨幅宣传画
这位出生于19世纪末的电影导演,对普通的中国观众而言或许有些陌生,但对于纪录电影的爱好者而言,尤里斯·伊文思的作品和人生传奇值得了解一下。
作为一生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电影史的巨匠,他的杰出,不仅在于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命周期,还在于他是纪录片的开拓者之一,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先锋电影诗人」。
他家境优渥,却坚定站在左翼一边,同情工人阶级;在有些国家他被视为仇敌,在有些国家却是人民的老朋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胡濒在《一所流动的「直接电影学校」》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伊文思与「共产主义」的渊源:「1917年前后他认识了苏联,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选择了共产主义;1938年他在燃遍抗日战争烽火的中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共产党,并把它介绍给世界;1946年他在作为殖民一方的祖国荷兰和作为被殖民一方的印度尼西亚之间选择了印度尼西亚,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奔走呐喊;1960年代,他又在中苏大论战中毅然站在中国一边……」
1971年末,伊文思和女友、合作伙伴、法国人玛斯琳·罗丽丹再度造访中国。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并邀请这位老朋友来华拍摄纪录片:「不要拍一个红色的中国,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我们知道欧洲人认为,在中国一切都很糟糕,但这并不是把中国拍得很美好的理由。」

街头买小吃的两位女孩
伊文思接受了邀请,或者说他找到了一个执着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而进行独立观察与思考的机会。「共产主义是这场战斗的先锋队,我相信共产主义,昨天在苏联,今天在中国,如果体力允许,明天再到别的地方。」这是伊文思晚年的总结,心中的理想国、乌托邦,他一生都没停止追寻。
伊文思手头常带着一本西班牙文的《毛泽东选集》。其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他用红蓝色笔划满了杠杠。他相信「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他想向西方观众呈现文革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新面貌,「以正视听」。
但是,尽管有共和国总理的批示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协助,拍摄过程仍困难重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高级记者李则翔是《愚公移山》的中方摄影师,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伊文思认为中国纪录电影的「宣传」气味太浓,表现方法太陈旧,致使西方观众不易接受。真实地反映生活是纪录电影的生命,不然又何必称为纪录片?他要求自己拍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实的,如果需要,甚至可以提供给法庭作证据。
伊文思自己在第二本自传《尤里斯·伊文思:一种目光的记忆》中的记述,写得更加直接。
比如,摄制组首先被带到大寨村。这里是当时中国人眼里的完美典型,但在伊文思眼里:「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短暂逗留,拍了一些素材之后,摄制组随即转道北京。可是,在清华大学的拍片经历同样使他不满。当伊文思问大学生们上大学之前做什么工作时,所有人都回答自己是工人。「这怎么可能?」伊文思感到失望。当他问这些学生对知识分子从事农业生产的态度时,所有人都称颂体力劳动,对插秧、养猪之类的农活齐声赞美:「这都是文化大革命式的生搬硬套的口号,它同我们想拍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
在新疆的经历更是让伊文思和玛斯琳啼笑皆非。在喀什,伊文思将之称作「喀什的噩梦」:那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早晨七点,十字路口与整条街上都拥入了成百名的男女,他们服装鲜艳,笑容可掬,小学生们穿戴一新,第二天如此,第三天仍旧如此……在一个商店里的排演可谓达到了顶点,安居乐业的居民们围着琳琅满目的柜台来回走动,自由自在地挑选商品。」

顾客在商店检验保温水壶质量
以上这些素材最终都没有编入纪录片《愚公移山》,但伊文思把当时没说出口的愤懑和困惑,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伊文思希望拍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摄影机和背后那双眼睛不希望看见一个被设计的中国,这里没有长城、天安门,没有大寨和喀什街景,只有日常中国人的工作、生活、学习,只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不解和对话。
学生和老师的对话,店员和顾客的对话,医生和患者的对话……在对话的情景中打开封闭,最终让世界看见一个鲜活而特殊的中国。
「真情实况从来不是绝对的」
伊文思很清楚,他所拍摄到的「真实」更多停在表面,他也有怀疑和不认同,比如他对清华大学生的批评:「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们是在这种空白的环境下长大,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或所知甚少,他们只会依照学到的教条来和我们谈论长征、延安、解放前的中国、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
但很多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经过选择的「真实」。
「在西安拍摄时,我们看见批斗的游行车来了,汽车司机立刻拐到另一条街上。」伊文思的翻译陆颂和回忆。
在《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陆颂和提到《愚公移山》初剪版本中有一段情节:伊文思跟船下海,问船长:「你理解文革吗?」船长如实回答:「不理解。」伊文思认为这体现了人民对于文革的思考,但审片者却给予了严厉指责:「全国人民都理解文革,为什么他不理解?」要求删去这一段。

清晨上海江景
除此之外,修改意见还包括:不要把《东方红》与上海落雨、群众打伞的画面连接;剪掉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镜头,或者加一句解说,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日出前江上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诸如此类,共61条。
伊文思没有遵从审查者的意志,他找机会把素材带出中国,并在海外完成了剪辑制作,始终忠于自己的感受,并尽一切努力保持独立性——这是整个过程中他所关心的最大的事情。基于对信仰的坚定,对革命的热情赞扬,在《愚公移山》中,他构建出了自己观察和思考之后的乌托邦。
「真情实况只能接近,它从来不是绝对的,它的四周有许多因素。但是我没有说实情之实情的奢望,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玩弄真实情况。」伊文思说。
晚年的玛斯琳则评价说:「我相信当时的中国人的确是在努力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自己也是相信这个乌托邦的。」
但对几十年后的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有大量的历史材料揭批文革,「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新中国峥嵘岁月|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新华社2019年9月27日);另一方面,当彼时社会以秩序而非混乱状态出现在眼前,关于普罗大众适应与相信的力量,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76年3月,《愚公移山》在巴黎公映,几个月后,文革被拨乱反正。
作为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一夜之间名誉扫地,背上一连串的污名:骗子、宣传家、盲目的共产主义者……租住在巴黎简陋的公寓里,失业十年——「只能依靠我们驻法使馆给他解决一些经济和生活问题。」陆颂和语——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热情赞扬,却变成了惩罚。
1988年,90岁的尤里斯·伊文思以在中国拍摄的素材完成了最后一部电影——《风的故事》,用「风」来概括自己的一生,并继续书写对中国的热爱。同年,威尼斯电影节向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雨中的上海街头
一年后,伊文思在巴黎逝世,享年91岁。就像《上海第三医药商店》的最后,店员小刘走出药店,骑上了自行车,消失在上海街头——个体终将淹没在来往不息的人海与特殊时代的绵绵细雨中。
资料来源:
《上海第三医药商店》
《:伊文思的乌托邦》
《他的电影专拍政治》
《“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 ——伊文思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