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洋铭读《吉尔伽美什史诗》|在追求永生的路上理解死亡
 2021-03-30
2021-0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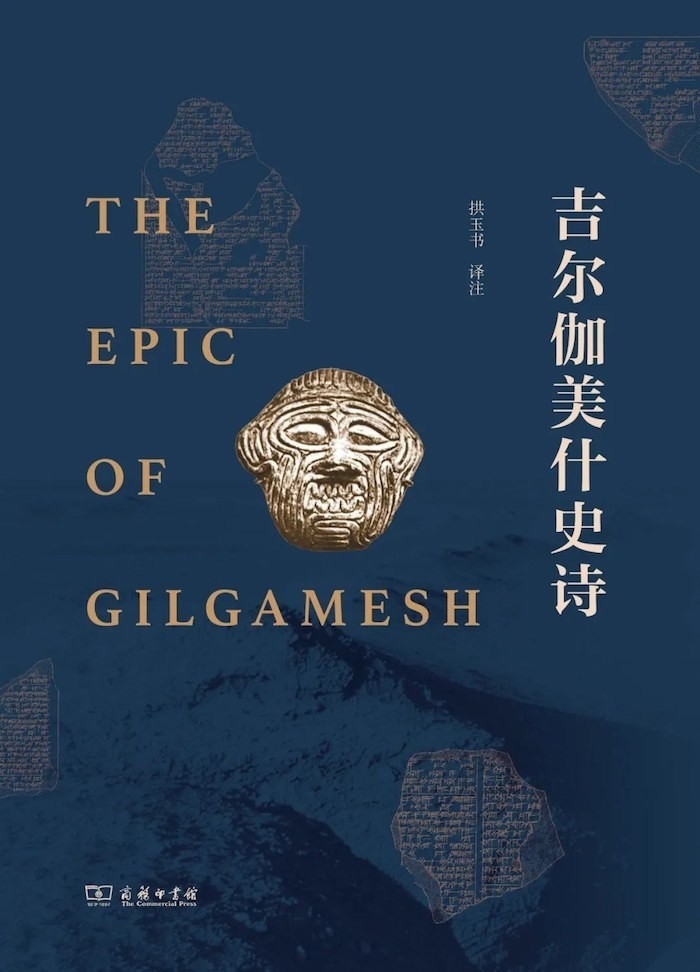
《吉尔伽美什史诗》,拱玉书译注,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288页,98.00元
一战爆发之后,常年旅居巴黎的诗人里尔克几经辗转,最后不得不暂住在慕尼黑。1915年底,欧陆西线战事正酣,里尔克也被奥军征召入伍,需在1916年1月到波西米亚北部的后备部队服役。所幸在友人的斡旋之下,他只在维也纳的军事档案馆中短暂地从事了几个月的文书工作,在盛夏到来之前就脱下了军装,并在当年7月重新回到了慕尼黑。战争给诗人的生活蒙上了阴霾,在这时候,慕尼黑对里尔克而言“就像是一张病榻”。他的为数不多的快乐和喜悦,都是在阅读以及和朋友们的相聚或书信往来中得来的。1916年的最后一天——即里尔克所说的“在西尔维斯特日”(am Sylvester-Tage),他在给友人海伦妮·冯·诺斯蒂茨(Helene von Nostitz)的信中这样写道:
……你有没有在岛屿出版社的集子里看到过这本书,里面有一首古代亚述诗歌的介绍,《吉尔伽美什》?我已经读到了准确的学术翻译(Ungnad译本),在这本真正的巨著中,我体验到了具有魔力的语言从始至终所给予过的最伟大的维度和形式。我不得不说,岛屿出版社的那一版,无论遣词造句多么地有品位,还是削弱了这首流传了五千年的诗歌的真正力量。在原文的片段中(我必须假定它们被翻译得很出色),有一种真正的、巨大的发生和矗立,以及恐惧,甚至诗句间巨大的空隙似乎多少都是建设性的,将那些四分五裂的泥板残片分别开来。这是一部关于对死亡的恐惧的史诗,远古时代的人们写下了它,在他们开始认识到死生之别是确定且无法避免的时候。我相信您的丈夫也会在它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深深的乐趣。几个星期以来,我几乎完全沉浸在这种感觉之中。(Oswalt von Nostitz编:《里尔克与海伦妮·冯·诺斯蒂茨书信集》,岛屿出版社1976年版,第99页)
在与其他友人的书信里,里尔克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着迷也有迹可循。在早些时候写给自己的出版商、岛屿出版社的所有者基彭贝格的夫人卡塔琳娜(Katharina Kippenberg)的信中,里尔克向她抱怨岛屿所出版的布克哈特(Georg Burckhardt)译本的准确性。(Bettina von Bomhard编:《里尔克与卡塔琳娜·基彭贝格书信集》,岛屿出版社1954年版,第191-192页)的确,当时已经有了由年轻有为的东方学家温各纳德(Arthur Ungnad)翻译、柏林大学圣经与古代东方学教授格勒斯曼(Hugo Gressman)评介的版本,与此相比,布克哈特的译文可谓舛讹百出,着实“削弱了这首流传了五千年的诗歌的真正力量”。这让里尔克震撼许久的巨大的力量,来源于人类对于死生之别的原初感受,而我们对这种感受并不陌生。
因死亡而产生的恐惧、疑惑、悲伤和思虑,伴随着人类命运的始终。这种感受始于千万年前的蒙昧年代,反映在原始和早期宗教、艺术和墓葬形式及其所反应出的观念世界中,并且在文明出现之后依然与我们如影随形。在叔本华看来,对于人类而言,死亡作为一种“邪恶”,必然“有一种治愈的方法,或者至少有一些补偿”,因此,“由于对死亡的认识所带来的反省,致使人类获得形而上学的见解,并由此得到一种慰藉……所有宗教和哲学体系,主要即为针对这种目的而发,以帮助人们培养反省的理性,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可以认为,古代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后文简写作《史诗》)就是疗愈死亡的“解毒剂”的原型之一。在近五千年前的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人借由他们的伟大统治者吉尔伽美什的传奇故事,思考并解释生死。一系列以吉尔伽美什为主角的诗歌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发展和演变,形成了里尔克和我们如今所读到的标准巴比伦语版《史诗》及其当代译本。

霍尔萨巴德遗址(Khorsabad)出土的新亚述时期的英雄雕像,被广泛称为“吉尔伽美什像”,现藏于卢浮宫,馆藏编号AO19862。

标准巴比伦语版《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第十一块泥板,其中记录了大洪水的情节,因此也被称作“洪水泥板”。出土于库云基克遗址(Kouyunjik),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馆藏编号K3375。
1853年,考古学家拉萨姆(Hormuzd Rassam)在公元前七世纪的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位于尼尼微的王室图书馆中发现了十二块泥板残片,即标准巴比伦语版(也称尼尼微版)的《史诗》。标准巴比伦语版《史诗》的第一块泥板始于对吉尔伽美什的赞美——“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他是伟大的乌鲁克城的城墙的建设者,是无可匹敌的英雄和战士,知道陆地之上和海洋之中万物的秘密。起初,为了遏制吉尔伽美什在乌鲁克的严苛统治,大神安努命令阿鲁鲁神创造了恩启都,一个生活在荒野中的力大无穷的野人。然而,在妓女莎姆哈特的诱惑下,恩启都离开荒野,来到了乌鲁克。紧接着,在第二块泥板中,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展开了较量,最终以吉尔伽美什的胜利告终,而恩启都与吉尔伽美什不打不相识,成为了他的亲密伙伴。在第三至第五块泥板中,他们二人一起出发,前往遥远的雪松林,杀死了雪松林的守护者洪巴巴,获得了雪松木,顺利地回到了乌鲁克。在第六块泥板中,返回乌鲁克的吉尔伽美什拒绝了女神伊什妲的求爱。伊什妲恼羞成怒,派天牛祸乱人间,而吉尔伽美什在恩启都的帮助下,杀死了天牛。第七块泥板的主要内容是恩启都对自己梦境中所看到的冥界的描述。根据其他版本可以知道,众神决定必须有人为天牛之死付出代价,所以恩启都必须死。恩启都因而“梦游冥府”,醒来就一病不起,不久后便一命呜呼。
恩启都死后,在第八块泥板中,吉尔伽美什以长篇的独白哀悼恩启都,并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仪式。随后,在第九和第十块泥板中,吉尔伽美什从恩启都的死感受到了对死亡的恐惧,进而踏上了追寻永生的旅程。他一路寻找远古时代大洪水的幸存者乌塔纳皮什提,想要询问他永生的奥秘。在吉尔伽美什渡过死水到达乌塔纳皮什提那里后,在第十一块泥板中,乌塔纳皮什提对他讲了大洪水的故事,并告诉了他在哪里可以找到能让人返老还童的药草。但是,吉尔伽美什好不容易得到的“返老还童草”被一条蛇偷吃了。最终,吉尔伽美什还是以一副凡人之躯回到了乌鲁克。第十二块泥板的内容并不承接前十一块泥板的情节,而是取材于另一篇以吉尔伽美什为主角的故事。在其中,恩启都死而复生,为了到冥界帮吉尔伽美什取回不慎掉落的木球,他再次下到冥府,几经周折后回到吉尔伽美什的身边,对他描述了各色人等在死后的下场。
尽管战胜了世间的一切、取得了无上的荣耀,却依然难逃一死。在恩启都的遗体前,吉尔伽美什这样问道:“我们曾协力同行,翻山越岭。我们捉住了天牛,并要了天牛的性命,我们铲除了洪巴巴,他居住在雪松林中。如今,是什么睡眠把你捉住?”在恩启都的葬礼之后,对死亡的悲伤与恐惧久久萦绕在他心头,“我将来也要死亡,我难道不会像恩启都一样?”吉尔伽美什走入山门,走过黑暗,渡过大海,来到了远古的乌塔纳皮什提面前,诉说了他的忧虑和恐惧。面对吉尔伽美什的诘问,乌塔纳皮什提向他解释了何为死亡:
人类就像芦苇丛中的芦苇,其后裔常被折断,
不论英俊男儿,还是美丽少女,
都难免夭折于华年。
谁也没有经历过死亡,
谁也没有见过死神的面。
谁也没有听到过死亡的声音,
然而人却可能猝然命丧九泉。(第216-217页)
在乌塔纳皮什提看来,死亡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生命如苇杆一般脆弱(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竟在巴比伦文学中找到了帕斯卡的踪迹),我们生存的时间并无定数。生命并不是在缓慢地消逝——因为死亡不可预知,随时都可能来临,它无关年龄,无关性别,无关美貌。在乌塔纳皮什提的回答中,死亡并不像吉尔伽美什描述恩启都之死那样具体——“直到他的鼻孔中爬出了蛆虫”;相反,在他的话语中,死亡是抽象的,超越了凡世的悲伤和痛苦。虽然死亡无色无声,但却有让人感到悲痛和恐惧的威力。“就像芦苇丛中的芦苇”,死亡的胜利不可避免,存在就是不断的死亡,正如乌塔纳皮什提接下来所说的:
在某个阶段,我们把房屋建造,
在某个阶段,我们搭窝建巢,
在某个阶段,兄弟分爨而居,
在某个阶段,仇恨遍布大地。
在某个阶段,洪水泛滥,河水四溢,
浮游在水上自在地游来飘去,
晒着太阳甚惬意。
顷刻间,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成子虚。(第217页)
乌塔纳皮什提口中的“在某个阶段”(阿卡德语原文:immatīma)并非只指存在于过去的某个时间段,而是一直在循环往复地发生,正如英国亚述学家乔治(Andrew George)的评注,“人类在世代交替之中永远长存”。从“发家致业”到“兄弟阋墙”——旧的家庭崩解,新的家庭建立,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依然是死亡。在古代世界的多数文化中,世代的交替都是以父辈的死亡作为关键的节点,而这死与生的轮替,即便是淹没世界的大洪水也无法改变。或者说,这是乌塔纳皮什提的比喻,将个体的生命放置在无限的时间之中。在漫长的时间之河上,人的一生短得就像一只蜉蝣,霎时间,死亡能够将阳光雨露化为子虚乌有。随后,乌塔纳皮什提终于向吉尔伽美什吐露了众神是如何决定了人的生与死:
被劫持与死亡,二者何其相像。
谁也画不出死亡是个啥模样。
死者不能在人间祈福祈祥。
大神阿努纳吉,聚在一起把事情商谈,
命运缔造者玛米图亦在他们中间,共同对人类命运作出了最后的决断。
他们确定了生与死,
却没有透露死亡期限。(第217页)
这是乌塔纳皮什提关于生与死的回答的最后一段。其中,他再次强调了死亡的不可见——它无声无息地出现,将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就像在战争中被掳掠到异国他乡、永生不能归还的俘虏一般,留给亲朋的只有无尽的苦痛悲哀。但是,流落他乡的人至少还能“在人间祈福祈祥”,求得神灵的怜悯和保佑,死去的人却只能在冥界踽踽独行,而这是由地上与地下的众神们“阿努纳吉”一同决定的。其实,乌塔纳皮什提的话中暗含玄机。他既强调人必有一死,这是诸神的裁断,也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他也反复提到,人们看不到死亡的模样,听不见它的声音,不知道它如何预知它的到来,更不知道如何逃出它的范围——因此,死亡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意识到乌塔纳皮什提对死亡本质的阐述中的悖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两河流域宗教和思想观念中死亡的意义。

乌鲁克遗址现状(2016年),位于现伊拉克境内塞马沃以东40公里处。蓝色告示板上的阿拉伯语标语写着“最早的书写从这里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
尽管在之后的情节中,吉尔伽美什得到了乌塔纳皮什提的怜悯,得知了如何获得能让人永生的药草,但这却是空欢喜一场。“返老还童草”被蛇吃掉,英雄最终一无所获,踏上漫漫归途,如同里尔克的诗里所说的,“似在走向庆典,却没有冠冕”。永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回到了乌鲁克的吉尔伽美什已经明白了何为死亡,转念去追求世俗上的光荣和不朽——例如他那坚不可摧的城墙。纵观《史诗》全篇,在追求永生的路上理解死亡——《史诗》中吉尔伽美什的经历,其实是上古时代的人们代代相传的情绪和经验积累的结果。弥漫在漫长历史之中的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沉淀在人们共同记忆的深处,在某一时刻进入口耳相传的传说,又被人们书写下来,成为我们所读到的泥板上的诗篇。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人类文明总是拥有许多遥远的相似处。幼发拉底河、黄河或是尼罗河畔的先民,共享着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在恐惧之外的思索与想象。或许直到永生成为现实,这种思虑会始终伴随着我们:“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哈姆雷特的生死独白之所以隽永,大概也因为它是久久缠绕在我们心头的悲情的回声。
对于死亡的恐惧只是《史诗》所涵盖的众多主题之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史诗》还关乎情感、智慧、成长与好奇心,关乎面对未知的勇气,也关乎对于命运的求索。《史诗》对各色神祇与凡人绘声绘色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古代两河流域人们的物质与精神世界。2021年初,在标准巴比伦语版《史诗》泥板出土一百六十八年后,以其为底本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汉语译注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知名亚述学家、北京大学拱玉书教授首次将《史诗》自楔形文字原文译为汉语。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智慧经典,经由译者的生花妙笔,在千年之后实现了与“日出之处”另一边的中国读者们的迟来的相逢。这首流传了五千年的诗歌的真正力量,即将迎来新的体验者——
请查看雪松木的泥版箱,
请打开青铜锁环,
请开启秘密之门,
请拿起青金石版,高声朗读
吉尔伽美什所经历的所有苦难。(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