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诗歌属于兰波,如西西弗一般无限充沛决意创作|此刻夜读
 2021-05-02
2021-05-02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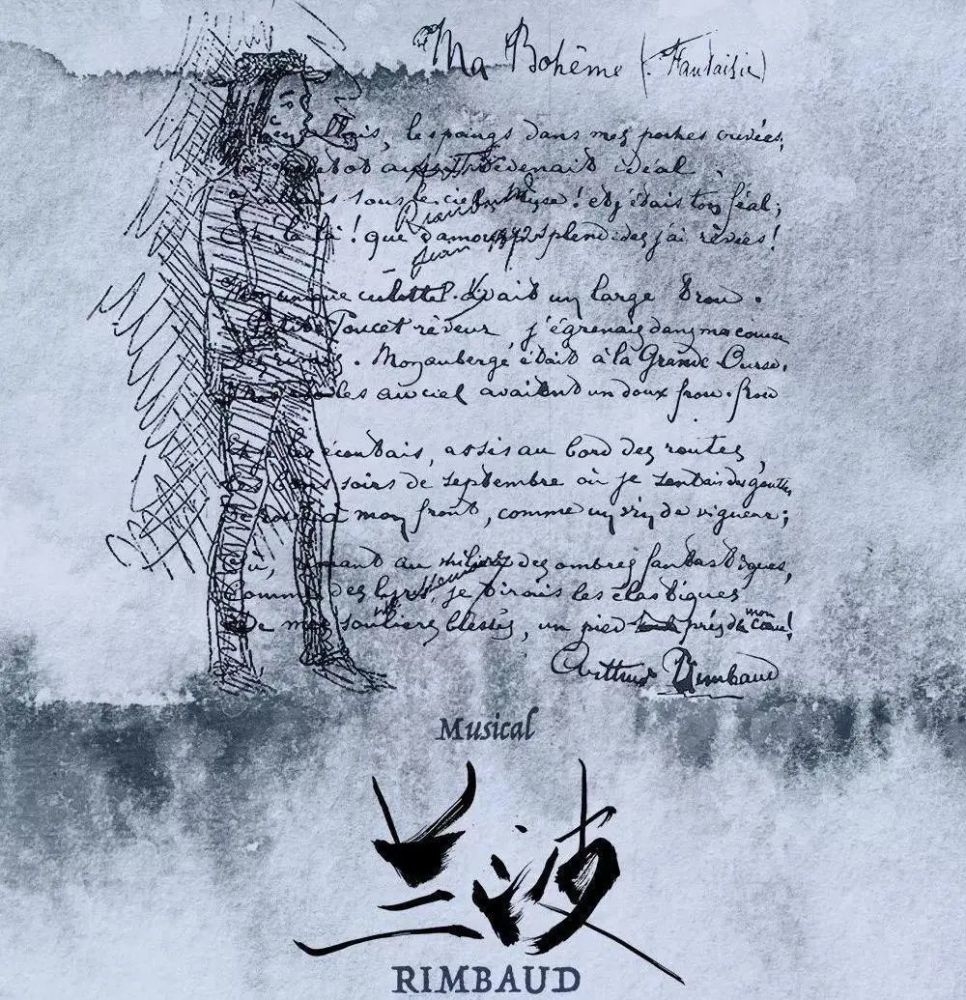
5月诗人
兰波
5月总是兰波精力最为充沛的月份,是决意与创作的月份。这是法国诗人伊夫·博纳富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作者)在研究兰波生平并为之写下评传时的感悟。他曾说,“我的很多成就都归功于兰波,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我产生本质的影响,只有他告诉我什么是生活、生活对我的期待、应该如何去改变生活。”
兰波的动人之处,在于他对“诗人何为”的不断质询的苦恼意识,对存在的可能性核心处的不可能性的持续探寻,在于他数次失败后的执着与生命的活力。而博纳富瓦将诗歌称作希望的运动,如同西西弗推动石头,诗人必须无限次地期许和开始。他们都是西西弗式诗人。
今天夜读,为大家带来伊夫·博纳富瓦眼中的同行兰波。

法国画家亨利·方丹·拉图尔的画作,左下角两位是兰波与魏尔伦
决意(节选)
5月总是兰波精力最为充沛的月份,是决意与创作的月份。猛然间他抖擞精神,直面紧迫的危险,似乎暂且避过一劫。这是“通灵人书信”里所描述的堪称典范的一场斗争。最为贫瘠、希望被剥夺得最为彻底的自由,此刻证实了它的价值、它的创造力,以及——就字面意思而言——它的诗意。


兰波照片、毕加索画的兰波
对兰波而言,最具威胁的危险是什么?显然是对自我的憎恶。“我坐着生活,”他写道,“好似落在理发师手里的天使。”他在一封致伊桑巴尔的信里写道:“我仍然玩世不恭地由人豢养。我把学校里的那些白痴发掘了出来:我献给他们所有我能用言语和行动造出来的愚蠢的、肮脏的、低劣的东西[……]。”因他无力战胜厄运,因他变成了写出《蹲》的着魔之人、写出《我的小情人》的惊弓之鸟,兰波勇敢地得出结论:他自身无比卑劣。“很明显,我向来属于低劣种族。”他坚信,自己属于奴隶与输家的种族。或许他也为巴黎公社的陷落所苦,因为公社与他相似:是被剥夺一切之人的反抗,始于战争带来的混乱,由一群理想即将幻灭的民众艰难地维系着,没有任何未来。长久以来,评论家们都愿意相信,兰波在公社斗争时曾奔赴巴黎,但他从未成行。1871年5月13日至15日的信件似乎证实了他并未离开夏尔维勒。不过,他的心始终与革命的城市中“黑色的陌生人”在一起。《让娜-玛丽》(Jeanne-Marie)或《巴黎重又聚起人群》(Paris se repeuple)中的段落足够证实这一点。他理解这场抗争。他想象自己站在它的熊熊烈火旁边,比起行动者,他更像是通晓其深层意义的见证者:“真是幸运,我看到漫天都是烟与火的汪洋;左右前后,所有财富珍奇如同千万道闪电熊熊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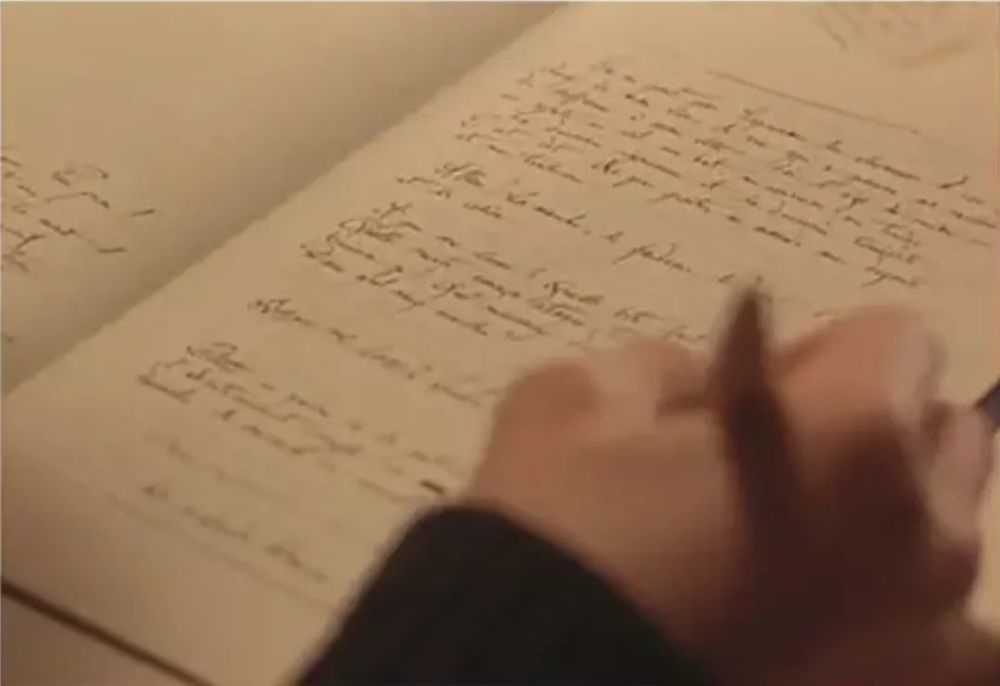
兰波传记片《心之全蚀》剧照
是的,5月初,随着公社日渐式微,他几近绝望。在他所有的诗歌中,《被盗的心》(Le Coeur volé)——确实,与《耻辱》一道——最是危险,最是黑暗。一颗被唾沫和扔下的“残羹”玷污的心,这一隐喻表达了长久以来他因爱的缺失而蒙受的苦难。在此之上,他又增添了彻底的无力感:“怎么办呢,噢,被盗的心?”在这行诗里,兰波唯一的求援方式似乎消失了:对诗歌,他几近丧失信心。他不早就对诗歌怀抱起了爱恨交织的混杂情绪吗?诗歌并非完满的纯粹,没有实际的效用,这不早就让他带着咄咄逼人的羞耻心,在杜埃对诗歌大加嘲讽了吗?每一天,他都对伊桑巴尔重复十遍蒙田(Montaigne)那句模棱两可的名言:“诗人坐在缪斯们的三角凳上,狂热地倾倒所有涌到他嘴边的东西。”这里所流露的疑心,与新诗中的嘲弄无甚差别。它们都试图揭露诗的虚荣,诗声称自己用美对抗不幸、用现实对抗匮乏,可事实上,它不过是令人作呕的情感发泄。《圣袍下的心》(Un coeur sous une soutane)也许创作或修改于同一时期,因为这篇短文顶着相似的标题,说着几乎一样的内容;在滑稽的修士与愚笨的丑妇身上,展示出了兰波自身的一小部分;它嘲笑诗歌不过是关于恶臭之物的含糊可憎之语,而这恶臭之物注定比“里拉琴一般抒情”的诗句与虚妄的希望更长久。
“这首诗不是没有任何意思的。”关于《被盗的心》,兰波在5月13日写给伊桑巴尔的信里这么写道。他的传记作者们试图用一些逸事,用兰波醉生梦死的放荡经历来解释这首诗。但在更深的层面,《被盗的心》所说的,是在某一时刻差点吞没兰波全部存在的自我恐惧。一种绝对的恶心感让兰波脱离之前所有的野心、所有的计划、所有的理想。多么可怖的状态啊,除了自我矛盾与死亡之外,没有任何出口。
兰波选择了自我矛盾。5月13日和5月15日,两封决绝、狂热、蛮横的信被分别寄给了伊桑巴尔与德梅尼。此二人绝不会理解通灵人(Voyant)的哲学。
或许,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纯然形而上的决意,我们是否必须关注兰波另一面深层的童年,即他儿时阅读的书籍,以及受到的影响?

兰波传记片《心之全蚀》剧照
这些接触中,最早期也最重要的,是针对波德莱尔的阅读。也许,兰波从1871年起便认识了波德莱尔——通过戈蒂耶作序的1868年版诗集——因为我们可以从《巴黎重又聚起人群》《恶》《仁爱修女》,甚至《让娜-玛丽之手》中找出《恶之花》影响的初痕。事实上,兰波主要延续了《祝福》(Bénédiction)与《圣彼得的否认》(Le Reniement de Saint Pierre)中的韵律和意象。其中的精妙诗句描述诗人母亲的高声咒骂、诗人长久的顽抗、与女人相伴时的不幸,以及最终从苦难中获得的至纯荣耀。读起它来,兰波怎能不受触动,怎能不为它的呼喊着迷?
“呀!我宁可生一团蜿蜒的毒蛇,
也不情愿养一个这样的妖相!
我永远诅咒那霎时狂欢之夜,
那晚我肚里怀孕了我的孽障!
[……]
可是,受了天使的冥冥的荫庇,
那被抛弃的婴儿陶醉着阳光,
[……]
我知道痛苦是人的唯一贵显
永远超脱地狱和人间的侵害,
[……]”
兰波必定在顷刻间迷上了这美好的信仰;纵使无法全然信服——他从不能彻底完成信仰的转变——至少,为了改变阴沉的视域,他愿意相信这信仰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恶之花》里,处处有着对不断变幻之存在的直观,铅石可化为黄金,精神可回炉重造。在这个“行动并非梦想的姐妹”的世界,一种行动之诗的理念形成了,它兼具解析的智慧与神秘的化学。兰波追随波德莱尔,很快踏上了这条道路。不必怀疑,正因他读了《恶之花》,他才能写出《仁爱修女》和《初领圣体》那令人赞叹的结尾。没有波德莱尔,兰波不可能这么早便掌握如此宏伟、如此坚实的灵魂科学;没有他,兰波不可能获得他仅有的些许自信,让他猛然懂得,作出论断无需仇恨,只需怜悯。纵使他的思想一向消极,这怜悯却有一丝爱的意味。这两首诗是兰波首度显出成熟模样的作品,从中,我们隐约瞧见了一种或可称为“胜利”的转变:他从内心里“残忍的怀疑主义”,进入一种斯多葛式的平静中。然而,他们能继续诉说的,唯有孤独与流亡,因为两人的创作均以女人的境况为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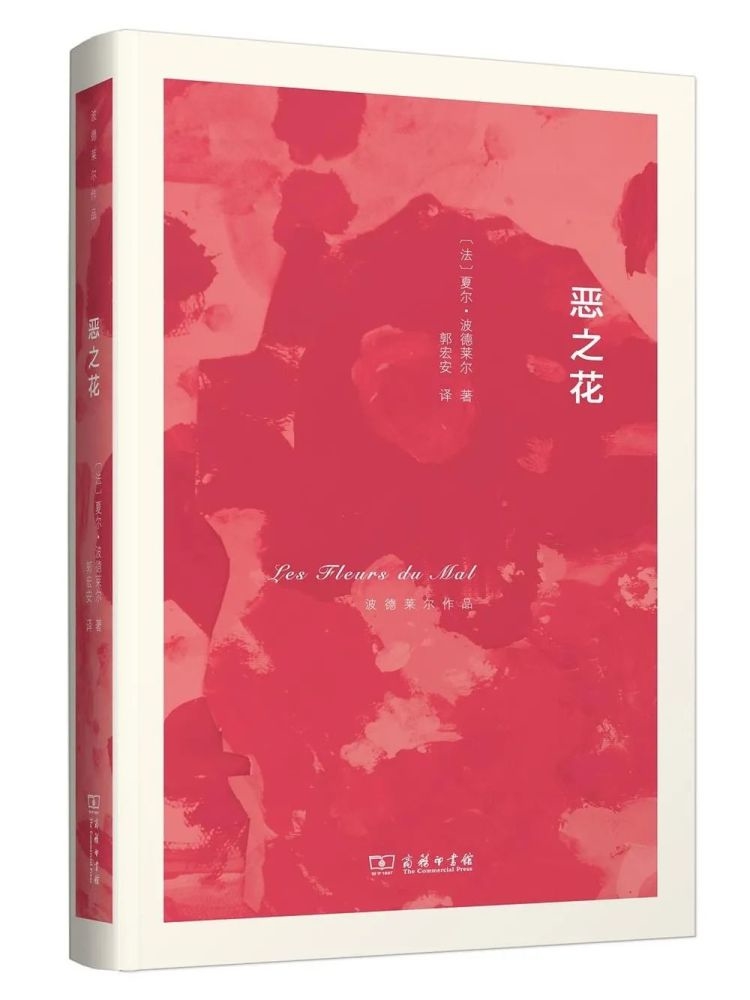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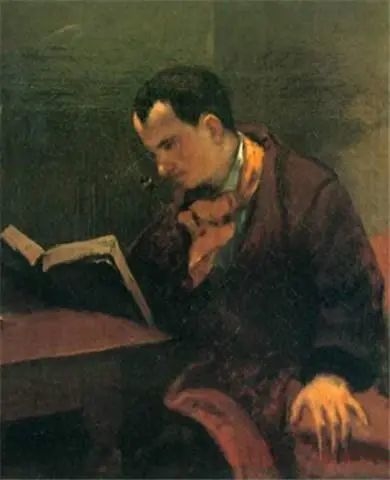
波德莱尔《恶之花》
是波德莱尔刚刚教会了兰波诗的责任。不过,《初领圣体》与《露台》(Le Balcon)之间、与波德莱尔表达爱意的所有诗歌之间,隔着多么神秘的距离啊!这距离所揭示的,并非两位诗人或多或少纯净的心灵,而是他们最初的苦难。波德莱尔从不曾像兰波一样无助!
那熊熊的炉火照耀着的黄昏,
露台上的黄昏,蒙着薄红的雾,
你的心多么甜!你的胸多么温!
我们常常说许多不朽的话语
那熊熊的炉火照耀着的黄昏!
我坚信如下判断:波德莱尔所尝试的蜕变,与兰波本来渴望的蜕变,无疑通往同一个终点,然而,即便掌握同样的炼金术,他们却拥有不同的原料,这迫使新的诗人远离《恶之花》指明的道路。波德莱尔想战胜虚无。人世间,存在屈服于碎片化、分散化和死亡的堕落;他明白,为有限的事物与速朽的个体献身,是关键性转化的第一步,转瞬之间可诞生完满的存在。而这献身正是爱,是幸运赐予他的爱。从前,在幸福的儿时所住的“白房子”里,波德莱尔曾被这样教导:相互的爱是存在的。兰波没有接收过这最基本的馈赠。因此,他试图戒除爱,或者在诗歌之路上重新发现它。无论如何,兰波都身处幸福之外,而我们能感到,这稀罕的幸福在波德莱尔那里并未全然消失,它虽然衰弱,却依旧灼热。波德莱尔有理由把爱称作“披着金色的天使”,因为他与天使一样履行着爱;兰波却身不由己,只识得路西法的苦恼。在能够重新创造存在以前,他必须试着重新创造爱情。
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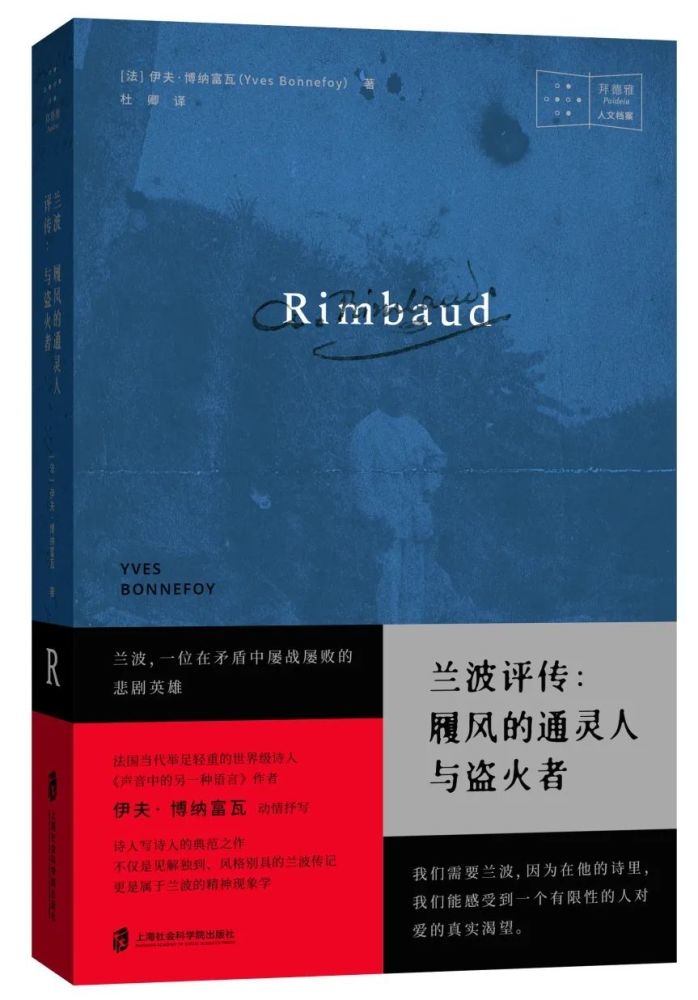
《兰波评传: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
[法]伊夫·博纳富瓦 / 著
杜卿 / 译
拜德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年4月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出版书影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每天准时与我们遇见的小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