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故事引人瞩目:由《柳青传》改编的电影《柳青》5月21日全国上映


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
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柳青
一位伟大的作家
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
十四岁时,油灯下,他吃力地啃《共产党宣言》;“一二·九”前后日夜奔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以后为办救亡刊物累得大口大口吐血;1939 年,到敌后战场跟部队上前线打仗,对常人已经够苦,对他更是苦上加苦,冷天里 冰河,夜夜行军,病体几乎支离破碎。他忘我地干,竭尽自己的力量,他自信参加革命够彻底了。而现在,他的自信心动摇了,因为他想到了离开这里,怕黄土埋瘦骨,文学事业将与身俱灭,他不能想象那种现实。他剖析自己深层模糊的意识:自己带着极大的个人抱负走进革命队伍,不愿做一个无声无息的人,以前的苦和个人愿望不悖,况且苦也是暂时的,咬咬牙就能过去,现在虽说也是暂时的,可暂时到何时?对于生活,如果总是划皮而过,文学事业的进取和希望何在?文学事业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是无止境的!咬牙岂能咬一辈子。

1932年11月,柳青(中排右一)在榆林六中与同学合影
他不仅带着强烈的创作愿望,同时也下过决心要努力工作,改造自己。这才出阵,就败阵而归,他自问:人生何为?
他握着拳,轻轻地敲着炕沿,咽下一口唾沫,好像在吞钢咽铁。不要说磨掉一层皮,就是磨掉一身肉,还是要干下去!此时,思想的改变,对自己仍很重要,对革命、对文学都非过这一关不可,否则,只是为了个人的打算,终将会使自己设法绕过困难,摆脱痛苦。(以上文字引自刘可风《柳青传》)

电影《柳青》宣传照
柳青是建国后三十年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业史》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巨大变革,他身体力行的关注民生、关注现实的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电影根据柳青女儿刘可风的著作《柳青传》改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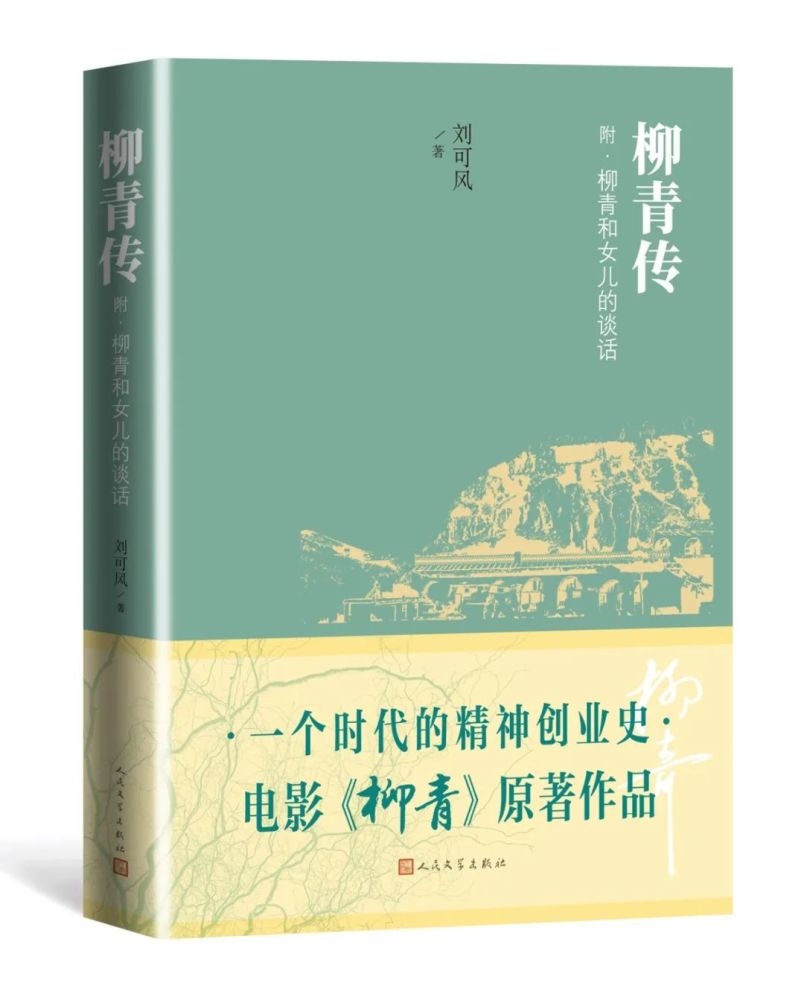
《柳青传》 刘可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柳青长女刘可风,从1970年到1978年陪伴柳青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九年,后又走访历史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自2000年起全力写作本书,分上下两部分呈现一个不同于文学史经典叙述的丰富的柳青;并附有柳青晚年极富价值的谈话,涉及《创业史》未完成部分的构思和对时代的沉思。全书为我们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

柳青和女儿刘可风及长子刘长风
柳青最后的日子(节选)
文丨刘可风
1978年春节前后,父亲第三次住院,身体已经很虚弱,一个月以后又感染了绿脓杆菌,有时精神委靡。一天,他强撑着说:“你回家把我的文字资料和手稿全部拿来。”我取回东西,他一份一份给我交代处理方式,微弱声中的一句句,都是让亲人痛彻肺腑的话,我怎么也不愿意他说下去:“爸爸,你肯定会好的,多少鬼门关你不是都过来了吗?”
经过不停的输液消炎,情况渐渐好转。空闲了,我就翻看拿来的资料,一份他复写的、留底的“交待材料”有一段话:“1956年,在一次讨论提级的会上,工作人员汇报说统战部提出民主人士郑伯奇(作协副主席)的级别低了,我说给我的一级不要提了,给他提一级,让他和我平级。”
我从来没问过父亲的行政级别。问他:“为什么这种事情也是你的罪状?”
他说:“他们说我招降纳叛,包庇‘反共老手’郑伯奇,证据就是我把我的一级让给了他。”
“你的级别……?”
“解放后一共提过两次级,按政策像我这样,没犯过错误的都提一级,我两次都让了,所以,我一直是刚解放定的十级。”

1961年,柳青在中宫寺家中接待来访读者
“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吗?”
“别的没啥,就是看文件受到级别的限制。”
我说:“《创业史》第一部稿费你给了公社,第二部你预支一部分给大队拉了电线,弄得家里生活总是这样拮据。”
我不是抱怨,只是想了解父亲是怎么想的。

父亲并没有多想,马上就说:“要想塑造英雄,首先要塑造自己,要写英雄,首先要学习英雄。我决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具有双重人格。”
父亲又说:“日常医疗费我从来没报过,稿纸也没在作协领过,一次就买了十元钱的,现在还没有用完。”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正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稿酬大幅降低。困难过后,又补发了,出版社的同志告诉我,一个领导说反正给他,他也要捐献,就不用补了。”
父亲说:“这种事情我从来不过问。”
不过,他也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是给我,我可以给本地区再办点事。”

柳青和皇甫村农民在一起
我说:“你怎么弄得一点积蓄也没有呢?”
父亲说:“《铜墙铁壁》有些稿费,都用在那个院子上了。”
虽然“文革”后皇甫村半坡上那座幽静的村舍已荡然无存,他仍然念念不忘抛洒了无数汗水,难以割舍的故地。说起这些事他的感情十分复杂:
“那所院子军区做过羊圈后,多年空弃,很破旧,建筑年代无人知晓,也无从考证。我初来时还有块清朝嘉庆年间重修的残缺石碑,可见年代久远。1954年搬进来,1955年第一次大修,才两年就出了问题。开始我想小修小补,不影响正常生活就算了,一动工,这里也不行,那里也是问题,改变计划,干脆好好修一下,这辈子再也不在这事上费心思,所以,‘小工程’变成了‘大工程’。谁料,几年以后又出问题,共大修四次,把那些稿费全用完了。”

“我怎么能想到,我的阵地,我精心维护,打算将来寿终老死的院落会……”他灰突突的脸上很是伤感。
最后,父亲对我说:“爸爸一毛钱也不给你们留,你们首先要能养活自己,才谈得上对社会做贡献。”
在西安的治疗成效甚微,听取了人们的劝告,我们把无限期望寄托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1978年5月11日,是父亲离陕去京治病的日子。
清晨,温和的阳光,寂静的街道,缓缓而行的汽车,父亲目视窗外,心静如水。父亲以往出行,来不接去不送。家人外人都一样。这次有人表示要到车站送行。父亲再三劝告:“大家都忙,不必浪费这些时间。”
父亲说:“我不喜欢客套。”待人接物父亲有时像农民,简单直率,这可不是他的优点。他每次从乡下到作协,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人们也习惯,从不迎来送往,“文革”中他回皇甫村,久别的农民和干部特别热情,告辞时要送他出门,他两手一拦:“到此为止,都忙去吧!”

父亲以为,这次也一如既往,不料,一进站台,眼前已经聚集了一片等待送行的人,而且越来越多,除了作协,还有剧协、音协和长安县的人们。朋友们一片深情的目光,许多简短的祝愿和嘱咐。父亲本来是个极富感情、容易激动的人,他用眼神和表情回敬人们的离情别意,努力使自己不要过分激动。就在登车前的一刻,剧协的马良田一把搂住父亲的肩膀,动容地说:“我们都对你特别有感情,希望你看好病早日归来!”大概是想让这惜别的气氛不要太沉重,父亲故显轻松地说:“对呀!民族大团结,回汉一家亲嘛。”马良田是回民。
上车后,在情深似海的目光里,父亲终于抑制不住自己,难以平静的面部泛起罕见的红光,他用尽气力,两手扒住玻璃窗,大声向告别的人们倾吐心声:“我离不开陕西,离不开大家,我一定会回来!”
阳光透过玻璃,照着他眼眶中涌出的泪水,熠熠闪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