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巴以两国,如果真的无法相爱,就做邻居吧
 2021-05-19
2021-05-19

以巴冲突持续。至今已造成200多人丧生,各国都敦促双方停火。
要了解以巴地区的争议可追溯至1948年,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第二天,以埃及、约旦、叙利亚等国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向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自此,双方的冲突从未休止。联合国调停无效,各方势力介入,硝烟弥漫,战争不断,仇恨遍布整块中东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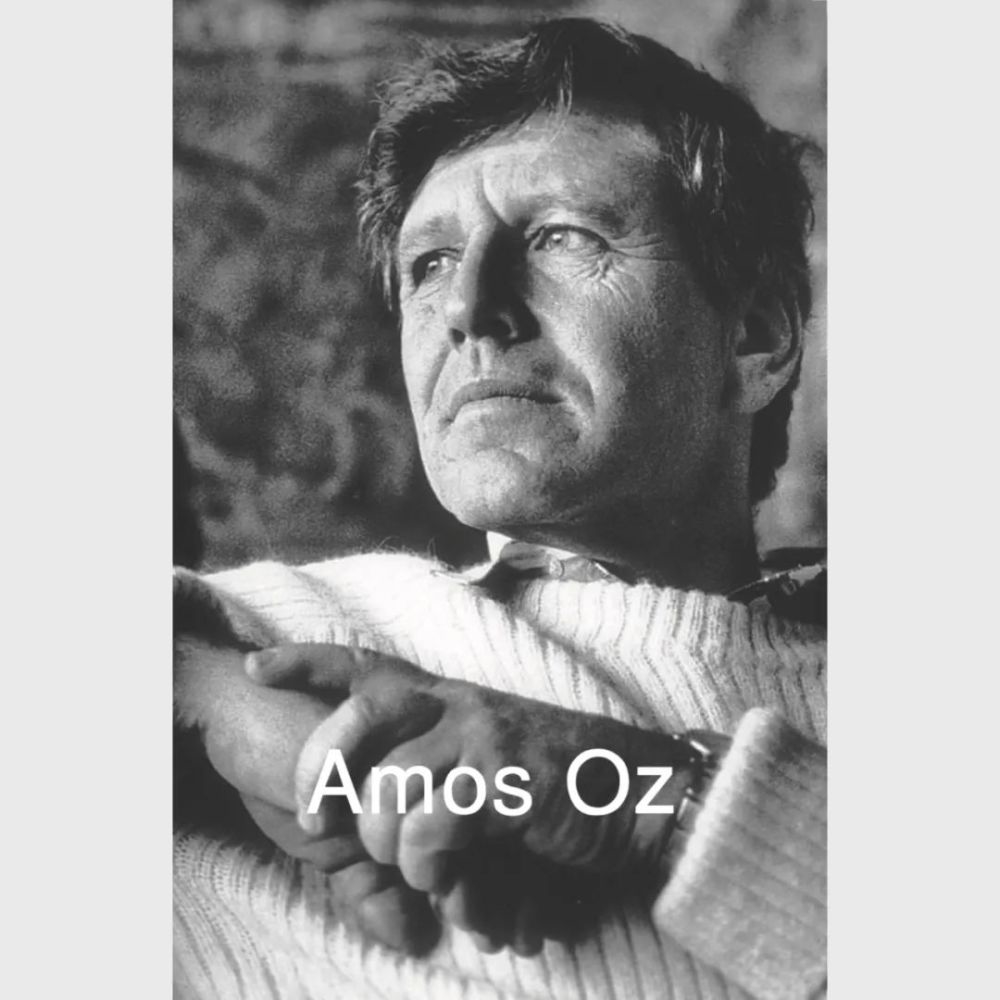
1939年,阿摩司·奥兹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父母分别来自苏联的敖德萨(今属乌克兰)和波兰的罗夫诺,他们怀着复国主义梦想去到巴勒斯坦——这座没有河流,到处布满石头的山城。小奥兹的童年里,爆炸、宵禁、停电和断水司空见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时不时就大动干戈。在奥兹心中,耶路撒冷是一个“倒地受伤的女人”,就像他的母亲,敏感、神秘、情绪化。(柏琳《双重时间》)
作家奥兹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人们说,“理解奥兹,千万不能忽略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他的女儿范妮娅认为奥兹既是作家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用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政论。”这些年,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将奥兹视作“叛国者”,他居然把自己的书带到巴勒斯坦去!奥兹说:“我要充满荣耀感地戴着这顶‘叛国者’的帽子,这顶帽子提醒我,要相信正义和真理,要同时给予巴以两个民族说话的权利。”
在两个民族水火不容的况下,将如何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和平协议?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独立记者柏琳对奥兹及其女儿范妮娅的专访,出自《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曾有个巴勒斯坦的政治家身陷囹圄,读了《爱与黑暗的故事》,写信给奥兹:也许应该由您来读一读我们(巴勒斯坦)的历史,而我应该读一读以色列的历史。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

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秘密
柏琳 文
本文节选自《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年4月

柏琳
《新京报·书评周刊》原资深记者,曾采写120多位国内外文化人物。现为独立记者,青年写作者。2018年入选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水手计划,正在进行有关南部斯拉夫地域的非虚构写作。作品发表于《读书》《单读》《花城》等。图为柏琳在周末郎园图书市集上做新书签售的留影
在战乱和恐怖袭击不断出现在以色列人民生活中的今天,和平的步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迟缓。擅长破解家庭之谜的奥兹,依然会把巴以冲突理解成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他说,如果真的无法相爱,就做邻居吧。
▍“巴以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以色列屯垦区正指责双方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图/路透社
柏琳:就在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悲哀地表示“巴以冲突”和解遥遥无期,而且可能情况越来越糟糕。你觉得,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的痛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依然无法达成和解?
奥兹:我可以用一个词回答你:法西斯。双方都是这样的状态,他们需要所有的支持都在自己这里,自己百分百正确,他者百分百错误。但是我一直说,妥协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方法。
我是个懂得妥协的男人,不然我也不会和同一个女人保持五十六年的婚姻。妥协从来都不快乐,没有人会觉得妥协容易,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成熟。现在巴以冲突看似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这么狭小,小到中国人都无法想象。从特拉维夫开车到约旦不到一个小时,从耶路撒冷开车到巴勒斯坦地区只需要二十多分钟。这样小的一块土地,它是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也应该是巴勒斯坦人的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和平共处,融为一体呢?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一个欢乐的家庭呢?答案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他们也不快乐,他们更不是“一家子”,他们是“不快乐的两个家庭”。不同的语言、历史、宗教信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这所小房子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单元,比邻而居。
我们需要把这所房子分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部分,以色列人得到A卧室,巴勒斯坦人得到B卧室,如果可能,厨房和客厅可以有一部分共享空间。如果不能做情人,就做邻居吧,希望有一天彼此都能邀请对方到家里来喝咖啡。我说得容易,其实很难,但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因为以色列人无处可去,巴勒斯坦人也是。在欧洲,不就是有个很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吗?他们分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相安无事,巴以问题应该以此为鉴。

阻隔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隔离墙
柏琳:我想起了一本书,美国作家乔纳森·威尔森写的《巴勒斯坦之恋》,用一种新视角展现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全书一个核心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总把自己看作历史的受害者,他们也做了很多伤害阿拉伯人的事情。你看过这本书吗?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奥兹:没看过这本书,但是听你说后,我准备回去看。人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这是普遍的人性。犹太人是受害者,女性是受害者,黑人是受害者,第三世界国家是受害者......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场“比赛谁比谁受伤害更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每个人都在说,“我比你更受伤害”。
即使在家庭内部,当婚姻触礁,兄弟阋墙,人们也总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把对方当成加害者,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人也喜欢把自己当成无辜受害方,但双方都很幼稚。
我真的认为,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从来不该判决哪一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双方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侵略者。在以色列内部也形形色色,正统犹太教徒,犹太教改革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使是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也不是一类人,而是好几类人的统称,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内部都是复国主义者,有的是资本家,有的信仰社会主义,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甚至是法西斯,我并不是喜欢这个家族里所有的成员,而有些成员也以我为耻辱,这很正常,大家庭内部,这种矛盾司空见惯。但我们必须有一个共识: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哪怕这个家园小得不能再小。

柏琳《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范妮娅回忆父亲奥兹:他用“讲故事”治疗民族伤痛
柏琳:作为他的长女,家里第一个孩子,意义总是有点不同。父亲和你的相处方式是否有特别之处?父亲以什么形象停留在你的记忆里?
范妮娅:我出生时,父亲才二十一岁。在他十二岁那年,他的母亲就自杀身亡了,留下这个孤单的独生子。他很早就开始揣摩死亡的秘密。我记得,我四岁时开始对死亡有了懵懂的认知,同时也产生了恐惧。我去问父亲:爸爸,我害怕死,怎么办?父亲抱起我,对我说:范妮娅,不要担心,等你长大时,爸爸就会发明一种让人不会死的神奇事物。
后来我长大了,觉得父亲当年的回答太不可思议:一个父亲怎么可以许诺孩子以不死的诺言?直到去年父亲过世,我五十八岁,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爸爸是对的,他没有对我撒谎。他的确发明了“不死”的事物——词语。他的作品,他留给孩子们的话,留给全世界读者的言语。对我而言,他真的是不死的。
柏琳:奥兹曾定义自己是一个“在旧式犹太人和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的灵魂”,而他与你合著的学术随笔集《犹太人与词语》这本书也大量论及现代犹太人在正统宗教性和世俗性之间的徘徊,作为新一代犹太人知识分子,你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
范妮娅:我首先是一个人本主义者,然后是一个以色列犹太人。何为“身份”?这个英语中的“身份”,来源于拉丁语,类似于“它”,是一个较低级的词根,表示一种出身、本能的意思。如果“身份”只能关涉这个意义,那么我们就是我们身份的囚徒。“我出生在犹太家庭,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最好的”,这种说法是民族主义的,是可怜的。
我父亲有一个叔叔克劳斯纳(他也出现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的家族名为“克劳斯纳”),这位克劳斯纳叔叔学识渊博,是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以色列知名学者。他在耶路撒冷的家的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克劳斯纳家族的“座右铭”:犹太主义,人本主义。他说他无法把这两个词分开。我们是犹太人,也是人本主义者。这是我们的家族遗产。
谈及身份,我愿意做“加法”。作为以色列犹太人,我背负着犹太人的历史,但同时也有全新的东西。“身份”必须是新与旧的“协商”。我是犹太人,我也是女人,是母亲,是热爱动物的人......身份必须是多样的。
柏琳:在奥兹的代表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以及其他作品中,有一个重要主题和如今的世界形势息息相关——犹太人对欧洲的“失望的爱”。联系到如今以色列国内政治“向右”形势,越来越无解的巴以冲突,欧洲乃至全球的极右民粹主义趋势,世界似乎正在朝着奥兹担忧的方向运转。作为一个深谙西方文化的犹太历史学家,你如何看待这种世界局势?
范妮娅:过去七十多年里,欧洲和美国都拥有战胜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世界人民似乎有种幻觉——我们已经永久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也好,罗斯福也好,似乎给那一代人强制注射了某种麻醉剂。七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人没有被注射过,新纳粹、狂热的新民族主义战争、极端的右翼势力开始升温......野兽在苏醒。人们好像忘记了从前疯狂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灾难。
关于这个问题,我父亲有一个说法,他想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无论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分子,还是以色列民族主义分子,他想对这些人说:对于那些已经失落在时间中的东西,请不要再去空间中寻找。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曾经的荣耀,再也不会回来。
就像一个男子在二十年前有一个爱人,二十年后的现在,他不能对这个女人说: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在时间中已经失落的东西,只能永恒地消失。为了逝去的爱情或者曾经荣耀的国度,我们可以写诗,写一本小说,想念它,纪念它,但我们永不复回时间的往昔河流。
我同意父亲的观点。看看今日特朗普的美国吧,其实事情很简单——美国人希望回到某种“黄金时代”,那时美国没有那么多移民,所有人都说一种语言,秉持相同的价值观......但我恐怕要说,这只是某种对过去的“幻想”。撇开这种“愿景”,看看今天,无论欧美,放眼望去都是“新人”,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彼此融合,这就是未来,我们应该学会和这种新的“身份”对话,和未来对话。
柏琳:那么,作为在犹太世界深受爱戴但也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对于你父亲的去世,以色列国内有什么反应?
范妮娅:一直以来,我父亲既是作家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用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政论。关于巴以冲突,他曾秉持中立的观点,但最近几年他有了改变。由于越来越狂热的新民族主义在以色列乃至在全球的兴起,他对我说:“范妮娅,我们要加快脚步,我们要快点说,快点写,快点告诉这个世界,警惕那些危险的人,他们要带给我们灾难。”
这些年,国内右翼势力说我父亲是“叛国者”,他居然把自己的书带到巴勒斯坦去!父亲说:“我要充满荣耀感地戴着这顶“叛国者”的帽子,这顶帽子提醒我,要相信正义和真理,要同时给予巴以两个民族说话的权利。”
曾有个巴勒斯坦的政治家身陷囹圄,读了《爱与黑暗的故事》,写信给父亲:也许应该由您来读一读我们(巴勒斯坦)的历史,而我应该读一读以色列的历史。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得知我父亲的死后,这个政治家泣不成声。
这就是我父亲在以色列的角色。他始终是那个坚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治疗”民族伤痛的人。不仅是巴以冲突,而是放之四海的问题。他说,请让我们讲述彼此的故事,走入幽深的历史隧道中,请让我们深深地了解彼此,请让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治疗狂热。
相关书籍
END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