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的“时尚圈”|中国不如欧洲“勤劳”?

授权转自公号:理想国imaginist
哲学园鸣谢

英剧《唐顿庄园》
我们的日常穿着、实用品、赏玩品,可归之为“时尚”。
四九以后,好长一段时间,盛行“绿军装”。由日常穿着,可窥得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开放程度。
就所见历史,如果一个国家高度集权化、政治化,平民的衣服穿着、表情,随之变得单一。反过来,如果时尚消费丰富多样,又与权力的关系如何呢?
可以说,政府权力集中度、文化保守度与时尚消费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是读《大分流》带来的其中一个思考。
今天分享三四百年前的“时尚圈”,内容来自畅销20年的经典力作《大分流》(全新译本)。这本书的作者彭慕兰,是两届费正清奖得主、经济史大家。
在他笔下,“时尚消费”的鲜活,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如此“亲密又复杂”。
清代平民百姓衣着式样的改变,似乎比明朝时少了许多,也比18世纪晚期欧洲少了许多。
清朝上流文化的道德主义鼓励这些女人比明朝时更加不抛头露面,鼓励她们与城市风月女子更加划清界限。
对许多史学家来说,乾隆这个心态被认为与好奇、贪婪和充满活力的“西方心态”背道而驰。
很难不去把中国的白银需求,视为和西方对瓷器、茶叶等物的需求一样,是“主动”打造全球经济的强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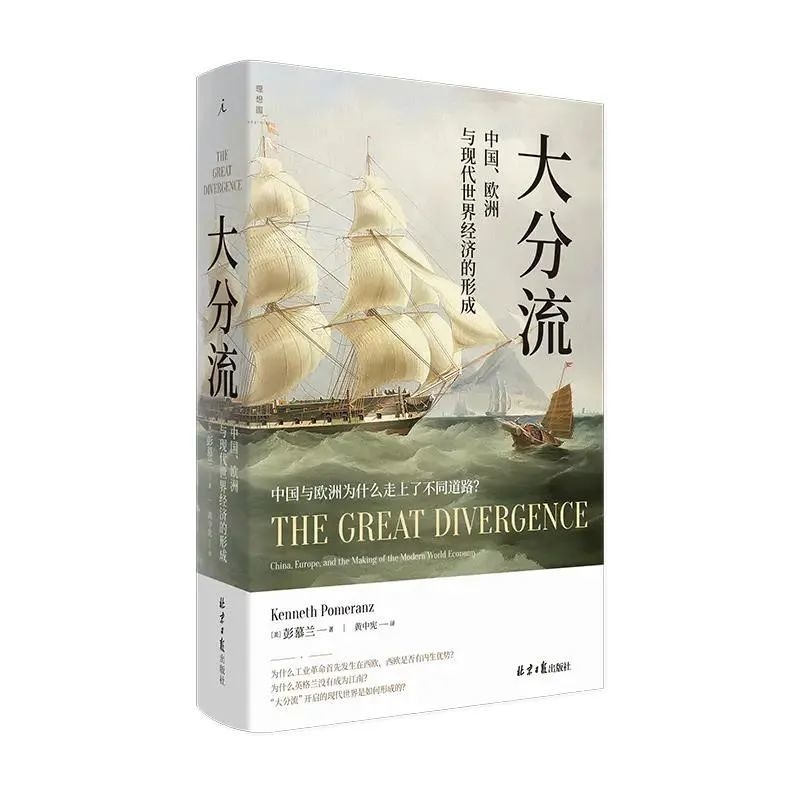
舶来品与时尚的速度
选自《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01
清朝的时尚与重振中央政府权力
但即使西欧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积累实物上非常类似,却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异之处。欧洲消费的成长和转型,似乎在实际所得增长和下滑时期都未停下脚步,更在18世纪中期加快脚步。比较中国、日本境内的趋势,都未发现这种方兴未艾的加速现象。
例如,柯律格指出新兴的清朝一旦底定天下(约1683年)且开始招引天下精英出任明末许多精英所不愿出任的公职时,以奢侈性消费为题的新出版品随即剧减。他表示,由于较古老的等级、身份确立方式重获认可,“对东西的谈论变得多余”,“消费社会”的发展还未及取得“临界质量”即戛然而止。

柯律格
18世纪中国文献对奢侈的抱怨,至少和16、17世纪中国文献的抱怨一样多,但小说则让我们看到更为多样的廉价小玩意儿。有人认为,如果我们手上有过去人所拥有物品的目录,18世纪目录所列的品项,平均来讲会比16世纪或17世纪目录所列的品项来得多(而诚如先前已提过的,欧洲的情况并非必然如此)。
不过,品味指南方面的新出版品减少,很可能意味着新商品和新式样成为有心跻身社会更高层者所必需之物的速度变慢。沈从文的那本中国服饰史巨著,也显示这样的可能:尽管晚明衣着、首饰式样上的许多创新,在清初继续从社会顶层往下散播,且清朝同时下令大改官员的衣着式样,但清代平民百姓衣着式样的改变,似乎比明朝时少了许多,也比18世纪晚期欧洲少了许多。
另一方面,欧洲时尚改变的脚步愈来愈快,尤以衣着方面为然。对欧洲(与北美)遗产目录的研究,几乎个个表明消费品在遗产总价值里所占的比重随着时日推移而下跌;而在许多研究里,就连这类物品的绝对价值也是下跌的。确凿的证据显示,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消费需求渐增且人们所拥有的物品更为多样,而若要使前述研究结果与这些铁证并行不悖,似乎就只能推断,有许多种类的消费品正以相当快的速度被当时的人抛弃。因此,一个人能在一生中购买更多的东西,未必意味着其在人生的哪个时刻就拥有较多的物品(例如在遗产目录里列出的品项)。

英剧《名姝》
物品的寿命为何会变短?有些物品,例如织物,变得(相对较)便宜,使它们更易遭替换。就其他类物品来说,新物可能比旧物更不耐用(例如玻璃和瓷器大概比锡镴、锡或木质餐具更常破掉),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但时人对时尚更加在意的心态,似乎也起了某种作用。毕竟,中断战事以让“木头小姐”(wooden mademoiselle)安然通过这样的事,就发生在18世纪。(“木头小姐”是穿着下一季巴黎时装,从圣彼得堡到波士顿等地巡回展出的人体模型)。
时尚更加风靡的这个现象,很可能意味着欧洲每年的奢侈性商品的需求比中国或日本的需求增长更快,尽管我们暂时假设这些物品的目录(和对它们的态度)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改变。
这意味着比较欧洲、东亚两地在拥有物上的支出水平之后,可能会发现两地此类水平的差距比拥有物本身的差距来得大;而那反过来局限了我们所能做的推断。为了达成我们当下的目标,也就是探索欧洲人是否可能每年购买较多物品,从而使欧洲的“勤劳革命”比其他地方走得更远,我们根据购买速度做比较就是可取之举;但要说这样的模式表明“较高的生活水平”,并说明为何此说成立,就难上许多。
比较能通过这样模式来说明的,反倒是品味上或可取得的物质上的差异。我们既已就糖、茶叶和织物做了比较,就该谨记我们并不确定欧洲每年在非必需品的花费上,是不是真的比较多。但倘若欧洲人真的和中国人或日本人一样穷,且在这方面的花费也的确比较多,那就值得思考这一由社会因素导致的“贬值”,是否就是使欧洲消费在历经经济周期、相对价格和政治稳定等方面的改变后,仍异常强劲成长的因素。
为什么在仍堪用的物品遭遗弃(或遭闲置)这件事情上会有快与慢的差异?比较社会史提供了一些线索。对中国、日本和西欧来说,17世纪都是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但17世纪中叶分别在中国、日本掌权的清朝、德川政权,却能在18世纪时让当地社会享受到大部分西欧所不能及的稳定。当然,欧洲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新消费主义最为鲜明的英国,在18世纪也享有相对较安定的(国内)局势,但政府未像清朝或江户幕府那样用心保存与重振传统角色和身份地位。
可想而知的是,清朝或江户幕府的做法可能使“通过时尚来界定自己身份地位并与人互比高下”之事变得较不重要;于是,在18世纪中国、日本的“繁荣时代”里,人们虽然也会有某种形式的物品积累和富裕,但却比较不是为了汰旧换新的理由而这么做。
至少,在中国有个值得细思的问题是,时尚的兴起在那里是属于某个非常漫长、缓慢且绝非线性的过程;而在那个过程里,精英阶级的竞比高下和自我认同,与做官、官阶的关联愈来愈浅。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是这一趋势里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官场生涯的日益不稳和失意,似乎助长精英追寻其他人生志业和(至少暗地里)追寻不那么直接倚赖官方科举制度来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方法。精英们的这一追求,加上私人财富日增,不只有助于助长先前已讨论过的时尚、炫耀式消费的兴起,还助长了其他活动,例如精英更多地赞助佛寺、更加看重私人组织的文献考据事业等。

穿袄裙、衣裤的清末缠足汉族妇人
清朝不只在1644年后成功重建秩序,还局部恢复了公益服务(包括当官和投身朝廷所鼓励但未主导的慈善事业)作为人生理想和身份地位标志的光环。而从前述的角度来看,清朝的这一成就,很可能阻止了时尚的成长,就如同这一成就也抑制了精英对佛寺的赞助一般。凡是主张出仕重获重视一事产生了拖慢时尚成长的广泛心理效应的论点,都必然流于猜测,但从中至少显示了一个相当直接的关联。
清朝时严格的官服规定,可视为某种禁奢令的施行。清廷通过让官场以外的人有权利穿上原本只限官员可穿的各式服饰(官帽上的顶珠、官帽等),高调奖赏那些在赈灾、筑路等种种公共工程上援助有功的商人、地主和文人。而穿戴这类服饰者,肯定不想看到它们贬值,或不想看到未有类似贡献者也能穿戴。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重振中央政府权力一事,虽然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曾以为的那样,掐断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更广大经济土壤上的生机,但可能还是足以把“特许体系”重振到稍稍拖慢“时尚体系”成长的程度。
清朝时精英阶层的女人无缘当官,但清朝的法令还是对她们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明朝时,诗词唱和就是精英阶层女人表达自我想法、感受和进行社会竞争的极重要工具,至少在长江下游是如此。
而在中国“漫长的18世纪”里,诗词唱和更加盛行,反映了当时的繁荣、(在没有世袭贵族的国度里)高度竞争的婚姻市场,以及(伴随考据之风鼎盛而来的)强调赋写诗文为有教养之人的必备条件的现象(而且对此的看重可能更甚于以往)。这种竞争与表达自我的方式所需要的购买行为,不像欧洲所需要的那么多。在较落后地区,包括新近纳入统治的地区,女人的诗集甚至使她们有机会,间接参与清帝国的建造和满汉两族的“文明开化使命”。这种支配边疆地区的做法,大不同于借由消费该地异国产品来支配边疆地区的做法。
与此同时,清朝上流文化的道德主义鼓励这些女人比明朝时更加不抛头露面,鼓励她们与城市风月女子更加划清界限。精英阶层已婚妇女和交际花社交、诗词唱和,在晚明的长江下游相当常见,但在清代就少了许多,而随着这两类人不再打成一片,商业化且在意时尚的娱乐圈,对人数更多、更富裕和更重要的精英阶层已婚妇女群的影响,大概也就因此减少了许多。

清末广州汉族贵妇与婢女
在这里,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恢复,可能也使人较无意通过愈来愈频繁的购买、抛弃物品的行为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地位。但凡是这类论点,我们都必须视为没什么凭据的揣测,因为我们对精英在各种场合的衣着(更别提对家户预算)所知太少,无法在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阐发。若要得到更多线索,我们得把欧洲时尚超乎寻常的加快现象视为待厘清的问题,而这问题所需要的解释,至少和中国、日本在品味上“未能”如此频频改变一事所需的解释一样多。
诚如许多作者所说,不管是哪种解释,肯定都有一部分着墨于心态的普遍改变。在18世纪西欧,随着个人在他人眼中(从配偶到职业生涯,再到宗教信仰的种种事物上)具有的自主选择权被视为彰显自己身份地位和个人尊严的重要依据,消费上的自主选择权很可能也因此同样被视为表达自我想法的重要工具,从而对欧洲日益壮大的“时尚体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些学者在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国精英身上,看到更加看重个人自主选择的现象(例如在择偶上),但这些学者也把事情看得够清楚,最终未把这些趋势说成和西欧一样显著,且指出它们并非代表那种把作为选择主体的“个人”摆在第一位的观念。
02
中国从欧洲进口的东西惊人地单调,与其从东南亚的进口截然不同
让我们稍稍转个角度来探讨此事。限制大家族的自主发展空间(例如立法禁止家族间的世仇报复和扩大法律的一体适用范围),乃是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诸国壮大的推手之一。在这过程中,诸国几可肯定削弱了大家族在界定个人身份上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推进了通过与买来之商品的新关系(而非通过亲族与不能让渡的遗产)来标示个人身份的趋势。
相对的,江户幕府和清朝则通过与地方制度结成伙伴关系来恢复秩序,并把许多日常治理工作交给地方制度负责;大家族在这些制度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以在中国为然,而中央政府提升地方大家族的权力和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远比着手抑制它们更为常见。或许,在这类制度和身份仍占上风的地方,人们较无意于通过选择商品和展现商品选择来不断界定自己的身份地位,从而较不需要汰换仍堪用的物品。

《本多平八郎姿绘屏风》,日本江户时代
但个人自主选择和群体成员身份两者被认定的价值,在不同社会里可能会被许多不同的方式改变;可能在某些领域里受到鼓励,在别的领域里又受到抑制。因此,若我们想为一个较具体的现象寻找解释,就有必要在一个较具体的层面上寻找。于是,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探索,欧洲在“时尚体系”加速成长的过程中,究竟涉及哪几类物品,以及那些影响它们在全球各地的生产和分配的因素。
如果说欧洲人的品味真的比中国、日本境内的品味变得快,这一差异似乎可部分归因于舶来品(尤其是异国制造品)在本国受到推崇的程度差异。毕竟,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中国瓷器等东西,都变成欧洲很重要的时尚,甚至在相当低层次的时尚亦然;而在东亚,西方的舶来品没有一样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的确,17世纪中国的艺术鉴赏指南,曾把几样外国制品列为值得收藏的名物,且在这时期还有其他几部中国、日本的著作,也显示了对西方产品的兴趣。西方的眼镜和其他穿戴在身上的饰物,在明末清初令某些中国人感兴趣;“西洋衣”(以非常昂贵的布料制成,仿以某位来华的意大利人为明朝皇帝行宫所建宝塔上的图案),风行甚久,在17世纪为中国宫廷妇女所采用,18世纪更为长江下游时髦女子所采用。同样在18世纪,异国皮裘(先是俄国皮裘,后来是美国皮裘)开始大受喜爱。
但即使如此,当来自亚洲的物品(例如纺织品)影响了欧洲的式样与消费模式时,为什么来自中、日境外的物品,却无一对中、日的式样和消费模式产生同样的影响?
西方论及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学术著作,普遍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对外国物品不感兴趣,乃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的文明较有优势。这一说法的确获得了一些文献的支持,像是乾隆皇帝的一段话,大概是反映这一心态的最著名陈述。他在1793年告诉来华的英国使节,中国所需的东西全可自制,对西方所能拿出的精巧玩物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他认为没理由扩大贸易关系。对许多史学家来说,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心态,这个心态被认为与好奇、贪婪和充满活力的“西方心态”背道而驰。

电视剧《戏说乾隆》
即使是思维较缜密的学术著作,虽然注意到了中华帝国的心态并非始终如一,因为中华帝国有时拥抱异国事物(以彰显普天之下皆我臣民的皇帝心态),有时又把异国事物拒于门外(以申明中华文化的优越),却还是常把这些皇帝的心态等同于所有“中国人”对外国物品的心态。
于是,从这一角度来看,欧洲对外国时尚较感兴趣,也就绝非偶然。这一说法意味着欧洲走上不同的道路,肇因于心态上的根本差异,而这一差异或许与欧洲人整体上更愿意冒险和创新有关。
但是,只要我们不再以清朝皇帝代表中国,那么就可以想到简单许多的解释,解释中国较不愿意进口大量舶来品的原因。毕竟,中国进口的物品和出口物一样多(由于当时的对外贸易体制,这是势所必然),而且,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充斥着异国的初级产品:供老饕享用的鱼翅、燕窝(以及许多较不那么异国的黑胡椒),制首饰用的珍珠,从中东和数个太平洋岛屿辗转运来的香,还有珍稀木材。对这些进口物的需求,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剧增。把许多这类物品从马来群岛运到广州的英国商人,发现他们要克服的问题不是供过于求,而是确保供货充足。
这些舶来品输入中国的数量,虽然个个都未像烟草、茶叶和糖输入英国那样急速增长,但它们的进口量原本就不可能急速增长。举檀香的例子来说,这类舶来品在中国奇货可居,商人因此四处搜罗这些物品,从而使一些太平洋岛屿的生态严重受创。
很讽刺的是,直到驶往中国的船只开始满载鸦片,这些岛屿才从这场浩劫中获救。此外,除了胡椒,这些舶来品几乎都是通过采集而来,而非由人种出来的。光是这一点,就使这些物品的生产不可能像新世界的种植园那样,因为有着大量奴隶在严密残酷监督下密集工作而得以集约化,从而不可能使单位价格下跌。人可以开垦更多土地来生产糖,却无法养殖更多鲨鱼或为生产燕窝的鸟打造更多丛林栖地。曾经有人试图借由掳人为奴来增加采集工的数量(尤其是在苏禄王国,位于今日的菲律宾南部),但采集工作本身的分散性,意味着连奴隶都保有颇大的讨价还价权力;加勒比海种植园那套营运方式在此完全不可能。
糖和烟草的消费的确暴增,但(诚如前面已提过的)它们大多产于中国境内,且由自由农生产出来。这意味着它们不但与土地的其他用途竞争,还与生产者利用时间(包括闲暇)的其他可能方式竞争。在这些模式里,不易看到中国人对异国奢侈品不感兴趣的证据。比较可能的情况似乎是,他们所买的舶来品,大部分不易转换为便宜的“日常”奢侈品(就欧洲人欲在东南亚取得的丁香和香料来说,当然亦是如此;糖和烟草也是不在此列的欧洲进口舶来品)。
凡是主张中国人对舶来品相对较不感兴趣的论点,都必然会指出进口制造品的稀少。但即使在这点上,诚如柯律格所指出的,中国的艺术鉴赏家所珍藏的物品里,的确包括数样外国物品。乾隆皇帝或许对欧洲的制造物没什么兴趣,但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精英却不尽如此,其中有些人的确收藏了钟和其他西方的奇珍异品。
不过,毋庸置疑,中国人均进口制造品极少一事,对关于得体衣着和家居装饰的观念影响甚微。此外,欧洲除了制造品外,别无其他东西可兜售,因此中国从欧洲进口的东西惊人的单调,与其从东南亚进口的东西截然不同。鸦片贸易勃兴前,中国从欧洲和欧洲人的殖民地进口的东西,约九成是白银,史学家就据此认为整个中国(而非只是宫廷)对外国事物不感兴趣。但针对白银在西方运往中国的货物里为何占如此大的比重,有个好上许多的解释:那个解释在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阿图罗·希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诸人的晚近著作里明显可见。
03
欧洲的“勤劳革命”,比中国还要显著?
从约1400年起,中国着手为其经济重新制定法偿币。这是由于先前一连串失败的纸币实验和元朝(1279-1368)严重管理不当的铜币政策,已使中国没有广被接受的货币媒介。在这一重新货币化的过程中,白银渐渐成为价值储藏(store of the value)工具、大型交易的记账货币(和往往也是实际交易媒介),以及这一庞大且高度商业化之经济体的官方支付媒介。这创造出对白银的庞大需求,使白银在中国的价值(相对于黄金和其他大部分物品),远高于世上任何地方;而且中国本身银矿不多。于是,在西方船只抵达亚洲的百年前,中国已在进口大量白银(大部分来自日本,部分来自印度和东南亚)。
西方人带着从历来最丰富的银矿开采的白银(1500年至1800年拉丁美洲所产的白银占全世界所产白银约85%)来到亚洲时,发现把白银送到中国(不管是直接送去还是透过中间人送去),可产生庞大且非常可靠的套利。
而且由于获利极大,追求最大获利的商人也就没什么理由送去别的东西[为了解“中国人的”心态,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分析了赴京朝贡团,发现这些朝贡团并未受此逐利心态影响,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活动是国君与国君在人为操纵的价格下所进行的,且基本上属象征性的交换活动。在这些交换中,逐利往往不是首要考量,尽管进行朝贡时通常伴随着逐利性质的“私人”贸易]。

马歇尔·萨林斯
多位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希望把白银留在国内(以备不时之需,例如支付战争开销),因此不断主张应改送别的东西到亚洲。他们的抗议在文献里占据显要位置,往往使后人以为“西方”拼命想要“亚洲人”买别种外国物品,而中国人则根本瞧不起西方人(或西方工匠工艺太差),致使西方人无法如愿。
但把焦点摆在这些论点的攻防上,就是误把某些政治领袖的意见当成整个社会的心态,一如把焦点摆在中国皇帝对朝贡贸易的正确形态和限制所发出的言论,失之偏颇。在这两种情况里,真正决定要做何种买卖者,乃是在市场里打滚多年的商人。
这种把中国的进口偏好看成文化保守心态的倾向,往往又因为把白银视为现代“货币”(即把白银视为残余的抽象价值储藏物,经转换后构成欧洲的“贸易赤字”)而更为强化。
事实上,我们得把白银本身视为物品,一种以矿物为基底且经过精炼的产品,极适于发挥某种重要功用,而且西方能以比亚洲任何地方(在某些时期日本不在此列)还低上许多的成本生产它;先天的地质条件使中国几乎完全产不了银。
此外,西方只有在少数几项制造品上,不只在原物料供应上占优势,也在更精良的生产技术上占优势(欧洲的铸币技术生产出比亚洲境内任何流通的钱币还更好、更难仿冒的钱币),而白银就是其中一项。中国人使用的白银呈绽状,因此这一铸币上的优势,对中国人来说无关紧要,但对南亚等地(往往是欧洲白银头一个购买者)的白银使用者来说就至关紧要。这些白银使用者买了欧洲白银后,透过本身的贸易网络,把许多白银送到中国。
将白银视为现代意义下的“货币”,认为它们被送去东亚换取物品,而不把白银视为被中国人拿来充当货币媒介的一种物品,未免失之武断,而且这一武断性在这个议题一提出来时就清楚地呈现了。毕竟,许多象征社会声望的商品(丝织品、胡椒、鸦片和可可豆)在某些地方被视为物品,但也能充当货币。此外,许多白银有时充当货币,有时又充当饰物(例如首饰被拿去典当或熔掉时)。
因此,把白银视为一项较特殊的物品,而非现代的钞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白银流入中国那段时期里,也有大量黄金从中国流到欧洲和印度。最后,由于西方学界长期以来把西方视为主动(且有心)将世界结合为一体的力量,这个说法强化了把白银视为送到中国购买消费品的残余价值储藏物的倾向。

光绪年间湖北官钱局造银锭
但中国这个经济体可能占这时期的世界经济高达四成(若把也正在“白银化”的中国藩属一并纳入的话),其更改货币基础一事所产生的力量不容小觑。一旦我们把这股力量纳入思考,就很难不去把中国的白银需求,视为和西方对瓷器、茶叶等物的需求一样,是“主动”打造全球经济的强大力量。
我们会在第六章更全面探讨新世界的白银。在此,重要的是一个较具体的观点:西方在白银出口上的巨大优势,使来自亚洲且能决定时尚走向的象征社会声望的商品大量流入欧洲。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那么多其他的舶来品涌入欧洲,因为它们是欧洲人用白银买来的,使时尚的转变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都快(第四章会探讨这一大量输入现象的其他原因)。
这一观点认为,这一独一无二的大量输入现象,源于涵盖欧亚美三洲的经济形势,而非源于欧洲独有的某个“物质主义”或“好奇心”。欧洲取得和经营美洲银矿的方式提醒我们,欧洲在海外强取豪夺的行径对其获得经济优势有多么重要(技术上的进步也是重要因素,但如果没占有矿场并强逼人劳动,那也是无济于事)。
就这个例子来说,欧洲对海外强取豪夺所产生的成果,加快了时尚改变的脚步,从而使欧洲境内以市场为基础的合意性贸易更快出现;因而,从这方面来说,欧洲在海外胁迫的成果可能相当重要。但至关紧要的是,这个案例说明了欧洲在海外殖民地的高压统治,致使欧洲内部产生了斯密式市场动态般的额外推力(后来又转移到进口替代式的工业化),而不是因为欧洲内部较有效率的市场营销、工业生产,才促成对海外的压迫。
最后我们还得记住,即使有白银所导致的奢侈品进口,为时尚机制提供了额外的推力,那些认为欧洲对“非必需品”的需求比中国或日本的需求强劲许多,因而得以在经济上造成差异的说法,仍然只是个假设,绝非如松巴特、布罗代尔等人所认为的已是定论。
诚如前面已提过的,不管社会顶层对奢侈性商品的需求有何变化,我们仍然没有什么道理认为,欧洲的“勤劳革命”和大众参与斯密式市场动态的现象,比中国(或大概日本)的这类现象还要显著。新的奢侈性需求有时候会被赋予第二个意涵,也就是认为这一需求促成成功商人与工匠进行新的资本积累,使较大型的经营者具有新的优势,从而催出生雇用无产阶级化工人的资本主义商行;但这种做法仍有待思考。本章最后一节将转而探讨这些论点;至于下一章则会探讨金融制度和“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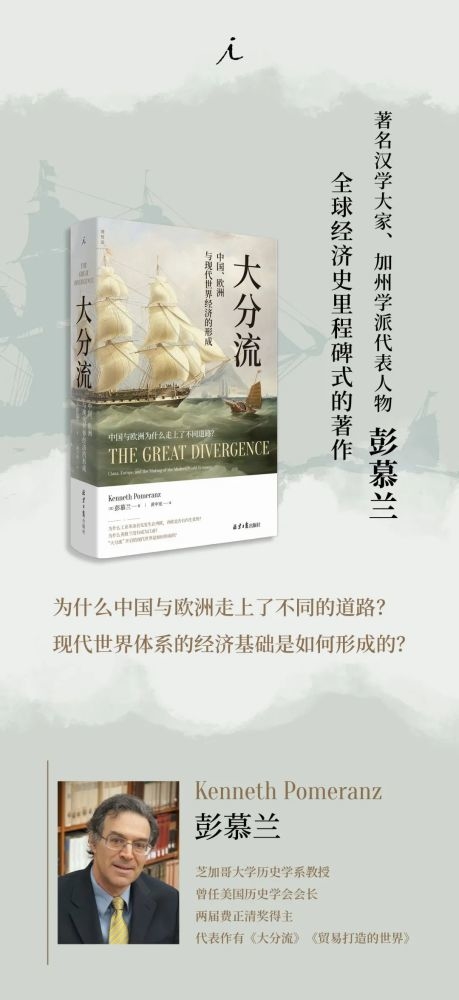


《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