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生和死是先天注定,我们的尊严来自于不死的思想|纪念

撰文丨李夏恩
“人生一世,生老病死,古往今来,莫之能外”。
死亡,不仅是让哲学家着迷的主题,也是史学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对哲学家而言,死亡是生命的对立面,是与万有相对的空无,是一个无法企及、无法感知却又无法否认的存在。如果将死亡视为一个生命终结归无的譬喻,那么它就像是放学后离开了学堂的学生,或是下班后离开单位的职工——学习也好,工作也罢,这些加诸己身的外物被死亡一一抛在身后,最终,自我的肉身和意识也被抛弃,只剩下纯粹的死亡。而对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便是跟在死亡之后,去捡拾那些被它抛诸身后之物,将其片片拼凑起来,通过追溯这个人学习、工作以及生活的印记,让已经死亡的生命再度呈现在生者面前,并且以生者的视角赋予亡者死后的意义。
因此,兼思想家与史学家于一身的何兆武,竟然鲜少提及死亡这一重要命题,才多少让人感到有些讶异。毕竟,仅仅是他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所经历的种种变相,就足以让他酝酿出自己对生死独到而深刻的见解。然而他却对这个问题长久地保持缄默,仅仅在一篇少有人知的文章中,约略提及了自己的生死观。这是他为一套名为“文化四季·生老病死丛书”所写的简短序言。这篇序言刚好就贯在古今中外数十位哲人文士撰写的生死议论之前,仿佛正是他为这场生死大讨论开了个头。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86年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著有《中国思想发展史》《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译著有罗素《西方哲学史》、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以及口述史《上学记》,影响巨大。
何兆武写下这篇短序是在2003年,时年82岁。读者本可以指望这位饮誉天下的思想家,会以经年的阅历和思考赋予这篇文章与众不同的观点。但被何兆武拈来作为开场引言的“人生一世,生老病死,古往今来,莫之能外”,却是一句众人皆知无甚稀奇的俗语。他更以一种寻常不过的笔调,点出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其他的动物对于自身的生老病死不但茫然无知而且漠不关心,而人却需要问一个为什么——由于一个什么原因,为了一个什么目的。人生一世究竟是为什么,又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终古之谜。一切物种都对此茫然无知,也根本无意去追问它究竟是什么回事。只有人类前赴后继地终古都在追求这个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的答案。这种追求正是人之所以易于禽兽的那一点‘几希’。”
人与禽兽的区别就是能思考人生的意义,这当然只是一句老生常谈。之后对生死的讨论,何兆武同样没有给出更别具一格的思考。“有生就有死,没有死就无所谓生。生和死是先天注定永不分袂的”。既然“生与死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体。了悟生死之为一体,正是自古以来哲人所追求的‘齐万物,一死生’的真谛之所在,以至于才有所谓‘学哲学即是学死法’的提法”。至于了悟生死的方法,“不单要靠静观与思辨,而且还有待于体验和感受。没有体验和感受,则静观和思辨是空洞的;而没有静观和思辨,则体验和感受就是盲目的”。
这段论述如此四平八稳,以至于既不能说它错谬百出,也不能说它蕴意深邃,它就像是一位照本宣科的老塾师在宣讲一套已听过无数遍的陈词滥调,只不过这一次被用在了生死观这样本应引人着迷的话题上。
想要从何兆武的论述中得出任何新启示的读者,或许会因此感到深深失望。一个自我安慰的说法是,这篇序言不过是这位老学者为了奖掖后辈编辑之力而写的应景之作,所以少有人读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何兆武最出色的著作《历史理性的重建》中对康德历史哲学的论述,至今仍是专业学者难以绕过的峰峦幽谷。他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泼天才华虚掷在一篇应酬之作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或许也是何兆武有意为之。我们眼中的老生常谈、陈词滥调诚然令人心生烦厌,但它们之所以能够千百年来众口相传,或许正是因为它们是历代智慧的累积,就像2+2=4一样,成功地经过了不计其数的验证,而最终得出的一个最能为众人接受的结论。
这是否是何兆武的本意呢?《读柏克》是何兆武众多学术随笔中最重要的篇目之一,也收在《历史理性的重建》当中。文章的两节是分别撰写、刊发在两份不同的刊物上,但合在一起又贯通一气,足见作者用心良苦。在这篇文章中,何兆武写道:“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够传之久远而历久不衰的,必然会有某些因素是诉之人类普遍的理性思维的,因而值得我们去重视和研究”。“一切现状都是过去历史的产物,既然我们无法与过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向过去汲取智慧并明智地加以利用。除了谦逊地低下头来向过去的经验学习而外,我们还找不出其他更聪明的办法。”
事实或许正如何兆武所写的那样,那些关于生死的陈词滥调,正是过去诉诸普遍理性与实践验证的道理。尽管看似是将它们拈来复述一遍,但唯有亲自体验和感受,才能真正理解这些老生常谈中所蕴含的深意。
当何兆武写下这段生死论述时,他已经几乎用尽自己的一生来验证其中的道理是否真切。如今,他已迈过死亡的门槛,抵达了这个人类终极问题的终点。尽管他再也无法用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来作答,但他漫长的、如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生,或许就是答案本身。正如从天而降的雪花,当它落在掌心融化消逝的那一刻,正是人类生死了悟的瞬间。

晚年何兆武
雪:战栗与美好
雪,想必在何兆武的一生中占据着鲜明的位置。尽管他并未刻意赋予雪以特殊蕴意,但上学时代的雪定然让他印象深刻,以至于多年后,他还会想起老北京冬天不时而至的大雪。
他在老北京出生,也在老北京长大。雪无论是在他的上学时代,还是在他晚年的记忆中,都“持久不化”。冰雪天地外出上学,“风吹在脸上,感觉就像刀割一样,耳朵不断地流血,凝成血块。手和 脚也都裂 开了,用北京话叫皴裂 。那 时实在是太冷了,冷得锥心刺骨 ”。即使是在教室里,也只能靠生炉子来抵御伺机侵入的冰雪酷寒,“整个教室几十个人,就生一个炉子,但还是不大管用”。
中学时代,何兆武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也发生在一个漫天大雪的日子里。当时他正在读初中。那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有时一连下了三天。“雪一直下到膝盖,也没有人扫雪,大家就这样踏着雪,每天步行上学、散学”。就在1935年12月9日早晨7点多,何兆武走在上学路上时,他听到两个洋车夫谈话,一个说:“西直门又关了。”另一个问:“怎么又关了?”那个人回答说:“今天闹学生。”到学校后,何兆武才知道那天是学生自行组织的“一二·九”游行。一周后的“一二·一六”游行,比“一二·九”声势更加浩大。第二天早晨上学时,何兆武看到道路两旁的树枝上挂满了冰,非常好看。“可以想见,前一天的场面会是多么激烈。宋哲元的29军用大刀、警棍和枪托殴打学生,并用水龙头阻止游行队伍,可是没有真正开枪,所以没有学生死,但有人受伤。第二天,各大报都开了天窗,也就是说,撇掉原版,只剩下一页空白。”

一·二九运动,面对民众演讲的学生
与雪配合的,似乎总是苦难的严酷记忆,不是自己被冻得耳如刀割,就是自己的同学和学长在冰天雪地中被军警殴打得血染白地。但苦难并不是全部。尽管北京的冰雪凛冬确实让人战栗,但回想这座古老城市里的旧时琐细,给何兆武留下的印象是“美好极了”。他在北沟沿的童年旧居对门有个小商店,每当赶大车的劳动人民从乡间回来,会特意在小商店门前停下歇脚。他们一进门就掏出两个铜板,往柜台上一放,招呼“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会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们,并会拿出一些花生米放在他们面前。“客人一边喝酒,一边和掌柜的聊天,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最让何兆武动容的,是聊天结束后上路时的那一声“回见”。这个场景一次次地出现在他的记忆中,让何兆武感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
他也记得周六下午没有课时,骑着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借书时的那一段路,“刚一进去是柏油路,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便发出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而富有诗意。”
一本给学生读的《世界名歌选粹》也能让刚上初中的何兆武深深着迷,《圣母颂》的音乐让他“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根据歌德诗《你是否知道那个地方》改编的歌曲,更让何兆武“觉得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感觉美好极了”。他的一位同学对他说,如果放学回家做完功课,“能一边听着窗外的雨声,一边躺在床上看小说,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如果看完小说还能吃一顿油煎饺子,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

青年何兆武
即使是冰天雪地中凶暴的军警对游行的学生痛下辣手的残酷行径,在事后也成为了何兆武心中绚烂的英雄记忆之一。他和同学特意将刊登学生游行报道的英文报纸《北平时事日报》(Peiping Chronicle)拿给英文老师请他讲解:“老师在讲台上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在下面听得也心潮澎湃,还知道北师大的篮球国手张连奎被军警打断了胳膊等,就像在听英雄故事一样”。
第二年夏天六月的学生游行,初中三年级的何兆武也躬逢其盛,这场游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略带恐怖协奏的轻喜剧,他和两名同学躲避军警乱挥的刀棒,趁乱逃进了路旁的一家照相馆,误打误撞跑进了冲印照片的小黑屋子里。他们屏住呼吸,听着外面嘈杂的声音渐渐平息才走出来,那些照相馆的人正在有声有色地描述外面“学生如何如何跟军警对打之类”,眼见三个学生从里面走出来,都大为惊讶,“原来里面还藏着三个人?!”之后,他们在一位同学家里吃了伯母亲手做的炸酱面,聚谈起那天紧张刺激的冒险,“大家都很兴奋”。
一面是脉脉温情的人情,一面是凶神恶煞的军警;一面是紧张兴奋的英雄冒险;一面是棍棒乱飞的血染雪地。美好与丑恶,幸福与苦难,宛如一双兄弟携手相伴,时而这位亲切招手,时而那位恶面相向。生活就像摆锤,在苦难与幸福之间摇摆。只是20世纪初纷繁诡谲的内外形势,不知何时就会将摆锤推向哪个方向。
上学记:苦难与幸福的联大神话
如果没有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摆锤或许仍然会在幸福与苦难之间摇摆不定。但北平郊外逼近的枪炮,却将摆锤猛烈撞向苦难的一方。北平的沦陷,何兆武一家不得不离开珍爱的故土,踏上逃亡之路。多年后,何兆武还记得离开北平的那天早晨:
“天气很凉,而且感觉非常奇怪。火车站一般人都很多,来来往往乱糟糟的,只有那天早上的感觉特别不一样,人还是很多,可是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整个火车站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
这是一种前途未卜的恐惧,战争的爆发将未知的苦难推到了每个人的面前,战火所及之处,生与死不过是转瞬之间。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阳,何兆武遭遇了人生第一次空袭,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39年2月4日,阴雨连绵的贵阳一时晴空万里,这场轰炸非常惨烈,“几乎炸了贵阳半个城”。何兆武再次踏上逃亡之路,而这一次,命运将他送进了战时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合大学。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报到,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好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何兆武的回忆中,西南联大做学生的七年,是“一生中最惬意一段的好时光”。
从鹿桥描绘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经典小说《未央歌》,到为了庆祝清华百年而拍摄的电影《无问西东》,西南联大作为战火纷飞之中傲然屹立的知识明灯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环境艰苦却名师林立,培育的英才更是各擅其才,在不同领域功绩卓著。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缔造了现代中国乃是世界未来的命运。西南联大,在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神话。
何兆武就是西南联大神话最重要的创造者之一,他的口述回忆《上学记》几乎可以说是西南联大的一首颂歌。另一位神话创造者则是他的同学汪曾祺。何兆武曾经回忆这位同学“一副旧社会文人的派头 ,经常趿着一双拖鞋 ,看起来甚至有点颓废 ,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他日后会做出什么特别的成绩。”但当时的何兆武自己穷困落魄的境况恐怕也不比汪曾祺好出几分。从1939年到1944年,对学生时代的何兆武来说是最困难的几年。这位中学时代一天三顿,常有白米大肉吃的中产阶级子弟,在西南联大却只能吃掺杂沙砾老鼠屎的“八宝饭”,纵使是这样的饭菜,也常常被一抢而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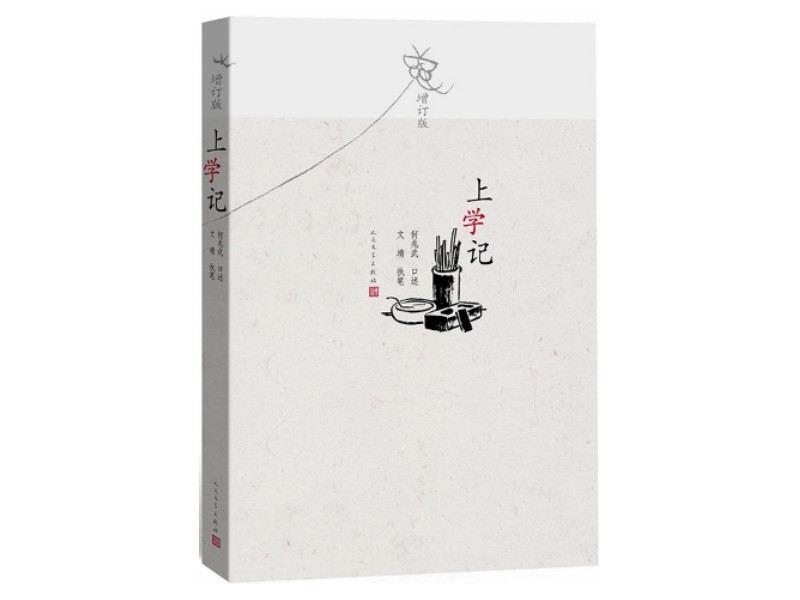
《上学记》(增订版),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3月版
贫穷与疾病常常联袂而来,研究生第一年,何兆武就感染了肺病,“那时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每到风雷交作的天气,何兆武就会感到气闷压迫,开始吐血。尽管一位同学开玩笑称他这是“天人交感”,但许多同学却没有乐观地挨过贫病的侵袭,“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
即使从外部环境,昆明也时常遭受空袭的威胁。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尽管何兆武会同意汪曾祺在多年后的回忆散文《跑警报》中的描述,将日机轰炸视为一种对中国人“不在乎”的乐观精神的磨砺,但他也目睹过一些悲惨的景象。1940年秋的一场轰炸,西南联大的图书馆、宿舍都被炸了。何兆武还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
神话毕竟是神话,虽然基于现实,但并非现实本身。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单独列出一章“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对西南联大师生间不计功利的团结友爱倍加赞扬。但如果翻阅西南联大的档案就会发现,这可能是联大神话中最不符合事实的一点:联大至少有两次面临分裂的危机,每次都是因为资金或是人员职位分配之类的纯功利问题而濒临分崩离析的边缘。
但纵然如此,何兆武对西南联大学生时代的热恋,却并非自抬身价的夸夸虚谈,而是真情实意。物质条件的困苦,在精神上却可以得到慰藉。西南联大自由散漫的学风,非常符合何兆武的胃口:“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

西南联大校门
在今天看来,这种校园管理简直像是将学生当成一群无需放牧的羔羊。学业的坚持几乎完全靠个人意志来进行,困苦的物质条件也会时时剥夺人求学的意志。但何兆武提供了西南联大最具吸引力的一点,就是简单的两个字“自由”。多年后,何兆武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时说道:
“‘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材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何兆武坦承自己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他初学土木工程,然后误打误撞进入历史系。学生转系如此随意,课堂上的老师也是随性而为。全校的公共必须课中国通史,由雷海宗和钱穆两位著名学者教授,但两位老师“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钱穆还在课堂上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国史大纲》做广告:“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有的老师甚至“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何兆武听得津津有味,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
一些学生甚至敢于和老师当面顶撞。一位姓熊的理学院学生,经常和教授力学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当面激辩,尽管时常把周培源气得说:“你根本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但师生间的争辩还是成为了南区教室的一景。一些高傲的学生不仅和老师争辩,甚至菲薄名贤,讥弹大家。何兆武在多年后,还记得在茶馆里,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对爱因斯坦最新发表的论文“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道:“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种自由狂放的“大不敬”气魄,成就了众多有跨灶之能的杰出学者。
也正在此时,何兆武着心于探寻幸福的含义。“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那么究竟何谓幸福?物质条件的享受或许是幸福组成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在与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同学王浩的交谈中,何兆武引用艾略特的一段话:
“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
“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种“dunch 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物质的艰困恰可以成为淬炼幸福的工具,在心灵与物质困苦交战的过程中,让幸福得以超脱物质享受而达至心灵完满的境地。纵使在心灵的世界中,也不仅仅只是由理智、逻辑、科学占据的精神生活,而是存在着另外一个天地,“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朋友Horatio说的话:‘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师生合影留念
因此,西南联大的困苦环境和自由学风,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这个非常时代,诞育出一种近乎纯净的幸福感。就像何兆武在多年后回忆自己的联大时代,如此动情地写道:
“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何兆武的好友王浩尚未进屋就在门外高喊:
“The war is over!”
声音如此高亢欢快,几乎因激动而变音,以至于乍听上去,何兆武还以为好友在喊自己的名字“zhaowu”。当天晚上,这些平日穷困潦倒的学生凑钱买了食物和酒一起庆祝。过度的兴奋让两位同学当场犯了神经病,大哭大笑,又吵又闹——“大概是多年战争引发的苦难和流亡生活的压抑突然之间爆发出来了”。这一因狂喜而癫乱的场景,让他想起了莫泊桑的一句名言:
“Mais , C'est si fragile,une vie humaine!(人生是那么脆弱!)”
上班记:折与弯之间的思想芦苇
人生漫漫,就像一根长长的芦苇,总有一些回忆就像芦苇上深色的折痕,会不断地提示人反复叨念、品咂其中的意味。在何兆武的回忆中,有一段回忆必然印象深刻,以至于在面对不同的访谈中,被反复提起。
那是在1959年,何兆武已经从当年的学生,成了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班的研究员。他被派驻到河北卢龙县下乡,编纂地方史。此时距离日本占领结束只有14年,所以许多中年人还记得沦陷时的境况。让何兆武印象最深的是,卢龙的老县城有四个门,每个门都有把守的日本兵,凡是进出城门的人都要向日本人鞠躬敬礼才能过去。
“做了亡国奴,还要向日本人鞠躬,岂不是很没有气节,但要是不鞠躬的话,就会是一刺刀。”
那么究竟是折腰求活呢,还是宁死不屈呢?何兆武用“这中间的难题还是需要从伦理学上给出解释”,并且举了一个夜行时被手持武器的歹徒抢劫钱包的例子,“这时候你奋力反抗当然足够英勇,但是你如果放下钱包,恐怕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英勇和明智,折腰求活和宁死不屈,两者可以得兼吗?是只能舍一取一吗?1959年在卢龙县听到的故事之所以让何兆武印象深刻,是因为他自己就看过太过的选择。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主题,生与死不仅是个人面临的抉择,更是攸关民族存亡。在强敌凭陵,国家沦丧之际,如果没有千万勇士视死如归,舍命搏杀,后果定然不堪设想。然而,当我们将视角放诸个体生死之上时,就会发现,宏大叙事下非生即死的极端境况,似乎并不完全适用于像原子一般孤立的个体。在面对生死的一瞬间,个人有着多种选择,而每种选择都可以找到合适的理由和说辞。而对何兆武来说,他亲历目睹的个人抉择,却时时像警钟一样,给他的心灵以强烈的震颤。
1946年夏天,昆明。战争结束,西南联大的学生正准备陆续北返。昆明的境况也变得危机四伏。7月12日,来到昆明宣扬民盟思想的社会活动家李公朴被特务暗杀。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追悼会上大骂特务,在回家路上也遭到枪击。下午一点多时,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的何兆武突然听到两声枪响,紧接着,何兆武看到有人抬着担架匆匆走过,只见担架上血污狼藉。传来的消息是他的老师闻一多遭到刺杀,被送往云南大学医院。

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
当何兆武赶到医院时,闻一多已经因伤重去世,遗体就摆在院子里。他看到闻讯赶来的闻一多好友历史学家尚钺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
“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呢”,但目睹一位宁折不弯的耿直师长倒在血泊中殒命,这不能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抚尸大恸的尚钺的发问“何必呢?”想必也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20年后,何兆武再次目睹这一抉择惨剧。杨超是与他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在那个传相举报、人人自危的年代,他拒绝用攀诬他人来换取自己的安全,留下遗书自戕,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只有三十九岁。而与之相对的人,其他好几十人明知这是诬陷,但为了活命,还是认下了莫须有的罪名。
“‘人’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以致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你一骂他,他马上就承认是自己有罪,没有一个敢据理力争,这一点使人思之不免黯然”。而在这些随众低头认罪的人中,就有何兆武本人。九年后,何兆武亦师亦友的目录学者王重民也做出了同样的抉择。在儒法之争的激烈风暴中,他拒绝逢迎上旨,将一部伪造的明代学者李卓吾的著作《史纲评要》说成是真品。为了捍卫学术尊严,他在书桌上留下了自己常用的手表和一部《李卓吾评传》,在颐和园后山丛树中自缢身亡。何兆武虽然也受到冲击,但他却坚定地选择活下来。并且与那些和他一样忍辱求生的人一起活到了云开见日的时代。
“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例如除了人这个物种而外还有哪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的?”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何兆武将当时遭受的艰难困苦归咎于人性的缠斗:“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毋宁说是人性在面临逆境时的抉择,犹如风中芦苇。究竟是逆风挺立,身折不屈,还是望风屈身,苟安求生?面对劲风袭来,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
当然,或许和风细雨之下,不必费心抉择,更有利于人性朝着正向挺立生长。往往劲风之后,摧折的都是高大挺立的乔木稼穑,留下的唯有善于迎风低头的稗草杂花。但对何兆武这样心智早已坚固的人来说,这一点也或未可知,因为人的生命力如此强劲,就像经霜的芦苇,在阳光下会愈显刚韧金黄。一旦能够出脱暴风骤雨,他蕴积的生命焕发出的能量会更加惊人。
从卢梭到波普尔,从罗素到柯林伍德,从康德到孔多塞,从柏克到梅纳克,从贝克尔到伊格尔斯,这些西方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经由他之手,译为中文,嘉惠学林。随着年纪渐长,他一直隐藏的棱角也随之渐露。面对年轻学者以“商榷”为名的批评(“商榷”这个词在人文学科有特殊的含义,放在何兆武这里,它的大概意思是:前辈作为学界巨擘,我等后辈仰止尊荣,所以特意从您的著作中挑些毛病写篇批评文章,希望能引起您的关注从此对我青眼相加),他报以缄默。在他2006年出版的口述自传《上学记》中,他对自己的两位名声远扬的学界前辈吴晗和冯友兰也直言不讳,从学风到人品皆加以点评。纵然这让他遭到两位大师忠实拥趸的批判,但他只是照单全收,终其一生对自己的文字也未加改动,甚至在2016年增订版中,更增加了个人的批评。

《思想的苇草》,何兆武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多年前,在风霜凛冽的时代,何兆武偶然之间发现了帕斯卡尔的《沉思录》,这位三个世纪前的哲人的沉思隽语,给了他心灵莫大的慰藉,或许正是从中,他找到了弯与折之间的中道: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作者丨李夏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