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我所有的诋毁都是赞美,反之亦然


《时光硬币的两面》作者孙甘露
文 / 孙甘露
看不见的容貌
人的容貌,是一个焦点,除了性别和年龄这两重因素之外,任何社会身份都无法根本改变或修饰它,使之仁慈、残忍、光彩照人或者不可理喻。
那些具有特殊容貌的人,会成为众人崇拜或厌恶的对象,他们能愉悦人的感官,或者在记忆中令人眷恋不已。
更多的面容是属于多数人的。公众对它们视而不见,它为镜中的目光所规约,避免了沦落为代码和标签的命运。它们有幸被记录在少量的照片之中,在亲友们的手中传递,偶尔为陌生的目光瞥见,引起一阵惊叹以及大量的漠视。
每一个个别的面貌,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帧海市蜃楼般的幻景,为最真实的存在所消耗,其中的若干面容甚至从未被凝视、端详、抚摸和热烈地亲吻,它们的干枯和苍老仿佛是被人预设的,很难说这意味着悲苦。另一些被印刷术疯狂复制的面容,在光滑的平面上凝聚了更多的假笑和哀伤。它们被编入各式各样的虚构和幻想中,被占有、折叠乃至毁弃,它们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拒斥和坍塌而不是永生,而大量的存在必然在导致大量的死亡。
但是,公众的视线依然为悦人眼目的形象所吸引。这些形象由某个和某种面庞演变而来,引导与暗合了不同人群的口味,塑造同时也分割着人们的憧憬之情。极少有人能够回避商业摄影师的典型之作,完美的容貌,无与伦比的身姿,环境总是纯净得如同在真空之中。这与那些严酷的新闻摄影适成对照。(大师们的作品人们虽然见得不多,但它们的存在是必须经常予以提示的。)视野的宽度可以使我们获取对比的概念和明暗变化的承受力,使我们最终确认容貌而非形象的真义。
乐观地说,容貌是一个人的诗篇。无论从审美还是实用的角度看,它既是人最高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工具,它生动、易毁、暧昧兼有抒情和叙事的功用。所以,少量的佳作和大量的平庸之作便是无可避免的了,这种数量上的对比可以理解为对人世的一种比喻。
我们的容貌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较之我们为照相机所记录下的形象,它在向众人敞开之际唯独对我们自己遮蔽了起来。由于造物主的缘故,我们的目光只能宿命地注视他人,而我们所谓的容貌永远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的他者的世界。我们是盲目的,自我的缺席加深了这种盲目性。自始至终我们是丧失自我的,而徒劳的寻求更促进了这种丧失,永劫不复地使我们更加远离自身。我们只是存有幻想,在世界众多繁杂的面影中,我们会接近这样一个形象:它不断地向我们显现,但最终我们也没有看清它的形象。
学校
就个人而言,学校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种回忆,一种别人的职业或者生活方式,一种通过我的母亲、妹妹、友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各类学校中)若即若离接触到的日常景观。我想,今天的学校与我十多年前认识到的学校就某些方面而言,可能略有不同。它的日常活动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陌生了,我仅仅是透过它的基本恒定的教员、不断替换的学生、今天仍在使用的教材隐约获得了一些感想。
按照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说法,学校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它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教给一个人以分寸感,使之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离开学校以后与这个社会相适应。尽管这是一个比较文学化的说法,但它仍然道出了传统的(多少带点英国式的)对解惑、授业、传道的基本态度。
就我个人有限的经验而言,念书时读到的课本大多枯燥乏味,往往是授课教师的性格、素养、谈论方式才使得这类干巴巴的精神食品被输送进了那个可怜的脑袋。对我来说,老师几乎就是学校的另一个名称。
学生可以说是无辜的,他们毫无准备地被家长、社会要求、未来命运的需要所支配,毫不留情地掷入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他们的反应一般是不被重视的,这需要等到他们离开学校,从别的社会角落,用别的方式将过期的反应及其结果呈现于一个比较为人瞩目之处。
面对这一庞大的机构,学生是无能为力的。学校需要教师来治理,他们应当急切地研究教学方式,改革教材。而不是等待外部世界的缓慢变化最终影响至教育本身。
我谈论的只是教育一斑,这一问题的所有复杂之处,绝非我所能道其万一。同时,我几乎还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在观望和回忆学校,所以,依然可以将这番话看作是一次对教师的吁请。教师的言行无疑对未来社会的意识形态将产生影响。所以,他们本身应该是一些更具个性的个人,具有更广阔的精神空间和创造性,他们应当在每一堂课上使书本上的文字向学生生动地涌现。他们应当将每一讲的内容视为一次精神的呼吸。
借此机会,我向曾经给予我不倦教诲的老师谨致谢意。

《时光硬币的两面》作者孙甘露
90年代
在展开的稿纸上描绘20世纪最后十年中一名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的个人设想是一件冒险的事。它的惊险程度不亚于一部小说的写作本身。
尽管我在试图展望90年代,但是在文学的意义上,我主张放弃年代概念。
十年对于一名作家过于漫长,但对于所有大于个人的概念它又过于短暂。在十年中可能会诞生一部次要的小说和一次重要的婚姻。或者相反。谁知道呢?
对于某个年代或许我会怀有期待和善意,犹如对于那些我们所关心和热爱的优秀人物。但是我们是否会对无数时代怀有善意,就像对广大的人群怀有善意呢?问题提得过大,类似于过去十年间文学界的爱好。但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它可能暗含着一种微小的个人希望。那就是,尽我所能写一部小说,也许是两部。至于婚姻,我想一次就足够了。
对于一个人的十年来说,这已经过于奢侈了。
闲话请客
请客是件雅事,且不论背后的动因;但这事一说就俗,就跟谁没请吃过或吃过请似的。其实并非如人们常说的:雅者见其俗,俗者见其雅;倒是有几分许子东在电视上论王朔的意思,是雅者见其雅,俗者见其俗;好比那些面善的撞见王朔、陈丹青爆粗口。方言里万世不易的俚俗部分,就跟饭馆隶属的菜系,去掉了,没味!
打小,外婆总是叮嘱我们,吃饭时不要说话,多半原因是怕我们噎着。后来读到“寝不语,食无言”,恍惚觉得找到了出处。其实外婆跟我一样,没上过几年学,那些规矩也就是旧时代的通俗。再往后,开眼瞧见一些外国电影,就见一堆人围着饭桌聊个没完,刹那解放了幼时攒下的拘谨,私下觉得光吃不聊是很丢份的。吃得好和聊得好互为映衬,好比阿城说从前山民甚至为泡茶而洗水;一壶好茶,茶和水各占一半,没有好水,再好的茶也给糟蹋了。饭局如许,请吃没聊好,就跟没吃好似的。
在家里用饭容易走极端,相对无言和大吵大闹都是常态;但如今国中请吃,说的基本是晚上下馆子:解馋、凑趣、蹭饭、吃冤家乃至鸿门宴。这一餐,功能上贯通下午茶、餐后咖啡、酒吧畅饮乃至宵夜,由华灯初上聊至夜深人静。从前窜酒吧的多,而眼下迟到早退的都是些窜饭局的。这厢儿说谢谢您赏脸,那边儿摞着话说,您这是给我多大面儿啊!嘻嘻哈哈,拍肩膀抱拳。各色人等在饭桌上约见,一手举着烟,一手掐着手机,谁瞧着都觉得筷子多余。烟雾使餐桌上的氛围平添热烈,颇有几分澡堂子的气韵。豪爽的,通常请吃;也有气派更大的,永远吃请。
记忆中最特别的请客,是在圣彼得堡郊外夏宫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坐落于离火车站不远处的一片树林里;车站上大都是些赶通勤火车回城的工人、学生,饭馆生意清淡,我们一行人边吃边等火车,菜点冒了,剩下不少。有多年俄国生活经验的郑体武教授,严肃指出这样是不礼貌的。话音未落,那位自我介绍在意大利开过多家餐馆的女厨子真的不高兴了,以为是我们嫌她手艺不好,死活要为我们再免费做一道她的拿手菜,诸位,一大盆意大利式的俄国菜啊,并且看(四声中的第一声)着我们将其全部吃掉……不再描绘那食物了,下了肚子也就是一团东西。厨娘那满意的脸,我已经淡忘了,但是那个撑啊。
请客吃饭乃汇聚万象之事,有人写餐馆,具名“天下第一楼”,窃以为道尽了世道人情。这几日股市强劲,一些涨了股票的朋友,踊跃请客;想不被这感人的情景触动也难,我打算借此请人撮上一顿,因为我看上的那只股票也涨了。尽管我没买。
辞友人书
你们有可能是这样一些人,你们小心仔细地在拥挤的卫生间里剔除牙刷里的牙垢,较之用这柄廉价牙刷来做晨间漱洗更为起劲,双重的污秽使洁具和清扫对象互相成为肮脏的策源地。
你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笑逐颜开地打发自己的作品以及别人的作品。你们在若干场合称自己的作品是“狗屎”、称别人的作品“真棒”(这两年因为迈克尔·杰克逊的缘故这个词正在走红),在另一些场合则将这两种称谓互相置换了一下,不过“狗屎”改成了文雅的“比较逊色”,而有俚语嫌疑的“真棒”变成了“比较满意”。
你们明智而又高高兴兴地拉开了架势,借用埃伦·格拉斯哥的说法,你们“相互鼓励成为庸才”。争取成为一名一流以下几流的作家成了暗自弥漫的风尚。
你们犹如一批演出经验丰富得惊人,而不再进行基本训练的走江湖的歌舞演员(我们的时代称之为“走穴”的),到处留下了你们的身影和怒吼声,就好像你们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或者心声。
宽容一点的话倒也可以容忍这样一种比喻:如果有谁打算拍一部80年代的写实电影的话,你们刚好可以做景深处的点缀,你们和广告牌和进口汽车一样可以鲜明地点明环境,以及人们那晦暗不清、难以辨认的灵魂。你们用各类文凭和各种型号的录像机来标明时代同时也标明你们自己的位置,你们把这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并且自认为是这一演变的受益者。
在此之前,你们在北方或南方的乡村里蹉跎你们的早晩得蹉跎的青春。尔后,你们又玩得兴起,奔赴美洲或澳洲的城市蹉跎你们的青春之后的头十年,谁知道你们将来还会抛出些什么伤痕来扰乱你们自己或者别人的晚年。
你们跑到美国人的厨房里做起了中国菜,余下的人则在亭子间里观看美国录像,许多香艳的故事在太平洋上空荡来荡去,真是令人难以忘怀。你们用幻灭的语调说出的乡土故事和异国情调的反思作品搅得男女老少在波音客机的过道里来来往往忙个不停。
思乡还是背井离乡者的主题,而背井离乡则是所有叶落归根者的回忆。那些死守土地和黄鹤般一去不返的人则是真正的梦想者和自我放逐者。你们用寻欢作乐来包装你们的苦难,正像你们从前用苦难来诋毁你们的欢乐。
你们不得不两次放弃你们所熟悉的语言。前次放弃了习惯用法,后次放弃了语言本身。从1967年开始你们成了永远的外乡人。母语成了你们的回忆,成为一种美,而不再是工具。
文明所缺失的正是你们,而你们则以集体的失败和个别人的成功使这种缺失扩展为一个精神的深渊。与你们相错而处的人无一幸免都开始滑向这一具有巨大引力的内心所在。幻灭感、厌倦感、焦虑感、失败感、挫折感成了存在和选择的共生物。
你们的父辈和子孙都成了这个精神漩涡之国的弄臣,只有你们才是国王。你们的痛苦和偶然的幸福覆盖了一切。但是你们只留下了片言只语。记录下一切的诗篇将由另一些人来填写。你们只在精神的宫殿里留下了你们的回声。
你们的故事在大地上流传尚需要时间,你们可能看不到这一切了。
你们的墓地(如果你们有墓地)将是一个荣耀的所在。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中间夹着的较平庸的文学时代。你们是未来作品的“曼弗雷德”,而不是拜伦。但是这两者间的一致性,使许多人误认了你们。
你们这些疲惫的人们,你们同时在大街上,在家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与缠绕着你们的理念作战,你们以少许观念逻辑加上大量的情感在所有的场所都干了个天翻地覆,这种战斗造就了时代的氛围,并且化成理念最终在战斗中获胜。你们失去的是个人的情感和少得可怜的可信赖的价值系统。这些东西在你们的作品中尽情地流露。
作为一种必要的陪衬,自我肯定(你们也不知道要肯定什么)强有力地在作品上空回荡。作品的形式感被任意地与叙述顺序、精确的措辞、典型或者不太典型的人物、连贯性、对随机性的明确理解等同起来。你们知道事件的起因,你们对最初的动力有着强烈的爱好。你们偶尔也把意识指向未来(尽管它忽明忽暗),但是又抱怨这个与你们无关的未来过于缥缈。
尽管你们的外貌、品性各不相同,但毫无例外地只干同一件事,描写你们的内心。你们的精神历程组成了我们视觉中的原野。一种被描述出来的自然界在被反复描述之后被肯定了下来。与土地的关系,人伦的微妙变化,对风俗的沉思,有关性欲的记录,古代思想的援引,对垃圾堆般的城市的嫌恶和个人奋斗史的升华描写成为同时代人的食粮。你们怀着爱意蔑视这一切。
因为一些特殊事件打乱了你们与情人的关系,于是出现了弃婴和伤心的妓女,直至人口贩子和暴力因素的出现使全部出版物荟萃了所有的可能性。纯粹的文学和俗文学的话题的出现是这一处境的佐证。人们试图分辨这一切,因为几乎全部角色均已登场,相互指认和被指认地铁入口处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忽然消失不见了。
这是一个穷光蛋们为了过上舒心日子东奔西走寻求幸福的时代,至于那些继续在家中面壁枯坐的人无疑是一些比较固执的穷光蛋。两者必择其一。
这是一次个人的告别,但是我将在何处与你们聚首呢?像考利说的,你们“不愿意教导别人,也不愿意被人教导”。那么,所有这些人还有重新会面的必要么?
我所要辞别的似乎不仅仅是某些人,甚至是整个80 年代,在这十年中写作和开始写作的人,在下一个十年中还会继续写作吗?
我所有的诋毁都是赞美,反之亦然。
(本文节选自孙甘露所著《时光硬币的两面》,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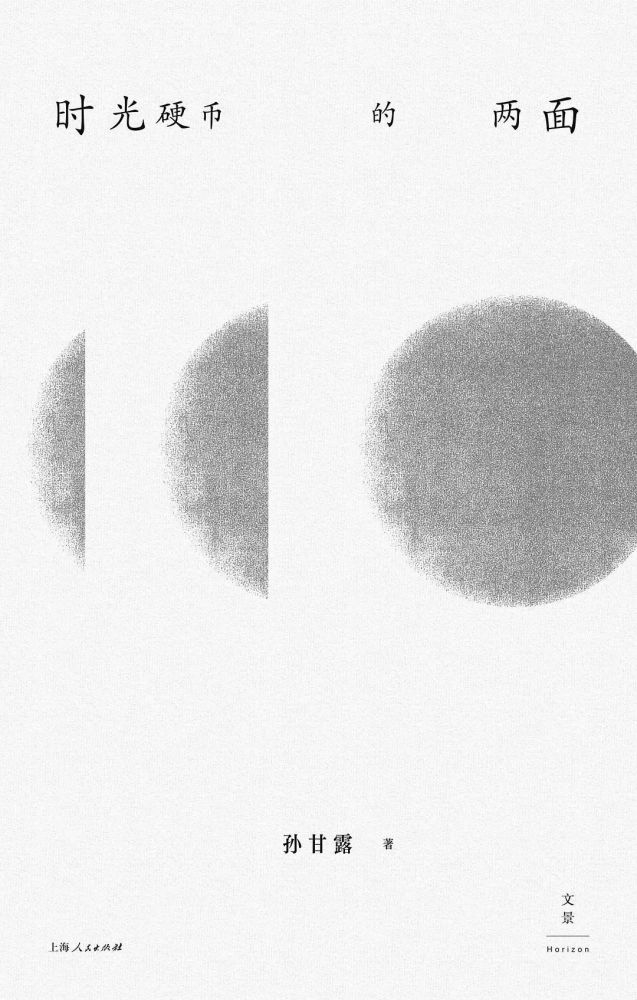
《时光硬币的两面》
孙甘露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5月
《时光硬币的两面》收入了孙甘露不同时期的随笔代表作。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灵魂的气息”共30余篇短文,从眼镜、洗衣机、电话,到睡眠、运动、散步,谈论日常生活的琐屑,不时闪烁幽默的微光;第二辑“我所失去的时代”回溯了80年代的记忆,包含作者对文学、艺术和创作的深邃思考;第三辑“上海流水”将目光定格在上海,记录了时光流转中的一个人与一座城市。
华文好书
ID:ihaoshu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