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父亲。”
 2021-06-23
2021-06-23

今天是父亲节,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母亲节时,脑海里能列出一火车的礼物清单,也能搂着妈妈的脖子肆意撒娇,但父亲总是以“不需要这些”、“不要浪费钱”等理由,把我们的关心和想念堵在胸口,如何对父亲表达爱成为一个共同的难题。
然而,在看过作家徐海蛟为早逝的父亲寄往天国的一封封“表白情书”之后,才明白勇敢破冰表达,珍惜身边眼前人的重要性。我们看到,无论是青春期的少年还是业已组建家庭的成熟男人,在这些父亲未能参与的生命重要阶段,徐海蛟一遍遍低声呼唤:“我需要一个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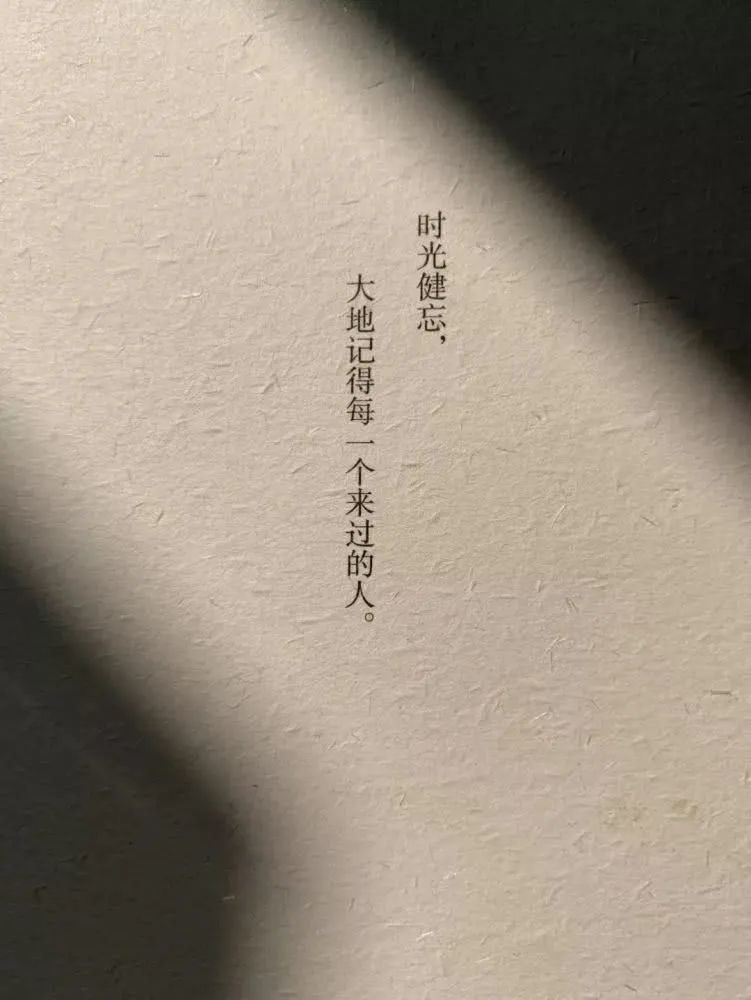
或许正是由于这份赤诚与温情,让徐海蛟的《山河都记得》获得了今年的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颁奖词将这部书写流离、记忆、爱与故乡的作品称为“用至诚之笔触写出了感情奔涌的生命之书”。

他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深情回望,那个依然生长在自己身体里的父亲。在四季更替的故土上寻觅,与父亲留下的气息再度重相逢。
《寻梦环游记》里有这么一句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的确,死亡是一场损失巨大的掠夺,而文字却能够找到缝隙,实现对真实世界的叛逃,重建一个崭新的时空和宇宙,弥补无情岁月撕裂出的伤口。

那么,这些深情缠绵的文字是怎样超越时空与逝者实现对话的?在强大的语言张力中又藏着哪些关于生命的永恒主题呢?进入徐海蛟的语言世界,我们能看见,一个人原已断裂的生命如何能够在亲人的记忆和想念中继续展开。
万物带来你的消息
文丨徐海蛟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得以避开1992年那个夏天的早晨。
如果那一天,三轮小客车的司机因为前一晚宿醉未醒拒绝载客;或者我突发一场急性病,由深夜腹痛辗转至天明;或者你走出家门时,被路旁一截树桩绊倒,正好伤及足部;或者三轮小客车急速行进中,突然爆了胎;或者天降大雨,车速就比平常慢出些许;或者你要坐的那个座位,偏偏被别人占了,你就挤到了逼仄窄小的车厢另一侧;也或者你没在走到村口时停住脚步,没有指给母亲看那片即将在明年变成宅基地的农田—你告诉母亲,明年将在此地建屋,我们就要有新房了。
父亲,以上这些命题,只要成立一个,你乘坐的简易三轮小客车只要快一秒,抑或慢一秒经过那个黑灯瞎火的十字路口,你将仍然留在人间。
二十六年过去了,我常常在脑海里回放 1992年夏天的情形。那个早晨,我明明七点多醒来,热好你和母亲留下的早餐,于一种莫名的空落里望着夏日白晃晃的阳光倾泻到门前田野。我看见稻子正在结沉甸甸的穗,田野由绿转黄。可在反复回想里,事实似乎变了一个样,仿佛有另一个我,正跟随着你和母亲往前走去,零碎的回忆拼接成了另外一种场景。我非常痛恨,在整个事件中,在死神向你发出召唤的早晨,我竟然没有作一丁点的抵抗。我无数次想,如果时光倒回,父亲,那个早晨我一定要更改这人世间最不公平的事实,我要和死神谈谈,不管你是否阳寿已尽,不管死神多么冷酷,只要他听得懂人话,只要他知晓世间的天伦之爱……父亲,我都要和死神谈谈,他没有权利在那个十字路口粗暴地将你带走。

但死亡一锤定音,从来不容置辩,不许说情和讲理。
父亲,你猝然离开后的二十六年里,另一个你却在我心里疯狂生长,像夏天野地里的藤本植物,枝蔓横生,根系探伸至每一个时间的角落。
十三岁,你离开后第一年,我需要一个父亲。在小学毕业的各种履历表中,我偷偷摸摸将你的名字仍然填在那些栏目里,我故作平静地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父亲还在。但字写得要比其他表格的小,落笔很轻,我知道那是因为不自信。一个已不存在世间的人,原本不用再填写他的名字,但我不允许他们在一张表格里忽视你。那一年,我和班上一个又笨又傻又壮实的男同学打了一架,后被班主任老师拉到办公室。打架理由简单,我去收他迟迟不交的作业本,叫了他父亲的外号,他反过来顺口叫了我父亲的外号。本来是一场还算公平的口角,我却认定自己父亲的名字不容亵渎,于是就有了身体的厮打。
十四岁,你离开后第二年,我需要一个父亲。幽暗的青春期像一个漫长的雨季,庭院深锁。少年的身体在成长中历险,我感觉到胸口的隐痛。我担心嗓音变粗,我厌恶粗糙刺耳的声音。我担心某个早晨醒来脸上会蛮不讲理地支棱起胡子,从而出落得像邻居的儿子那般丑—他白净的脸,一入青春期就长满胡子,有如进入春天的荒地疯长着野草。我更害怕青春痘侵袭,于平整和白净的面颊上布满粉刺和脓包。一个夜晚连着一个白天,一场水雾连着一片细雨,我在雨季的巷道里穿行。白天,我被觉醒的身体弄得坐立不安,夜晚,身体里的荷尔蒙又像拱动的小兽,一刻不能消停。这样的季节,我需要一个父亲,需要被一个男性的声音告知,男孩的身体在哪个时节醒来,又将完成怎样的蜕变,我需要弄清楚不安和悸动皆因生长所致。
十七岁,你离开后第五年,我第一次离家远行,我需要一个父亲。你应该走在我前面,帮我拎着那个人造革的黄色皮箱,我像你一样以右手的手指梳理头发,以左脚迈出门去。一个即将成年的人,第一次走向更开阔的世界,他要自己购买第一张客车票,他坐上嘈杂的客车,这时候父亲应该在身旁,以最少的话语叮嘱他到了外地如何与人相处,叮嘱他隔一个月往家里写封信。一个男人的远行要始于父亲,而归于母亲。
二十三岁,你离开后第十一年,一场痛彻肺腑的失恋击中我。我在自己的执念里难以自拔,以为只要借助爱情,就能留住世间任何一个想留住的人。这件事固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求医问药,只有父亲能告诉儿子爱的真相何在。我想会有那样一个时刻,我们静默地坐于灯下,在彼此面前倒上一盅老白干,就着一盘水煮花生,一碗青豆炒肉。我们是不善饮的父子,但有些时候必须有一盅酒,必须有呛人的白干,必须让它在经过喉咙时引发热辣辣的滋味,我们才能谈论从来避之不谈的事。依然不是促膝长谈,只在昏黄的灯下,说一句或两句话,但每一句话都是有响声的,像酒杯磕到桌面一般。父亲会说:“往后长着,爱情不独一份,要走很远的路,才能遇到共度一辈子的人。”
二十五岁,你离开后第十三年,妹妹遭遇一场凶险的感情危机。公司里一个男人追求她,两人恋爱不成,分手也不成。对方死缠烂打,不肯罢休。我们让妹妹全身而退,迅速离开了那家公司。对方气急败坏,不断电话骚扰,扬言若分手,就得留下一条胳臂一条腿,妹妹吓得瑟瑟发抖。这几近扭曲的人,时不时出没在我家附近,后于每天下班后等在公交车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野兽出没的威胁,我需要一个父亲,那时候危机的第一片阴影将落在你的额头上,而我只是那个站在你身旁的儿子,我只需和你一道注视着那片阴影,来分析明天我们如何应对。我需要父亲由阅历带来的智慧和勇气。
二十九岁,你离开后第十七年,结婚前夜,我需要一个父亲。新屋里敬神,红烛燃着,香烟缭绕,世界蒙上夜色。那一刻,我需要一个父亲。我们一道站在窗前,父亲会说出一盏灯火的意义,那也是世俗之于一个男人的意义。他曾经在深山里走过无数夜路,像风浪里沉浮的一叶孤舟,每一盏灯的出现都令他感动得想要呼喊。因了对灯火的渴望,因了远路的漂泊与游荡,我们才殷切地守护一个家国的梦想,就像守护寒夜里最后一团火光。
三十岁,你离开后第十八年,我守在产房门口,女儿于夏日的一个中午降临人世,在阳光最盛的时刻,生命完成了一个分支。父亲,或许你对女孩颇有微词,你向来格外看中传宗接代这类事。但我仍然期望,你能和我同在,我们一道迎接这个夏天里最奇妙的一朵蓓蕾。我渴望看到你抱起小婴儿的样子,那就是你自襁褓里抱起我的样子,也就是我抱起女儿的样子,这是生命的交接,由你的臂弯到我的臂弯,由你的寄望到我的寄望。
三十三岁,你离开后第二十一年,我躺在手术台上,等待麻醉。医生摆弄器械时的金属撞击声敲击着我的耳膜,那一刻,手术室里的冷几乎一下子夺走了我积攒三十三年的热量。我闭紧双眼,我需要一个父亲。我的父亲恐惧各种事物,唯独面对疾病,他有最大的胆量,我需要一个不说话的父亲,需要他坚定的眼神,需要他和我一起走到手术室门口时毫不犹豫的步履。
父亲,更多时候只剩下寂然。无数黄昏和夜晚,我独坐在橘红的霞光里,暮色像大提琴的曲调一般哀婉,有时候我伫立于窗前,细雨织出绵长的回忆,你的脚步再没有自窗外响起。这往后长及一生的时光里,你只以无尽的沉默示人。我以为,每一天都在远离你,越来越远,远到再也望不见你的一星半点。直到我成为父亲,我才明白,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大地上展开,在地理和时间里展开。一个人的生命同样也可以在人心里展开,在记忆和想念里展开,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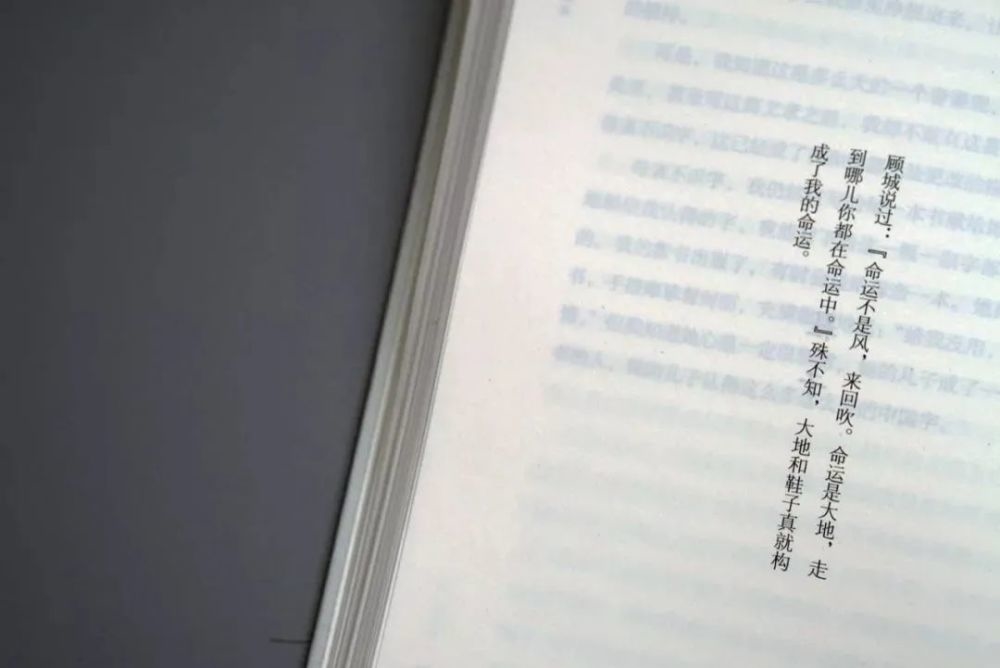
这样看来,一切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
父亲,当人的肉身消失,顺带除去了身体的局限和挂碍,也除去了来自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在这人间,我们从此以另一种形式相逢。而你,活在轻盈的欲望以外的世界里,你以无所挂碍的方式丝丝入扣地拥抱我们。我开始相信,无限事皆出于你的意旨。
你埋藏在我身体里,像一粒恒久的种子埋藏于无垠的土地,你借助我的血肉之躯生长为人间的一棵小树。你的血液成为我血管里的一股潜流,成为我骨骼里硬朗的钙质。你的味觉赋予我对食物的选择,我喜欢食肉,喜欢麦饼、年糕、面条……父亲,这些都是你的喜欢。每一回吃麦饼,我都要留下一截外围的厚圈,据说这也是你的一贯吃法。而现在,在一个餐桌上,女儿仍然和我不约而同将手伸向一盘包子,我们神奇地重复了曾经我和你同时将手伸向一盘馒头的动作。你的听觉,赋予我对是非的选择。那些藏在街巷里的困苦,那些日光即能照见的不公,那些发轫于远古的英雄故事,在进入我的耳膜后,都能激荡起与你心里相似的波澜。
你又俯身于万物,将自己分为我的千万分之一,让我在更宏阔的世界里逢着无处不在的你。
秋风乍起,寒雨和落叶带来大地的消息。那是你曾经劳作的大地,你在那里种植小麦和水稻,种植红薯和玉米,并以此养育年幼的我。那是你长眠的大地,是你的故事依然生生不息的大地。父亲,我将收到你的来信。你的生命消融在秋光里,消融在晚风和薄暮里。古老的九月像神秘的蓝色雏菊打开好奇的眸子,当秋凉平复我灵魂里每一处的褶皱,躁动与不安变得宁和服帖。父亲,我与你在秋天的黄昏相逢,你附着在一片边缘通红、中间如金的叶片上。那是你自小就有的魔法,你那样轻灵,在经过一棵大树的时刻,自我的目光里坠落。你知道我是爱树的,你拂过我的脸颊,轻拍我的左肩,这是深秋的召唤,也是父亲的问候。我们远隔着一个辽远的人间,远隔着生的全部愿望,远隔着一杯热酒,一碗白米饭,一件贴身棉衣,一声小婴儿的啼哭。父亲,我们又如此切近,近得我仿佛可以触到你沉思的目光。此刻,你就是我掌心的一片叶;你又是带着叶轻扬的这阵秋风;你还是满山在夕阳里闪闪发亮的茅草的穗子。
我在深冬的老屋里醒来,檐上的冰凌闪现晨光里第一道晶莹。父亲,那是你在童年时为我折下的一根冰凌折射出的光线,依然有着三十年前的剔透。多年后,你一定在一个冬夜想起我们早年的事来了。那些隆冬的清晨,下过一夜大雪,寒意吐着冷冷的舌头,你并不畏惧第一个钻出被窝,将一块瓦片搁到灶膛内昨夜藏起的余火上,再将红薯置于瓦片上。红薯慢慢熟透,香味穿过厨房,穿过干冷干冷的空气,钻进板壁,进入我们的鼻子,寒气被挤走了,一个新的日子就在这暖融融的香里开始了。
你光顾了这座故乡的老屋,你在木格子窗外凝视我们平静的睡眠,你听过我们梦里均匀的呼吸,留下这看似不着痕迹的礼物。
我相信更多的事物与你有关。在漫天而至的雪花里,那第一片和最后一片一定出自你的魔法,只是你不想那么快让我们觉察。否则,这两片雪花不会恰好落在女儿睫毛上。我相信北风的歌声也与你有关,你只是不想吓到我们,以至于总是那么遥远地在野地里吟唱,每当要靠近我们的耳朵了,又随即快速离开。

到了春天,你就有了更多魔法。你有办法让深黑的大地露出一张明朗的脸,你在一条我们必经之路上的水洼里投进一片好比孔雀羽毛般绚丽的彩霞。你在四月的樱花树上安插了一只红嘴的鸟儿,每当我从树下走过,就被那只鸟的鸣叫吸引,等我站定,樱花一片两片三四片,以轻梦和诗句的形式落向衣襟。父亲,这是否就是你的生命课?在一树花前,让我感念生之短暂与珍贵;在一树花前,让我无限接近你此后的轻盈,接近这春光一般绚烂的消亡。
父亲,你在每一段行程里,一程山水,一程云烟。你是我走出月台时,抬头遇见的那一片云。那一刻,出发的汽笛已响过,一片云朝我挥手,在轻缓的动作中,我看见别样的深意,那是父亲临别时才有的表情。你是我返回故园时望见的第一缕炊烟。我小时候,大家都还在,家里的人满满当当,声调各样的脚步声带着蓬蓬勃勃的朝气。每当炊烟升起,祖母便站到家门前喊外出劳作的人吃饭。祖母喊声嘹亮,对面远山传来回音,整个村庄都能听见,随后,家人便自各处汇集而来。父亲,你早就读懂了炊烟写在天空的寓意,你又重新变出了这个我熟知的戏法,让我在多年以后与故乡相视一笑,让我相信故乡是我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这是我们生命的应许之地。
一程山水,一程云烟。父亲,无尽岁月,我们都是长河里的一朵浪花,我们永远地别离,我们又无数次以另外的形态重逢。我坐在秋天的水边,面前一束束湖光逐水而来,父亲,这是你在爽朗地笑,你总是那样笑着逗引孩子们。我走在陌生的城市街头,人群中有一个背影,让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停了下来,我喜欢让目光追随一个陌生背影,直至他消失在黄昏街角,我相信那一个熟悉的背影或许就
是你。
你是黎明的晨曦,是八月山野里我能望见的最亮的星辰,是大海上风暴来临前,那一只一直在我船前徘徊的白鸟,你像闪电割开被乌云遮挡的航程。
你是我的犹疑不定,是我挥刀也斩不掉的优柔寡断。你是我的胆怯,是我的张扬,是我正直的部分,你是我那部分多余的爱。你是我摇摆不定的现实,是我对世界蓬勃的想象,你是我与生俱来的矛盾。你是我根深蒂固的人间欲望,又是俗世上那片不肯落入凡间的云彩。父亲,你借我的命继续活着,我是你一次一次的重生。在每个清晨,你醒来,在每个夜晚,你仍然不肯睡去,你进入我的梦里,你在我的呼吸里游荡,在我舒展开四肢的时刻绽放。
父亲,你是我另一个部分,既是遍寻不见的上游,又是摆脱不掉的宿命。你消逝于世俗的人间,消逝于柴米油盐酒菜面饭,又皈依于万物。你在我的每一段行程里,在我每一个置身的时空,悄然出现,又悄然离开。
你是我无影无踪的父亲,你是我无处不在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