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增加的社会,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本采访由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提供,内容有删减编辑。
提起哲学,人们经常觉得它和日常生活是两个极端。前者充满着大量复杂晦涩的理论,和后者的鲜活琐碎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提起哲学家,大多数人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康德那样离群索居、不苟言笑、总是背着手来回踱步的严肃形象。
和徐英瑾的交谈完全不会给人这种感受。他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授,在专业领域,他钻研“人工智能哲学”这类高深莫测的哲学学问,而在业余时间里,他写一部以三国为主题的历史小说。从纳粹的闪电战到托尔斯泰的小说,历史和文学常常成为他思考哲学的独特资源。他还上播客,在很受欢迎的《忽左忽右》上对《白色巨塔》等热播的影视侃侃而谈。
在新近出版的《用得上的哲学》一书中,徐英瑾写道:“哲学家要提高自己的常识感,而做到这点,并不是通过阅读哲学论文,而是要阅读许多非哲学性质的书籍,比如地理、气象、自然科学,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的书籍,来拓展自己的眼界”。
在这本书中,他尝试将抽象的哲学学问与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相连接,书写一种具备常识感的哲学书。
《用得上的哲学》,徐英瑾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5月版。
这种尝试会带给读者新鲜的感受,但自然也需要面对哲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
斯宾诺莎的身心一元论如何能帮助你观察企业的文化?怎么借助摹状词理论反对各种洗脑术?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反对,又给我们看待日常生活里的爱情以怎样的启发?用哲学的视角反思日常生活里的学问、连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固然会让人觉得脑洞大开,却也不免遭遇是否“曲解哲学”的质疑。
而在徐英瑾看来,对于哲学科普来讲,鱼和熊掌难以得兼,哲学的科普和通俗化一定面临一定的简化,作为专业的学者,他只能尽力做到表述准确,但最重要的,是读者能否从中收获对自己生活的反思。
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常常被当作哲学的代言:不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一过。反思,或许是现代人的生活摆脱不了的宿命,就像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在一个风险和复杂性都急剧增加的社会里,每个人都需要通过持续的反思来定位自身,并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哲学虽然看起来距离生活遥远,但它是潜藏在我们心中的一种反思的冲动。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ID:ibookreview
采写|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危卓 柳宝庆
1.
学哲学,首先要注重学语文
新京报:去年高考,有一篇被很多人质疑“不说人话”的高考满分作文引发过关注。那篇作文的话题和哲学也比较相关,徐老师当时有关注到吗?当时那篇作文被人诟病的一点,可能就是用一个很晦涩的方式去讲哲学道理,但和哲学本身清晰说理的追求背道而驰。
徐英瑾:撇开作文这个个例不看,其实整个中国文化在表达这件事上都没有很追求“把事说清”。我在这本书里专门花一节讲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它不仅是几条具体的规则,更多是体现一种讲道理的文化。不要用太多模糊的修辞,把话说得太玄虚,这是市场经济与法治文化成熟的社会的一个特点。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文本是合同,白纸黑字,不可以有任何模糊其辞之处。相反这两者越不发达、偶像崇拜文化越严重的地方,可能人们表达也更习惯于模糊和玄虚。
《罗伯特议事规则》,亨利·罗伯特著,袁天鹏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在书里把“语言”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用语言哲学来收束前面对逻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的讨论。在何种程度上研究语言是研究哲学的基础?
徐英瑾: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母语会奠定一个人思考的基本框架。我觉得语言是我们学习任何一门技艺、学科的基础,但是对哲学可能尤为重要。因为哲学的道理常常极为抽象深邃,而且总是有些缺乏实例,你面前的文本语言可能是你全部的学习物料。
我们会发现像康德、海德格尔这些大哲学家,他们的伟大体现在原创性的思想,同时他们表达原创性思想的语言也值得重视。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用德语表达过纯粹的有原创性的思想。在他之前的莱布尼茨-伍尔夫体系,伍尔夫尝试用德语来表述莱布尼茨用拉丁语书写的思想,但这并不是表达原创思想。这里就可以见出康德的伟大。
同样,海德格尔哲学几乎是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我们需要用他的那套语言去理解,才能接近他的思想。在美国,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敏感性,也至少是和律师一个级别的。
《纯粹理性批判》,(德)康德著,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我常觉得,现在哲学普及的困难,是大家中文都没学好,没有过语言关。在中国学哲学最大的基本功是语文。语文学习希望能够培养我们对长句子的把握能力,一个长句子来了,即便你听不懂,但要是能做到能迅速把主谓宾分清楚,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多时候哲学文本阅读,就需要很强的这种语言理解能力。
新京报:现在我们面临的语言学习环境其实并不好。
徐英瑾:是的,这个事也令我很无奈。现在社会的交流环境很不利于我们去训练自己对长句子的准确理解能力。我其实有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可能对“00后”这一代人来说听起来很受打击。我觉得语言学习的希望可以寄托在“10后”一代身上。我觉得他们赶上了一个新的技术时代就是“点读”时代,点读设备里面播放的语言至少都是标准的汉语,发音、语法都很规范。
2.
我们要不断去接近“真正的共情”
新京报: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把话说得模糊的模式——“金句”。金句的特点其实就是模糊,有很多解读的延展空间,但是它说的确实相当漂亮,所以堪称眼球经济时代的流量法宝。造金句基本上也成了很多自媒体的必修课。你怎么看这种语言现象?
徐英瑾:其实这是一种“谚语偏好”,它是心理学上“易取性捷思法”的一个变种。简单地来说,为什么我们喜欢金句?金句很短,往往押韵,朗朗上口,它有一种音韵上的和谐与美,和我们以前口口相传的谚语、歇后语一样。
而对这种语言韵律感的迷恋其实是一种人类固有的癖好,我在书里也有提到。在人类文化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对音乐的崇拜也是原始宗教崇拜的某种副产品。我们对它们的这种迷恋也是比较非理性的,比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都在提,但是它本身有逻辑上的道理吗?其实未必。
金句的短也方便和具体的语境相分离。当你无法理解金句和它诞生的具体语境的关系时,它确实很有可能被误解,但你也不太可能能从逻辑的角度反驳它。在当下的环境里,金句可以成为一种“吸粉”的工具,但它一定不是一种思考问题的工具。尤其是我们搞哲学的,特别需要警惕。
新京报:你写过这么一个观点,如果要提高我们的共情能力,可以多去阅读优秀的小说,因为优秀的小说家往往具有出色的共情能力。如今的很多问题,不管是“性别战争”,网络暴力,还是身份政治,其实都和共情相关。从哲学的角度看,你觉得人和人之间可能获得真正的共情吗?
徐英瑾:在共情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舍勒和卡尔·马克思这“二马”都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些启发。
舍勒做情感现象学,区分了不同的情感样态,初等的共情其实可能人人都有,我们看到小猫小狗被虐待,都会觉得痛苦,但是这和我们看到人被虐待,程度还是有些不同。同时,看到距离你更亲近的人被虐待,感觉又更痛苦。所以这个就很像费孝通先生的那个比喻,我们的共情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共情圈。所以舍勒觉得,教育和旅游,会让一个人的共情圈慢慢扩大。
而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这种共性圈更是和你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是一个股票经纪人,你在巴黎和柏林都有朋友,可能整个欧洲都是共情圈。同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表面上的种族斗争,其实也和对立双方所属的经济圈层有很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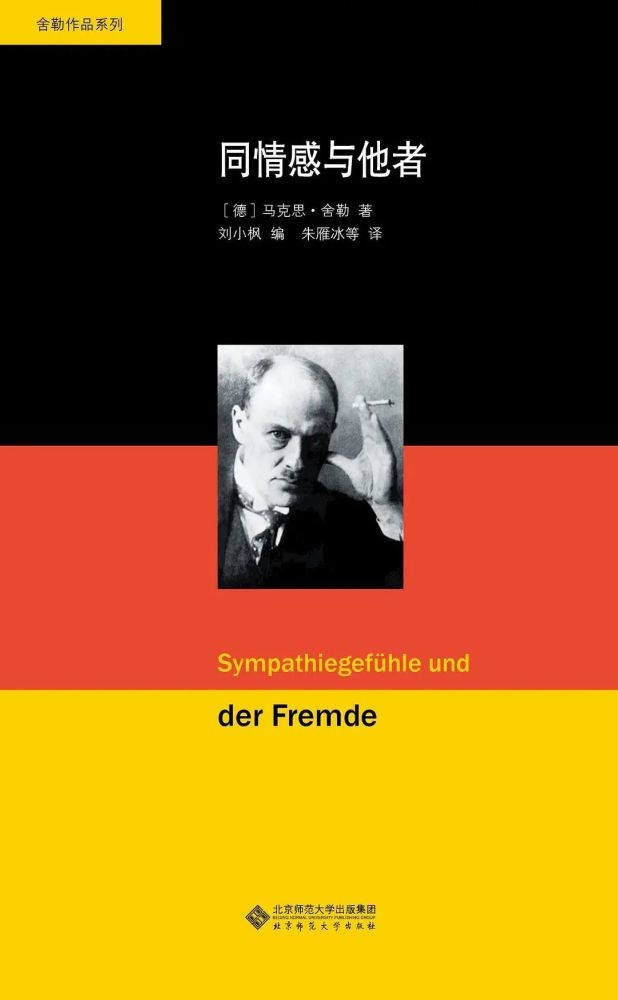
《同情感与他者》,马克思·舍勒著,北京师范大学2014年版
所以马克思让我们从一个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共情的问题。为什么阅读小说可以帮助人们培养共情能力?相对来说阅读小说是一种无利害的审美体验,看小说不是为了赚钱,相反,看小说需要花钱。我们是在挣脱了经济考量之后,纯粹地在小说里听其他“圈层”里人的故事,这对我们扩大共情的感知力很有用。
而所谓“真正的共情”,我们只能去接近。如果我们因为不可能达到百分百的共情,就否认共情的可能,那就会陷入怀疑主义。诚然,比如性别问题,有可能一个男性在认知上理解了女性主义的很多理论,但受制于具体的经验,依然对女性有很多的不理解,此时合适的态度应该是承认自己理解的这部分,然后去努力做得更好。不能因为做不到100分,就连已经拿到的分数都不去承认,这是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态度。
3.
哲学与日常生活:
反思一定会让生活更幸福吗?
新京报:你在《用得上的哲学》里试图为连接哲学和日常生活做努力,比如每一节的最后,都会有意识地用一个具体的场景来联系这一节讨论过的哲学思考。当哲学和日常生活场景相连接,它确实变得更通俗了,但这其中是否有简化乃至曲解哲学本身的风险?你怎么看待哲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这种张力?
徐英瑾:肯定是有简化的,只能尽量平衡。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希望哲学能够更好地抵达更多的人,那么此时“简化原意”的一点牺牲可能并非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代价。
现在国外的很多人,会把一些“金句”当成是孔子说的,可是其实不是,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些句子能影响他们的生活态度。同样,哲学进入日常生活,重要的是人们能从中收获属于他自己的启发,也许这个启发和理解并非完全遵照原意。这点可能和历史知识的普及不太一样。当然,作为写作者我一定是尽我所能地保证准确。
新京报:坊间还有一种常见的论调是,哲学提供的这种高度反思性的思考方式,会让人把生活中很多简单的问题越想越复杂。特别是当我们把生活里的很多现象、常识解构、分析之后,反倒更痛苦了,所以有句金句讲“懂了很多的道理,却还是过不好一生”。你怎么看哲学反思本身的限度和风险?
徐英瑾: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也提到过,他有一个比喻就是有关这种“哲学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像一只苍蝇在一个透明的牛奶瓶里面乱飞,瓶口其实就在前面,但是就是飞不到口,还撞了一头包。
我们如果用哲学去反思日常生活,确实有过度反思的风险。很多时候我们从生活里抽象出了一些反思的对象,但是却忘记了生活本身。我之前参加一个播客的时候,提了一个有关河床和河流的比喻,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根基,那个河床,如果我们的反思触及到了这个层面,很有可能会影响一些生活的基本信念,是有风险的。所以在学哲学之外,常常观察生活里大家是怎么说话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报:我们知道,很多哲学思考都会借助“思想实验”。比如大家熟知的“缸中之脑”、“电车难题”等。“思想实验”其实也是哲学比较“出圈”的一种方式,像基于“缸中之脑”实验的电影《黑客帝国》就是一种通俗化的哲学表达。思想实验对于我们思考哲学问题有怎样的影响?其中的利弊如何权衡?
徐英瑾:思想实验是一种对复杂现实的抽象,思想实验的抽象程度可能比自然科学里实验的抽象程度更高。自然科学里我们可能能模拟一个近似真空的环境,但是思想实验抽象的是更复杂的社会现实,很难做到“真空”。这导致思想实验模型的解释力常常会被质疑。我个人认为哲学的思想实验只能作为我们初入哲学问题时候的一种工具,但不能作为一种深入研究的普遍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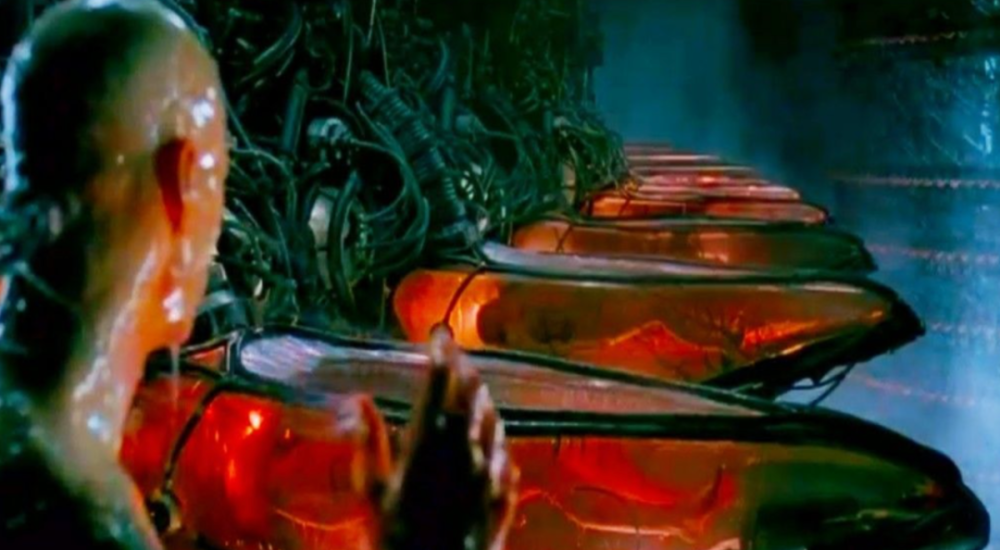
《黑客帝国》剧照
新京报:思想实验因为比较形象,很多时候也给人们一种错觉,觉得思想实验很容易找到漏洞,很好反驳。人们对哲学的态度有时候也是这样,会觉得人人都能评说两句。
徐英瑾:思想实验在专业的哲学文献里面,在正反两个方向上通常会有十几二十几个回合的辩论。大众看思想实验或是哲学里的很多问题可能就是其中辩论的第一个回合,所以觉得它好像没那么复杂。哲学问题思考的起点往往不是很困难,但是越往后会越复杂。
4.
不够“聪明”的人工智能
对人类威胁反而更大
新京报:大众读者提起哲学,往往想到的都是一些欧陆哲学家的名字,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之类的(当然,看不看得懂另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欧陆哲学会很重视哲学史的研究和对哲学家的文本进行精细的研究。你自己的路数比较偏英美分析哲学,这本书也是更多以问题而非哲学史的逻辑组织架构的。你怎么评价目前欧陆和英美这两种哲学的做法?作为一个主要做分析哲学的学者,你又怎么看待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徐英瑾:不管是哪种做哲学的方式,都是很重视哲学史的。哲学这个学科的特点就是当下很多前沿的问题,其实都能在很古老的问题中找到思想资源。所以我们在做今天的很多哲学研究时还是经常要回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二者的差异可能在对待“读书”这件事的态度上,英美分析哲学可能更强调哲学问题本身的永恒性,把提出这个问题的古人看成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一样的人。相对来说欧陆哲学更重视哲学家的思想和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之间的联系,强调把哲学思想放入到特定的那个时间脉络中去研究。
虽然两种做哲学的思路都研究哲学史,但是对待哲学史的态度还是非常不同的。由此其实也引起了一些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对立。可能很多欧陆哲学研究者会觉得分析哲学研究者把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们的问题直接移植到当下思考,对待哲学史上的那些圣贤不够严肃。
不过这里说一句题外话,在哲学阅读上,我个人觉得相对于历史细节,学会思想框架是比较重要的。在文化传播上其实同样如此,比如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注定是需要进行一种移植的,并不是要让人家原模原样完全接纳我们的很多文化细节,而是传播一种文化的框架。
至于你说的大家谈起哲学,为什么都是谈欧陆哲学家,我觉得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肯定有传播学上的原因。比如萨特,除了是哲学家,他也写戏剧,很多时候他也会用一种很文学化的语言,甚至就通过戏剧这种形式来传播他的哲学思想,传播效率比起分析哲学这些枯燥的论证当然更高。
萨特的戏剧卖得特别好,《存在与虚无》反而卖得不好,当时在巴黎被称为“一公斤”,因为《存在与虚无》正好可以当一公斤的秤砣用。还有很多别的欧陆哲学家的语言也有这个特点,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用今天B站的语言来说,他们可以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圈子里“吸粉”。
《存在与虚无》,让·保罗·萨特著,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新京报:总体来看,现在英美分析哲学的崛起势头比较明显,哲学也越来越和科学进行密切的互动。你在这本书里也多次提及哲学与心理学、神经科学这些学科之间的关联。去年中科院也成立了哲学研究所,在你看来哲学和科学目前有一种怎样的关系?
徐英瑾:哲学和科学原本也是不分家的,近年来可以说是回归了二者之间的联合。比如以我自己研究的人工智能哲学为例。很多人都觉得人工智能只是一个科学领域的问题,哲学家帮不了什么忙。我觉得哲学在这个前沿领域里至少能发挥以下的作用。
首先是整合。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这样还在成长的并不成熟的学科领域,整合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等知识。其次也牵涉到很重要的伦理、法规问题,这部分可能专门设计人工智能的专家不一定考虑的清楚。
如果我们再追溯久远一点,最早的一代人工智能是符号人工智能,其基础的技术逻辑就是数理逻辑,这本身就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领域。所以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哲学和科学之间渊源深厚。
当下我们更多地都是把人工智能当成单纯的技术,可是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还是要深入到塑造它的文化和思想土壤中去,比如人工智能从观念上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产物,它的背后是逻辑主义、机械主义的思想,我觉得哲学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公众理解人工智能这些新概念背后的这些思想、文化基础。
新京报:说回人工智能问题。最近几年有关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走向的预测很多,一部分学者甚至担心所谓“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会威胁人类的生存。你觉得人工智能未来可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吗?开个脑洞,假设我们确实面临需要与人工智能并存的局面,你会持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吗?
徐英瑾: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你说的未来是多远?把时间尺度拉到无穷远,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我们谈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可以预见的未来,我觉得不太可能诞生强人工智能。虽然我在心灵哲学上的观点是反对“神经学沙文主义”的,即认为关于“智能”的一般原理,也可以在非神经元环境中出现。但从既有的现状来看,大规模的通用人工智能研发成功的迹象几乎没有。
很多人会谈论AlphaGo战胜李世石,这件事有很大的工程学上的意义,但是科学的意义我觉得其实有限。在工程学的意义上,围棋很难下,现在我们能让机器下赢人类,无疑了不起。但是它所运用的包括深度学习或者蒙特卡洛算法等,其实都是早就有了的东西,底层的逻辑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AlphaGo击败李世石和多年前卡斯帕罗夫被深蓝打败,没有本质的差别。

李世石与AlphaGo的比分战成1:3,其中胜利的一局也是人类智慧面对AlphaGo的唯一一场胜利,为了纪念这场胜利,近日李世石战胜AlphaGo的棋谱以NFT形式保存并拍卖,最终以60以太坊(目前约合13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到目前为止,即使是AlphaGo这个级别的人工智能依然距离你所谓的强人工智能很远,它还是一个专门人工智能,只能在某一个功能可能比肩甚至超越人类,但还不是一个通用人工智能。AlphaGo的脑子生来就是为下围棋服务的,但人类的脑子并不是设定为了做某件特定事的。
我写作的《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马上要出版,这本书里面我提了一个基本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相对于用来实现特定功能的这种专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反倒是对人类比较友好的技术。不聪明的人工智能——我们现在调侃的“人工智障”——反倒对人类威胁大,它不够智能,所以需要大量的数据、我们的隐私来做分析。相反如果人工智能真正进化到和人类一样聪明,反倒可能没有那么依赖大数据,它会拥有更强的推理能力,对我们的隐私等反倒没有特别大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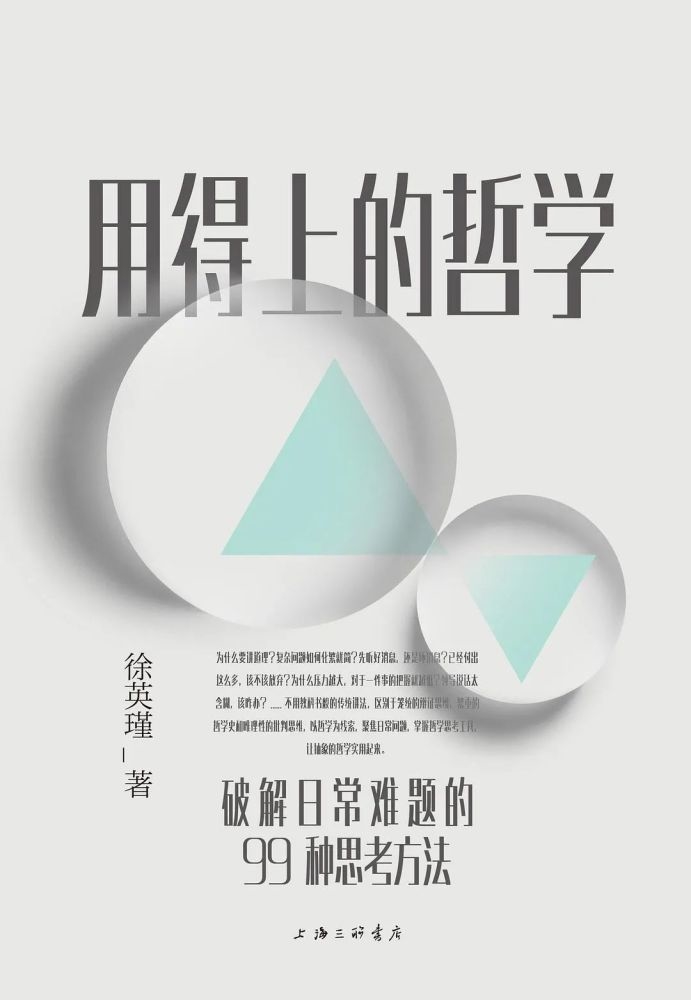
用哲学反思日常,做出自己的生活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