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帝国》读书会棉花之外,有无“帝国”?

4月13日,复旦大学董少新教授发起的东亚海域史研究团队,联合艺术考古读书班,共同习读并讨论了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此书出版之后,在学界内外均引起广泛反响,并在近日格外成为中文知识界的焦点。
十余名校内外师生围绕此书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讨论。话题涵盖物质文化的全球流通、资本主义与全球史书写范式、“棉花帝国”与中国、陶瓷与棉纺织品的差异等等。本文在尽可能保证对话临场感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润色,并经发言人审阅。限于篇幅,本次读书会整理稿分三篇发布。本文为第二篇。
全球史应有什么样的写作方式?
邓菲(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这本书有全球史的视野,也继承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它把棉花作为一种取径和视窗。书中有很多反传统的观点,也有新的关注点。作者重视全球的农村,妇女儿童,这些关注点的改变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贝克特在书里说,资本主义变革的中心不一定是从我们以为的欧洲中心开始,而有可能是其他的区域。这方面有一点点反传统,而且很多的学者也认为他跟马克思主义是有关系的。
贝克特在澎湃新闻的访谈
里自己讲得很清楚,他提到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带给他很大影响。当然马克思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他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是有预见性的,但与马克思相比,贝克特更强调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全球生产,而不是首要关于欧洲的。他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有异质性、特殊性的。这种异质性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棉花帝国中会有分流,会有不平等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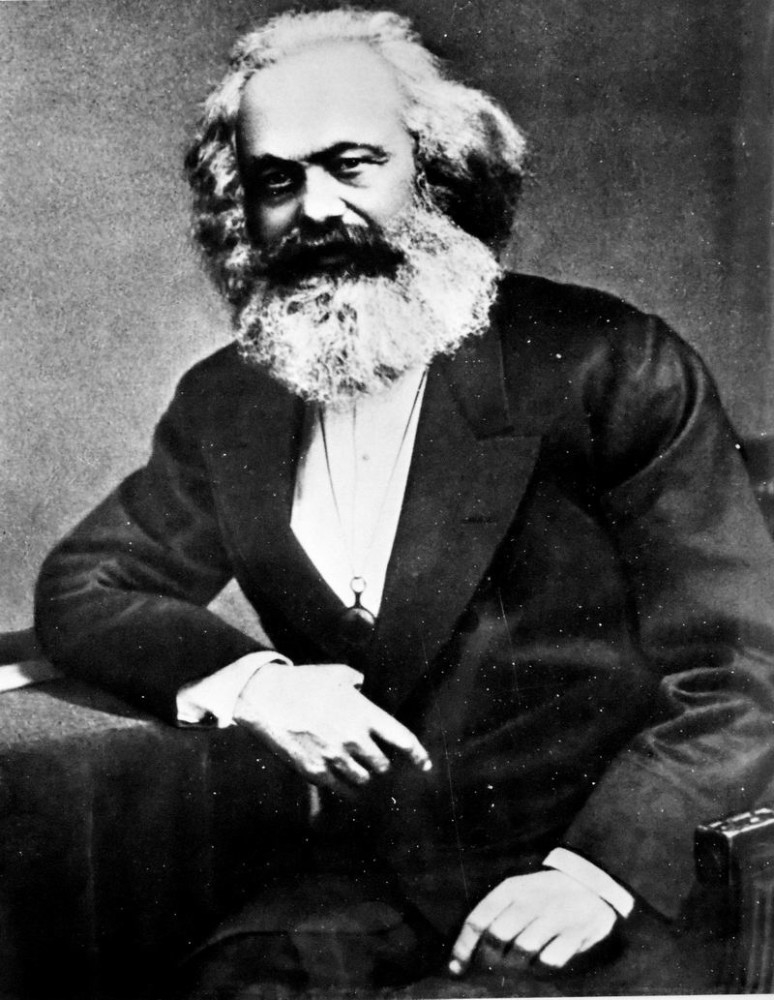
马克思
另外,贝克特现在也被打上了很多标签,比如“有老牌色彩的社会史学家”。还有人认为他其实是新资本主义史学家,这些形形色色的符号都很有意思。但我其实有一个小的问题:他在这本书里面不断强调棉花是一个透镜,棉花的特殊性和代表性。他也讲到,对于棉花帝国所做的论断不适用于其他商品——糖、咖啡、香料或橡胶,可能就无法构建出这样的一个全球网络。所有商品都处在这个全球的交易贸易网络中,可是只有棉花可以构建起这么整合的一个网络。
姜伊威
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其实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棉制品就是最大宗的一个全球贸易体。
邓菲
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当你换成另外的一种物质、商品或原料的时候,还能否重新构建、重新书写出这样一个世界体系?如果能的话,当然很有趣,可以讨论它们的关联和交互;但如果不能的话,会不会一定程度上挑战到它的合理性?因为棉花太特殊了。当然,这种特殊性是本书的有趣之处,但如果我们换成陶瓷——类似于奢侈品——或者更加常见的商品时,这种叙述如果没有复制性的话,那么由其他物质或商品所构建出的资本主义图景或是全球体系是何种面貌的?这关系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所建立起来的全球贸易体系是不是真正屹立不倒的?他讲棉花写得非常有说服力,我们也基本相信他在这个框架下所做的种种叙述。但棉花之外的其他商品应当怎样去理解?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董少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我个人认为他讲棉花的特殊性,以及它与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形成的关联,的确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更有典型性,这是有道理的。而我的问题是,仅仅是棉花的话,充不充分?学者们做过很多研究,譬如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作用——茶以及糖都是国际贸易品,再譬如东南亚的橡胶园,在20世纪也很重要——我们需要轮胎。
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前,棉花还有多大程度上的代表性?譬如工业革命之前香料、白银,当然还有瓷器——如果把所有这些重要商品都统合起来,再与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形成关联起来,是否更有说服力?但所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棉花这么有代表性、这么有串联力,这也可能就是棉花的独特之处。

青花执壶,明代永乐年间瓷器(青花瓷),南京博物院“江苏古代文明展”文物。
但我也不太相信《棉花帝国》这一本书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就像邓老师一直强调的,棉花只是他的一个视角——棉花是作者进行资本主义时间之旅所乘坐的一辆小火车,纵向地观察了一遍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但并不一定说资本主义就起源于棉花,可能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个相伴的历程。
姜伊威
棉花有一点和其他商品不同的在于,它从农业环节,制造业环节,再到消费,几乎串联起了所有的经济领域。
朱莉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棉纺织业之所以成为欧洲工业腾飞的前提,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棉纺织品最初进入欧洲的时候,跟欧洲传统的毛织品产生了竞争关系。这是其有别于其他在新航路开辟以后大规模进入欧洲的外部商品的特点。因为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商人们要求国家禁止进口棉纺织品,以保护本土的毛纺织品,这就表现为国家保护主义。棉纺织品作为欧洲传统毛织品的挑战者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同时又存在着通过技术来提高产量的巨大空间,因此大大激发了欧洲工商业者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所谓资本主义通过让外部劳动力提供原材料以及内部的技术革新,使英国成为新的纺织业中心。
这里面可以联系到《大分流》的内容。因为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当然有销售问题,传统的贸易网络对欧洲的棉纺织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推广作用。这就像马克思说的,世界贸易的存在先于工业化,工业化产生的本身就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之上。
因此,棉纺织品先是作为一种欧洲原有毛纺织品的竞争品,在欧洲进行了产业化之后又声称了世界网络,制造出新的需求,一方面让这些地方的农民去生产这些商品,同时又在创造新的需求。所以,新航路开辟之后的全球化贸易网络,一直能够串联到工业革命这个时代。
中国在里面被讨论的比较少,在这本书里面的篇幅不如印度多。书里也说到,中国在14世纪的时候,已经有纺织机的革新了。但为什么没有出现更进一步突破的技术革新呢?
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就是李约瑟难题。
姜伊威
我讲一个私人经验。2018年的春天,中国丝绸博物馆办了一场很大的展览,展示了全世界各地传统纺织的机械,还办了研讨会,主持的学者是白馥兰(Francisca Bray)。这个展览很全面。之后的几个月我走访了江浙地区几乎所有的纺织博物馆,那段时间看了很多的纺织机。这些纺织机器的原理,如果看多了也就基本能一眼看懂,也能分辨出不少来。像中国传统的大花楼机,已经非常复杂和庞大了,但依然是用比较简单的机械原理工作的。
后来我在南通看到了张謇大生纱厂的机器,没记错的话是两台丰田的梳棉机,非常庞大。因为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很多传统的纺织机了,而这两台丰田机器给人的冲击是非常直观的,那种震惊就像日本人第一次看到黑船一样。我们作为当代人尚且会感到传统纺织机器和工业时代的巨大差距,盛宣怀或张謇这些清朝人,看到这个机器会是什么感受呢?你会感到之前再精致的技术都是没有办法与之相比的,它所需要的动力人力,完全不是一个几何量级。

张謇的大生纱厂
高晞
日本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主要优势是不是技术差距?机械化程度比中国纺织厂要高?
姜伊威
从技术上讲,到1920年之后,当时华商纱厂的技术已经不弱了,也可以生产高支纱,但因为市场分工里处于弱势,即便有技术也只能以生产24支以下为主,主流产品是12-16支纱。日本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占了甲午战争的便宜。只要拿住不平等的条约,就可以占领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因为中国厂商面临的根本问题,还是一系列的制度不平等。
技术上的瓶颈不在纺织,而是在机器业。当时纱厂用的机器,的确是要通过洋行向欧美日本购买,自己生产不了。
高晞
谢程程,你再展开讲讲李约瑟难题?
谢程程
李约瑟难题是说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没有发生在中国。关于李约瑟难题有很多回应,有学者认为这是伪命题。但我觉得,在全球史的进程里去思考,我们可以给这个命题什么样的回应?我觉得贝克特没有往大分流的动因和真正起点去展开。书中有章节提到,有的国家成功有的国家失败,我觉得本可以作为一个节点,但是他并没有在书中明确表达那是否就是大分流。
陶瓷与棉花,是否共享了同一个剧本?
刘朝晖(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刚才讲到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让我联想到了近代的瓷业。李松杰的研究就是关于近代瓷业。我们以前在做中国近代瓷业转型研究的时候,只是想到似乎要回应现代化的这个叙事议题,但是不是还可以用全球视角来看待?
当时的景德镇,譬如康达等人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就试图推广机械生产。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想到了和刚才几位老师一样的问题,并在思考是否有可能作为一种替换,用同样的视角来写一部瓷器帝国?当然这个很难,因为可以写一部瓷器的全球史,但瓷器可能和资本主义的联系就没有那么明确。还有就是前面同学说的,在研究跨文化艺术史的时候,除了传播和流通角度之外,还能谈什么?讲完“中西之间”之后,还能讲什么?我们做物质文化史研究,还是要去回应物的问题。
邓菲
也许我们只回应物质层面的问题,积极的反响不会很大,毕竟社会经济的层面才是更大更受关注的问题。
姜伊威
陶瓷的问题,李传鑫曾经和我对过一次数据。汪敬虞先生主编的那套史料集里,把纺织分在了工业部门,陶瓷分在手工业部门,这个分类虽然老套,但是1950年代学者们的思考仍然有相当大的合理性。比如工人数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我们看到景德镇的一个瓷器工厂人数大概在500人左右,而上海的纺织产业工人是几十万人。如果讨论很重要的劳工问题,五百人的工人抵抗可能只构成一般的地方性社会事件,但纺织工人的有组织罢工,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李松杰(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
刚才王老师提到,贝克特这本书指出的棉花的特殊性。我联想到罗伯特·芬蕾《青花瓷故事》,也是全球史视域下物质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但有别于棉花的全球性流动,瓷器具有不同的商品属性:“包括传统艺术手法、国际贸易、工业发展、政治纷扰、精英阶层的支出、仪式礼俗和文化接触等。”我结合个人的研究,即近代景德镇瓷业与社会文化,谈下我的看法。我认为正是瓷器不同于棉花的特性,为近代景德镇瓷业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从微观视角来说,他们可以依托世代传承的手工生产模式生存下去,没有动力和必要接纳现代大工业生产体系。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全球现代化的多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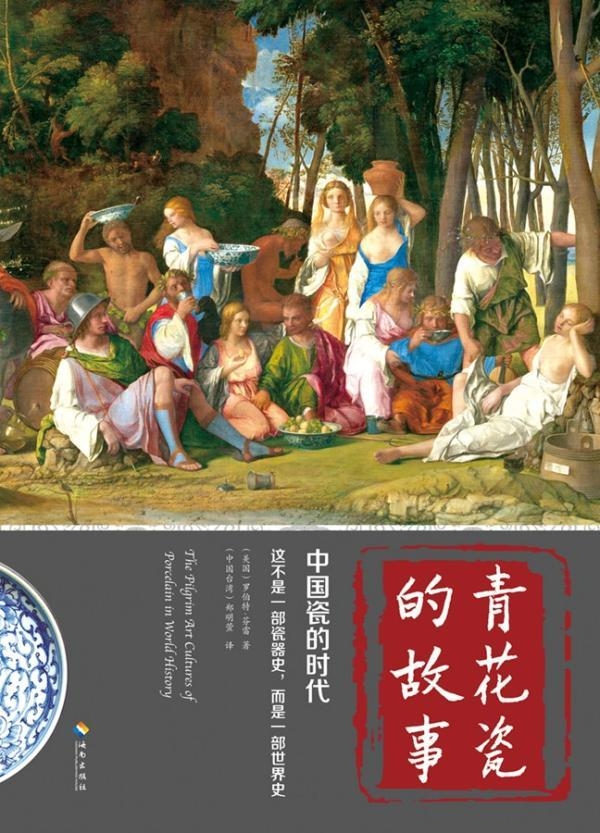
《青花瓷的故事》
今天回过头来看,从近代的竞争、所有的改革,包括大工业化,如果认为西式资本主义有特殊性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国家力量的特殊性。从近代以来,国家力量一直尝试着融入到这样一个乡村区域中心去,但是景德镇的瓷业从业者一直成功抗拒了西式现代化,在学习借鉴中寻求“第三条道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景德镇手工制瓷模式的复兴,景德镇又回归了从中心扩展到四方的状态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式手工现代化”的合理性,我认为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李传鑫(复旦大学文博系博士生)
我回应一下之前刘老师的问题。我陶瓷相对于棉花来说,有很大的限制。雷德候的《万物》讲到过陶瓷工业化的前身。但是我们谈到工业化——陶瓷跟棉花最大的不同在于,除了生产工业化,它还存在着一个装饰的工业化,这一点上棉花是不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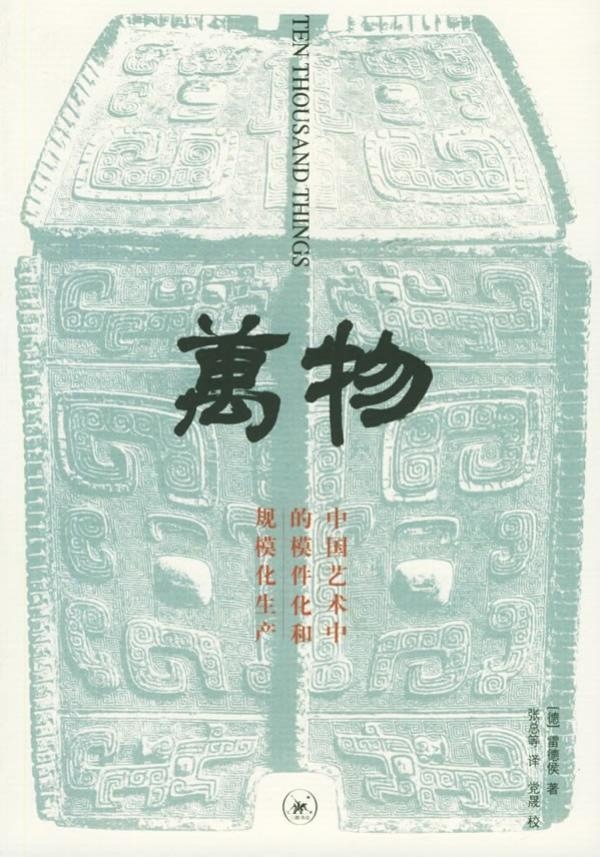
《万物》
这个装饰,就是它最大的限制。我们能够在旧的形态下把它模件化,所有的花纹都是一部分一部分。它会做成纯工业化的装饰,全部都一样,一张花纸全部贴出来。半手工装饰是将类似于透明的塑胶纸、沿着选定好的纹饰轮廓插出连串的小孔,然后敷在坯胎上,用植物颜料刷出装饰轮廓,能够做到趋于标准化,或者放大缩小的种种组合,但仍然是手工完成的。看过这本书的应该都知道。但是这也就极大限制了它无法像棉花那样成为全球商品。它是一个奢侈品的定位,手工限制决定了它的产品性质。
我和李老师做的其实是相同时段,我也研究景德镇独立的手工运作体系,也是想近百年来景德镇如何去对抗工业化,它又是靠着它的这种装饰的无法工业化,去对抗它完全的机械工业化。
百年梳理下来,从康达到晚清的洋务运动,一直到1930年代杜重远来景德镇改革,到建国之后大的意识形态下来,似乎有了成功的“工业化”,但它保留了原始的手工形态,大工厂之下的手工生产部门一直保留。1990年代大国企崩塌,但是保留的那一块依然是正常运作的。一直到现在,景德镇依然能够被称之为世界瓷都,也是因为装饰的半工业化状态一直维持。
另外补充一点,棉花或许无法和陶瓷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比对。棉花作为生产成品的原料,在陶瓷的生产体系里对应的是陶土或者被称作适合生产精致瓷器的高岭土(kaolin)。回到刘老师提出的问题,如果要按照同样的思路这一本陶瓷类的“帝国”,书名可能要被定为《瓷土帝国》或者《高岭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