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译者的“他者”思维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反观——以《古诗十九首》为例
 2021-07-01
2021-07-01

本文来源:《长江学术》2021 年第 2 期
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致谢!
作者简介:谢艳明(1968—),男,湖北赤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诗歌与诗歌翻译研究。
摘 要: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的诗歌阐释观点后,中国自古以来的诗词研究者们无不皓首穷经地解读古典诗词。然而,受常态化的汉语文化思维结构的影响,许多古典诗词文本得不到充分的多角度的阐释。翻译是译者使用“他者”思维对原文本的检索和阐释。在外域文化思维介入之后,译者会得出与传统训诂不同的阐释,并且从中国古典诗词文本中发现逻辑思维、叙述结构等多方面的问题,从而产生更传神合理的译文。
关键词:他者思维 叙事语法 叙事逻辑 诗词翻译 文本阐释
DOI:10.19866/j.cnki.cjxs.2021.02.009
苏轼在《题西林壁》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一个人长期置身于某个事物之中,反而不见得认识它的“真面目”。中国是诗词的国度,自古以来,诗人们创作了不计其数的优秀名篇;中国也是诗教的国度,诗词教会我们语言习得、立身为人乃至“治国平天下”。许多诗词我们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并且引用起来信手拈来。我们如此热爱诗词,如此重视诗词,对于本国文化里的诗词,我们是否能完全认清它们呢?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了“诗无达诂”的阐释观点,许多诗词都可以从多角度去理解,即便是诗词研究专家、大学者们,也不敢说能全方位地阐释一首诗。不能全方位阐释诗词,除了因为“诗无达诂”的本质外,还会因为我们身在中国文化之中,会受到常态化了的汉语文化思维结构的影响,跳不出思维的局限。虽然译者的阅读行为很难超越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话语体系的规约,但翻译场毕竟是“自我与他者相遇的一个接触区”[1]。翻译是译者使用“他者”思维对原文本的检索和阐释过程。“他者”思维是对“我者”思维的突破和补充,当“他者”思维反观古典诗词文本时,译者会突破固化了的单一文化思维,会发现传统的训诂之不足及局限性,从而对原文本产生全新的认知和阐释。
一、诗词翻译中的
“我者”与“他者“
翻译既是两种语言的沟通行为,也是两种文化的交互行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文化是语言的生命气息。没有文化,语言就会失去灵性,成为没有灵魂的符号。语言与文化自然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从文化中产生,也会不断地培植和规约文化。因为一种语言以及由该语言产生的知识会给我们提供习惯性的、可以预测的(predictable)、可以计算的理解,让我们按既定的模式去辨识事物和书写事件,因此,语言在培植和规约过程中形成特定的文化思维结构。这种结构像基因一样,可以遗传,形成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即特定语言中常态化的思维结构。用李泽厚的话说,就是“积淀”,它是一种持续的社会记忆的积聚,通过它,人类个体被社会化并且适应某种文化。“积淀”也就形成了“文化心理结构”[2],人类认识的“结构”是人类具有历史性和文化特殊性的共同经验的功能。可以说,每一种语言的文化思维结构都是独特的,与其他语言存在差异性。每一种文化思维有其独特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会养成对本文化的“习惯性地缺乏理解”[3]。
翻译就是外语思维强行介入本族语思维结构的行为,在翻译过程中,外语与本族语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对源语言文本进行解码和转换,另一方面对本族语的思维结构进行检索和解读,从而突破了一种语言相对稳定的思维结构,更好地认识其局限性。本文设定源语言——汉语——为“我者”,译入语为“他者”。“‘他者’(Other)是相对于‘自我’(Self)而言的。‘自我’必有‘我性’(selfhood)或‘同一性’(sameness or identity),‘他者’必有‘他性’(otherness)或‘他异性’(alterity)。”[4]“他者是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只有在我与他者的对话情景中,我才能认识我的存在。”[5]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汉学研究和翻译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的研究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研究之不足。他以自身的经验和体会总结说:“以自我为参照,我是不可能理解我自己的,我只能参照那个不同的东西 因为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既听不到别人听到的声音,也看不到自己的脸(若不借助于镜子)。”[6]由于译者通晓源语言和译入语,并且对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也是熟知的,能够运用两种文化的思维模式对文本进行阐释,所以他在面对原文本构建产生译文的脑文本时,必然综合了“我者”思维和“他者”思维。
“我者”思维与“他者”思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主要是由于语言表达的差异和文化思维模式不同而引起的。汉语与英语在语法规则上存在很大差异,并导致文化思维的不同,因而诗歌的传释活动也有差别。汉语,尤其是古汉语,语法比较灵活,词与词及句与句之间保持着松散的关系。英语的词语要组成句子,句子要组成篇章,需要很多“细分的元素”[7],如名词前要加冠词,定位定关系需要前置词和连接词,动词的变化要与主语、时态和语态保持一致性的关系,等等。“英文中的法则,其任务是要把人、物,物、物之间的关系指定、澄清、说明。”[8]汉语(包括文言文)其实也有语法规则,但相对于印欧语系来说要宽松得多。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字句还能突破这一宽松语法的限制,进行“自语法解放”[9]。宽松的语法规则使得中国诗歌的词句之间和诗行之间具有离散性特征,在逻辑上也不那么紧密,就如诗经中起兴的诗行与主题诗行之间的关系那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似乎是意义之外的“音韵”将它们衔接起来。而英语诗歌的词句显然要注重语法和诗意的衔接以及逻辑联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典型的英语思维的产物,它们的篇章结构与英语散文基本一致,如《第18首》(Sonnet18)开篇由一个问题引出主旨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然后从反正两方面论证(夏天如何不好,“你”如何比夏天更好),最后做结(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马韦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的《致他羞涩的情人》(To his Coy Mistress)甚至运用“三段论”(syllogism)的逻辑推理。此诗第一节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我们的世界足够大时间足够多,小姐,你这样的羞涩就不算罪过。”(Had we but world enough, and time./This coyness, Lady, were no crime.)第二节用“but”来个转折,“但是在我的背后我总是听见,时间插翅的战车匆匆飞近。”(But at my back I always hear/ Time’s wingèd chariot hurrying near.)最后一节用“therefore”得出结论,“让我们趁现在大好时光玩个尽兴”(Now let us sport us while we may)。像这样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写的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是很少见的,汉诗无论在篇章结构还是诗意表达上要松散得多,也随性得多。
灵活的语法使得中国古代诗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拼接组合诗句,甚至读者都可以参与其中,将原本不属于同一首诗的诗句拼接起来,组合成新的文本。如“一枝红杏出墙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等等。这些拼接的诗行并不是当今的网民们首创出来的,古人将这种诗句拼接称作“集句”,即从不同的诗篇中选取现成的诗句,再巧妙地集合成新诗。汤显祖的《牡丹亭》总共55出戏,集句诗就有54首之多。比如,第52出《索元》王大姐上场诗:“残莺何事不知秋,日日悲看水独流。便从巴峡穿巫峡,错把杭州作汴州。”[10]第一句拼接自李煜的《秋莺》,第二句拼接自王昌龄的《万岁楼》,第三句出自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第四句出自林升的《题临安邸》。“这种灵活性让字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读者在字与字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解读活动。”[11]这无疑是汉语诗歌的一大优势,印欧语系的诗歌无法具备这种叙述上的灵活性。然而,汉语诗歌中离散性和灵活性叙述往往导致逻辑不严密和叙述的纰漏。不过,中国文化常态化的思维结构往往使得汉语读者对此视而不见,习以为常,并认定为理所当然,因而在阅读过程中不会去深究这些缺陷,或者说,这些缺陷不影响他们的阅读和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将汉语诗歌翻译成英语,我们会运用英语的思维结构检索源文本,在“他者”思维的作用下,汉语诗歌中的一些逻辑缺陷和叙述纰漏更容易被识别出来。以下,本文以《古诗十九首》为例探讨译者的“他者”思维如何反观古典诗词。
《古诗十九首》是创作于东汉末年的一组古诗,其集子名称来自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他将当时传颂的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中,并冠以此名。这十九首诗都没有正式的篇名,我们习惯将每一首的第一句定为题目[12]。这十九首诗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艺术成就极高。近两千年来,它们得到了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们的盛赞。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在其巨著《文心雕龙》中称它们为“五言之冠冕”[13],他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的《诗品》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也。”[14]甚至当代的诗学大家叶嘉莹都说,“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15]在历代诗词评论家们看来,这十九首诗是完美。运用单一的“我者”思维模式,我们或许不能全面地阐释和评价它们,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看作为五言诗中的极品。这种习惯性地缺乏全面理解,“不能缓解我们自我膨胀的感觉”[16]。这十九首诗无疑是艺术成就极高的,因此喜好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译者们往往会选译或全译它们。然而,笔者阅读它们的英语译本时,在英语思维的检索和反观下,发现这十九首诗优点是十分明显的,但缺陷也是存在的。本文主要以汪榕培、西顿(J.P.Seaton)、辛顿(D.Hinton)的译文为例反观这十九首诗。汪榕培的译文入选“大中华文库”;西顿和辛顿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兼汉学家,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颇深,他们的翻译是在文化思维作用下的对原作的反观,具有典型的“他者”思维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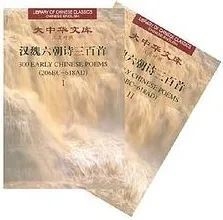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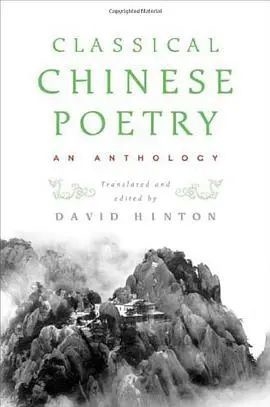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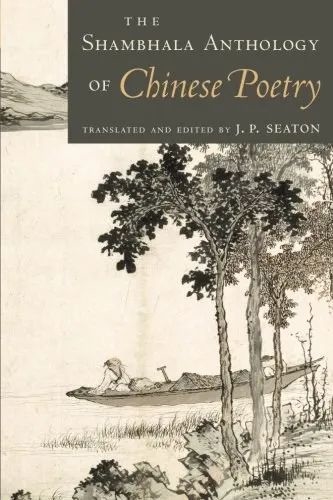
二、从叙事语法视角反观
《古诗十九首》
前文已讲过,汉语文本在语法结构上缺乏许多“细分的元素”,诗词的行文表现出主词模糊、时态不清、字词关系不明、方位不确定、篇章结构不明朗等特点,这些不确定性给翻译造成一定的障碍。在汉译英时,译者往往需要明确这些不确定性。比如,《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行行重行行》,叶嘉莹认为它是一首“易懂而难解的好诗”[17]。其“难解”之处——“难译”之处——就在于这首诗中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第一句“行行重行行”没有主语,也没有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但译者往往要确定好主语和动词时态,于是就进入了两难选择:到底是远行人还是送行人做主语?行的动作是过去还是现在发生的?动作执行者是男子还是女子?没有“他者”的介入,这些问题我们或许都不需要解答。第二句“与君生别离”也是个无主句,不过交代了第二人称的宾语“君”(“君”也可以界定为第三人称),但仍然不能确定到底是远行人还是送行人“与你硬生生地分别了”。下面两个译文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视角,译文一是送行者(或在家的思妇)对远行者的话语,译文二则是远行者对居家者的话语:
1. On and on, alas, on and on!
Far away from me you will be gone! [18]
2.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gain,
from you, my Lord, my love, I’m parted in this life.[19]
在时态上,汪的译文采用将来时,似乎远行者(you)和叙述者(me)现在还在一起,远行者将要远行,叙述者正在送行;西顿的译文采用现在时,似乎远行者已离开。接下来“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从临别分手时的悲伤情感中“一路接写下去,一句较之一句为遥远,一句较之一句为绝望,从渐行渐远的日益加长的万里的距离,到天涯阻隔人各一方的清醒的认知 ”[20]当然我们无法明确这一段是远行者的叙述还是送行者的叙述。此诗最后两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也是解说纷纭。“弃捐”既没交代主词也没交代宾词,谁抛弃了谁,或抛弃的是人还是物?“勿复道”是“你不要再说了”还是“我不再说了”?“努力加餐饭”是“要你好好吃饭”(尽管被抛弃,仍然关爱着对方)还是“我要好好吃饭”(好好吃饭,保护好自己的身子以待君子)?汉语读者也许不需要深究这些问题就可以理解这首诗,然而,译者则不然, 他必须弄清楚这些种种不确定性。以下两种译文分别代表了这两种阐释:
1.I can’t tell you how abandoned I feel,
but I’m eating well, building strength.[21]
2.Do forget about it! Let it be!
I hope you’ll eat your fill and be carefree![22]
西顿将这两句诗译为“And so my heart will say no more than this: try hard to stay well” [23],他忽略了“弃捐”这个词,模糊了“谁要谁保持好身体”, 尽管有漏译之嫌,但也不失为一种解释。译者站在 “他者”语言思维的立场上要弄清楚这首诗的种种不确定关系。然而,当译文明确了这些关系之后, 译者只能以一种明确的关系译出一种故事来。
这首诗和许许多多中国古典诗词一样省略主语或宾语,取消指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前置词,使得叙事“时无分古今,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事无分远行与送行。” [24]它只是建立一种叙事或抒情的“基型” [25]。这种“基型”的极其高明之处在于它可以构建许许多多的故事来。《行行重行行》中各种不明确的关系任由读者围绕这个“基型”去阐释,去构建故事。遗憾的是,将其翻译成英语时,译者只能采取“妥协”(compromise)的方式翻译出其中的一种故事,因为英语语言的“细分的因素”无法生发出多故事来。
另外,标点符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更是不确定的,因为古汉语原本就没有标点符号。一些诗词在加上特殊的标点符号——如引号——之后,语法结构明确了,叙事抒情显得更加生动。《孟冬寒气至》中有四句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如果仅仅使用逗号和句号将诗行隔开,这四句诗就只是描述性的话语。西顿将这四句译为:
A traveler from afar has come
and brought a missive meant for me:
“I’ll forever think of you,”it opened
and ended“long though we be parted.”[26]
他将描述性的话语译成直接引语,诗中叙述的故事一下子就生动起来,情趣横生,拉近了读者与故事的距离。由此可见,借助“他者”思维,通过西方语法结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和理解中国诗词中的叙事“基型”,还可以拓展诗词阐释空间。
三、从叙事逻辑视角反观
《古诗十九首》
作为“五言之冠冕”的《十九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完美,还存在着一些叙事逻辑方面的不足,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在单一的“我者”视角里不容易被发现。而这些不足之处在“他者”思维检索之下,很容易呈现出来。虽然“逻辑”(logic的音译)是个外来词语,但这并不是说中国自古没有逻辑,只不过我们称之为“名学”。中国古典诗词其实也讲究逻辑结构,也有“起承转合”逻辑自洽的概念,但是中国诗词很少运用诸如“三段论”这样的逻辑手法,诗人们更注重于感性的阐发,而不是理性推理。他们往往注重于含蓄,以“不说破”和“绕路说禅”[27]取代理性的逻辑。在一些诗中,离散性的事物联系和松散的语法结构会使得诗词叙述出现前后叙述矛盾、逻辑结构不合理、前后不照应等现象。
虽然《迢迢牵牛星》被誉为中国爱情诗的佼佼者,虽然其结尾两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极为出彩,但此诗却犯了一逻辑错误,那就是前后矛盾。此诗一开始用“迢迢”叠词描写牵牛星和织女星(河汉女)之间相隔遥远,其倒数第三四句却说“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银河的水清,而且不深,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这与开头的“迢迢”相矛盾,前面不是说他们相隔很遥远吗?这里怎么又说“相去并不远”?他们相隔只是河的两岸,而且可以对望。或许我们可以用现代文艺批评中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解释开头是遥远的地理距离,结尾是说并不遥远的心理距离,似乎这样可以将矛盾转化过来,但是这一解释未必适合中国古典诗词。
很多译者或许发现“相去复几许”阐释为“牵牛与织女相去能有多远呢?”与开篇的“迢迢”是矛盾的,因而将“复几许”的距离描写忽略而不译,以避免前后矛盾,如西顿的译文:
Afar, far off, the Herd Boy,
White, bright, the maiden by the River in the Sky.
The River in the Sky is clear, and shallow,
yet how shall they ever cross, to meet again.[28]
这一前后逻辑矛盾还出现《庭中有奇树》一诗,如果我们按照近两千年来沿用的对“奇树”的训诂。“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这首诗写一个思妇对远行的丈夫的深切怀念之情。由树及叶,由叶及花,由花及采,由采及送,由送及思。诗的开头就说庭院里长的是一棵“奇树”。按照很多学者的理解,“奇树,犹嘉木”,即“非同一般的树”,自然是珍稀的了。朱自清认为“奇树”来自蔡质《汉官典职》:“宫中种嘉木奇树”,不是平常的树。然而,此诗的结尾又说“此物何足贵”(这棵树上长的花儿谈不上珍贵),这不自相矛盾了吗?汪榕培将此诗译为:
In the courtyard stands a tree so rare,
With leaves so green and flowers sweet and fair.
I pluck a flower from a twig above,
To offer as a token of my love.
In my laps and sleeves, sweet fragrance stays.
But flowers will not reach him who’s far away.
Such a gift is not the worthy kind;
Long parting weighs alone upon my mind.[29]
将“奇树”译为“a rare tree”,将“何足贵”译为“not the worthy kind”,显然不但没有回避掉这一前后矛盾,并且将其更加突出出来了。当然,汪榕培的翻译是依据近两千年来对“奇树”的阐释。这首诗到底存不存在前后矛盾呢?笔者查阅了《说文》对“奇”字的解释,其中一条说“奇,一曰不偶”。此处的“奇”是“奇数”之意,即“不成偶、不成双”。在东汉末年,“奇”已经有“不偶”之意了。《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云:“奇肱之国,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此诗中若将“奇树”训诂为“不成偶的树,孤单的树”正好可以比拟独自在家的思妇,她虽然已婚,可是丈夫远行在外,留下她一个人守着空房,这不跟“不成偶”一样的吗?庭院中的这一棵树,是一位困顿于闺房中的孤单女子。
可见,有时诗词语篇本身不存在上述问题,但受固化的单一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受从一开始的“权威”阐释的引导,一些诗词的阐释有失偏颇。当我们试图将它们翻译成英语时,经“他者”思维的检索,我们可以发现按照传统阐释翻译可能出现语言理解和逻辑等方面的偏差。
《迢迢牵牛星》还存在着结构不合理,前后照应不足的问题。此诗头两句用“迢迢”和“皎皎”的描绘,引出“牵牛星”和“河汉女”(织女星)两颗星星,比喻相爱而又不能相守的两个恋人。不像莎翁的《第18 首》开头提出对比的双方,接下来从这两方均衡拓展开来抒情,这首诗从第三句起着重描述“织女星”对“牵牛星”的思念,而没有一句单独描写“牵牛星”的话语。这种抒情描写没有照应开头两句,造成了不平衡的心理感应。我们再读辛顿的译文,这种不平衡的感觉特别明显:
Far, far off the Ox-Herd star drifts.
And the Star River’s radiant lady—
she weaves shadow-and-light finery,
her shuttle whispering, whispering
all day long. She’s never finished.
Her tears fall, scattering like rain.
Star River’s a crystalline shallows,
so thin keeping them apart, a mere.
wisp of water brimming, brimming.
They gaze and gaze, and say nothing.[30]
阅读此译文,读者会感到第一句很突兀,它既不充当全诗的主旨,也不引出下面诗行。当然,这不是译文的问题,而是原诗就缺乏合理的、平衡的叙事抒情。《青青陵上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诗人经过洛阳北邙山的一片坟地,看到了小山丘上长满了青幽幽的柏树,他想到了躺在坟墓中的人,然后联想到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瞬息而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既然人生如此短暂,那么我们就该快快乐乐地活着,要抛弃烦恼,活得有质量。自古以来,酒便是提高快乐商数的重要工具。诗人劝朋友姑且喝一盏酒,相互娱乐一下,不要计较酒的多寡和薄厚。“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让我们驾着驽马到南阳城和洛阳城去嬉戏游玩,这样可以暂且消除内心的积郁,让人忘却烦恼;出游可以感受外部世界的快乐,让身心愉悦。然而,此诗的后半部分并没有提到南阳,只说洛阳。“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诗人描绘了洛阳的繁华景象,以及宫观林立,雕梁绣柱、画栋飞甍的“王侯第宅”, 最后以“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就让我们尽情享受这豪华的盛宴吧,使我们的内心得到愉悦, 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乐呢?)做结。可是,前文提到的“南阳城”在后半部分只字不提,后文不回应前文,这不免给读者内心添堵。
经过“他者”思维的检索,我们发现作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还存在着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明月皎夜光》开头的四句“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这句四句描写自然景观时一会儿写天上,一会儿写地上,一会儿又跳上天,一会儿又落下地,显得叙事失序,有点混乱。一些诗前后主题不一,如《东城高且长》不像是一首诗,而是主题不同的两首诗。还有一些诗在描写人生志趣时前后境界不同,《今日良宴会》的前部分本来是抒发人生失意或不得已的彷徨苦闷,却写得意气风发;后部分的主题发生了变化,转入了人生无常的悲叹,并且要求读者赶紧谋取高位占据要津。
翻译活动过程往往是译者的“我者”和“他者” 思维的综合过程,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本阐释“转换成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问题,即如何形成文化间的互恵理解,提高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和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从而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要做到这一步,只能‘从他者出发’,把自己的偏好悬置起来,从而看见他者、听见他者,进而理解他者,建构文化的多维视野” [31]。中国是一个诗词大国,诗词训诂实践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我们不能封闭在自我的理论和方法中,必须与世界融合, 让“他者”文化思维介入进来。“中国文化的单一视角有局限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文学(文化)外译是跨文化行为这一命题的认同。仅以一种视角考察文本跨文化转换与这种行为的跨文化属性不相匹配,这种行为的分析需要超越单一的自我文化视角。” [32]正因为“他者”思维可以提供一个文本阐释的新视角,突破单一的“我者”文化思维形成的偏见、局限,以及看不见的死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传统阐释的偏差,还可以扩展传统的诗词训诂,甚至补充其不足。中国诗词的阐释要注入自我视域中的他者,在他者镜像中寻找自我, 这不仅可以扩展中国诗词的阐释空间,克服单一的自我文化思维的局限,还有助于寻求更合理、更传神的译文,有益于中国诗词文化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学的共同体。
注释
[1]周宣丰:《文化“他者”翻译的权力政治研究》,《外语教学》2014 年第 6 期。
[2]李泽厚:《美学四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36 页。
[3][6][16]〔德〕顾彬:《“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读书》2006 年第 7 期。
[4]周宣丰:《文化“他者”的翻译:后现代哲学“他者”思维的启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7 期。
[5][31]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7][8][9][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 页。
[10]〔明〕汤显祖:《牡丹亭》,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88 页。
[11]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
[12]《古诗十九首》在《昭明文选》中先后出现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和《明月何皎皎》。
[13]〔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58 页。
[14]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成都:成都古籍书店 1996 年版,第 30 页。
[15]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9 页。
[17][20][24]叶嘉莹:《迦陵谈诗》,北京: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20—44、32、28 页。
[18][22]汪榕培:《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1 页。
[19][23]J. P. Seaton.The Shambhala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6), 54.
[21]D. Hinton.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105.
[25]“基型”是叶嘉莹在其著作《迦陵谈诗》中探讨《行行重行行》的叙述方式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但她没有在书中给出定义。根据上下文,这个词指作者创作一个“元故事”,任由读者穿梭在这个“元故事”中间,凭借自己的理解去拼接组合故事。一个故事基型可以生发出多个甚至无数个故事来。中国古典诗词的奇妙之处就是诗人可以利用汉语的优势构建故事基型,而且这个基型是充盈着情感的。
[26][27]J. P. Seaton.The Shambhala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6), 58,56.
[28]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85—89 页。
[29]汪榕培:《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1页。
[30]D. Hinton.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105—106
[32]吕世生、袁芳:《中国古典戏剧翻译的他者文化视角——以汉学家阿林敦、艾克敦的〈戏剧之精华〉为例》,《国际汉学》2017 第 4 期。
转自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