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子兴|哲人其萎:异端与教授的思想合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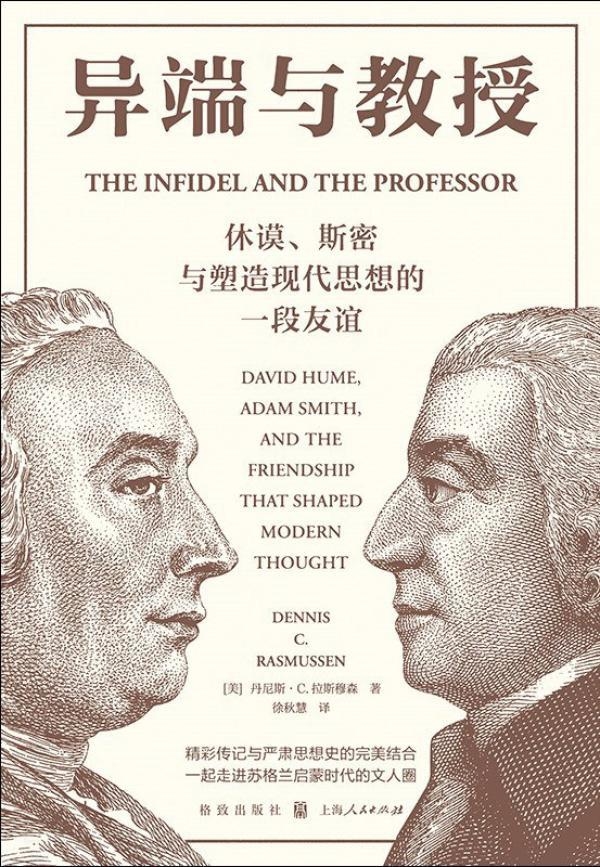
《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美]丹尼斯·C.拉斯穆森著,徐秋慧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388页,88.00元
一
1776年8月25日,大卫·休谟溘然长逝。与苏格拉底之死一样,大卫·休谟的死亡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哲学事件。丹尼斯·C. 拉斯穆森(Dennis C. Rasmussen)注意到,早在《自然宗教对话录》出版之前,休谟就有不信神的恶名,所以他的死亡就成为一件备受期待的事情。这个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当然是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在生命终结之时,休谟是否仍然坚持他的怀疑论。人们假设,不知悔改者在面对死亡时会感到悲痛与绝望。每个人也都想知道,如果他将怀疑论坚持到底,他是否会经历这种悲痛与绝望”(Dennis C. Rasmussen, 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99)。
人们翘首以盼,想要看到死亡对休谟及其学说构成的挑战。然而,对休谟而言,人们的广泛关注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以趁机对其哲学做出最后的、最有力的证明与辩护。对休谟而言,死亡不是一个无法逃避、只能被动接受的厄运,而是他积极做出的行动。他像苏格拉底一样,以一种超然的、无忧无惧的方式去世。在临死之前,他仍然保持振奋的精神、快乐的心境,以及对朋友的关爱。他的死亡反而展现出强大而热烈的生命力。他的一生就像一团持续燃烧的火焰,其死亡则像是焰火,将生命的华彩完全绽放出来。休谟因此声称,临死前的岁月恰是他最该重过一遍的人生阶段。
我很少因为疾病而忍受疼痛,更奇怪的是,尽管我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但我的精神未曾有片刻不振。如果要我指明,在我的生命中,哪个阶段最该重过一遍,我将会选取这段最后的时期。我一如既往地维持着对学习的热情,以及同样的与人交游的快乐。除此之外,我认为,对一个六十五岁的人而言,死亡只是让他少过几年体弱多病的生活。尽管我也看到,许多征象表明,我的文学声誉终于迸发了新的光彩,但是,我也知道,我原本也不会有许多光景来享受这份声誉。与今时今日相比,我很难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一种对生命的超然态度了。(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245)
在1775年春天,休谟的肠道疾病持续恶化。他预计大限将至,遂着手安排身前身后事,积极准备自己的死亡。据拉斯穆森的叙述,休谟为死亡所做的准备工作中,有三项至关重要:督促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安排《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出版,写作《我的一生》。

休谟
二
1775年5月,斯密曾在一封写给休谟的信札中透露,他将在“这个月底或下个月将书稿交付出版”(《异端与教授》,格致出版社,2021年,220页,以下仅标页码)。对于焦急等待的休谟来说,这封信不啻一巨大安慰。然而,苦等至次年2月,休谟仍然没有见到该书出版,以至于再次提笔给斯密去信。“据我多方面了解,您的书已经付梓很久了,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广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20页)休谟在信中猜测,斯密可能过于关注美洲事务,以至于耽误了作品的出版。于是,他又劝斯密,“如果您一定要等到北美殖民地事态尘埃落定后再出版,那您可能还要等很久”。不仅如此,休谟认为,美洲殖民地事务不像斯密想的那么重要,其著作还是应该尽快出版为宜。在这封信中,休谟也谈及自己的健康状况,并邀请斯密来家小住。“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差,几天前我称了一下体重,发现轻了整整五英石(合约三十二千克)。如果你耽搁太久,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221页)
事实上,在休谟与斯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生涯里,休谟对《国富论》的关心只是一件寻常小事,算不上他为死亡所做的专门安排。当然,在与斯密经年累月的交流中,休谟或许早有期许,认为《国富论》必将是一部非凡之作,他希望在离世之前看到这部皇皇巨著的出版,如此方能不留遗憾。《国富论》最终在1776年3月9日出版发行,斯密给休谟寄送了赠阅本。4月1日,休谟便给斯密寄去贺信,表达他看到此书成功出版后的兴奋之情。“精彩!干得好!亲爱的斯密先生:我为您感到高兴,仔细阅读此书后,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休谟也对著作内容略作评述,认为“此书思想深刻、内容可靠、观察敏锐、文中提供了大量如此新奇有趣的实例”,并认为“它最终一定能吸引公众注意”(2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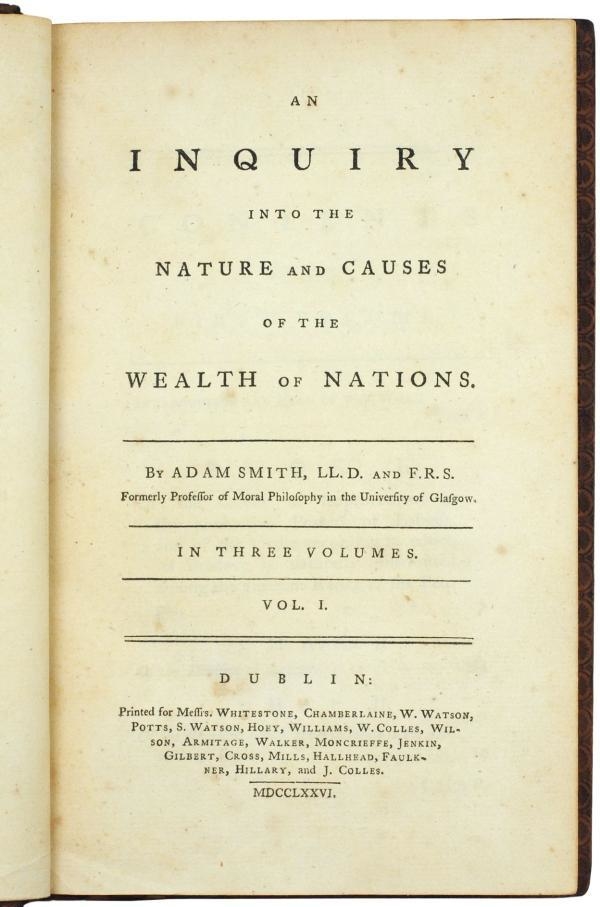
《国富论》
在《国富论》出版前后,休谟与斯密鸿雁传书,两人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实际上,他们是可堪托付彼此遗志的至交。对哲人而言,遗著的出版、学说的弘扬与流传是性命攸关的事,必须托付给最亲密最忠诚的人。1773年,斯密身体欠佳,感觉自己命不久矣,遂前往爱丁堡与休谟相会,指定他为遗稿继承人。斯密与休谟约定,如果斯密的健康情况到了无法亲力出版《国富论》的地步,他会将手稿邮寄给休谟,请休谟与出版社交涉出版事宜(217页)。在临终之际,休谟也向斯密“托孤”。1776年1月4日,休谟起草了遗嘱。这份遗嘱指定斯密为其遗稿执行人,并希望他在休谟去世后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
休谟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完成《自然宗教对话录》初稿,并在往后的岁月中反复打磨修改。休谟在生前一直珍藏着这部著作的手稿,未将其交付出版,只寄送给几个最亲近的朋友阅读。对这部著作,休谟表现出罕见的谨慎态度。因为,在这部著作里,休谟最尖锐、最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异端”思想。依据拉斯穆森的解读,休谟在创作《自然宗教对话录》时,将其对宗教的批判系统性地冶为一炉,综合为一个“具有毁灭性的整体”。在这篇对话中,休谟揭示了设计论证与第一因论证的弱点,也证明邪恶问题极难得到满意解决,并质疑了宗教为道德与政治带来的益处。于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严阵以待,将其怀疑论武库收拾停当,对宗教展开了密集、全面的进攻,没有为虔敬的读者留下任何出路或避难所(265页)。
《自然宗教对话录》是休谟对宗教思想发起的总攻或决战。休谟充分理解这场战役的艰难与凶险,他必须全力以赴、心无挂碍。在休谟看来,只有死亡才能为他创造这样的条件:休谟的挑衅与攻击必然会激发信众的怒火,但到那时,怒火只能向死者喷射,不再能影响他的情感,也不至波及亲友。不治之症让他窥见了时机,他开始借助遗嘱,积极安排出版这部分外珍视的作品。在休谟心中,亚当·斯密是助其实现遗志的首要人选。但是,斯密秉持一贯的审慎行事风格,对休谟的嘱托有所保留。休谟最终调整遗嘱,请出版人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承担起确保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职责。为了稳妥起见,以防斯特拉恩在其死后五年内没能出版书稿,休谟又将副本的所有权留给了斯密。1779年,休谟过世三年后,《自然宗教对话录》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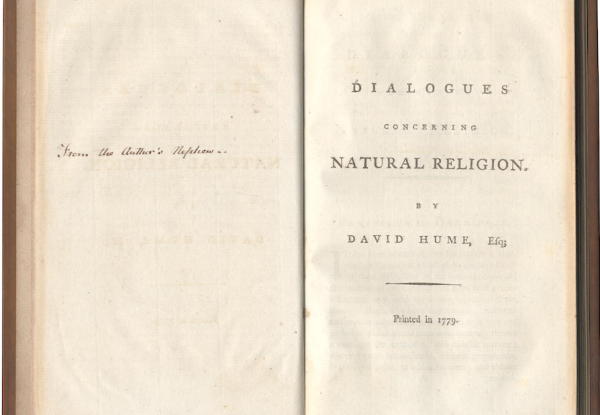
《自然宗教对话录》
1776年4月,休谟完成了他写给自己的“葬礼演说”,即自传随笔《我的一生》。无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休谟预习了自己的死亡:他努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不带偏见,不受虚荣影响的旁观者,在自己的葬礼上向宾客与公众致辞,为死者盖棺论定。当然,他与一般的旁观者不同,他最了解死者的一生,最知晓其志向、性情与才情。我们应该如何审视死者的一生呢?他自认为最有资格为公众提供一些指引。我们不应忽视,其陵墓与自传之间存在张力。他在生前嘱咐陵墓的设计者罗伯特·亚当,墓碑上只需刻上名字与生卒年份,“其他的就留给后人添加吧”(305页)。既然是非功过任人评说,休谟为何还要给后人留下一份自传,一篇评述并理解其人生的导言呢?
《我的一生》着力刻画了休谟的文学成就,以及因此获得的声望、尊敬,乃至财富。在最后一段,休谟对自己的性格做了一番总结。在其笔下,休谟具有平和、节制、友善且乐天的性格,他“擅于与人交往,不易与人结怨,能够克制所有激情”。所以,中伤的毒牙不曾伤害他,政治与宗教派系的攻讦也因其泰然自若而解除武装,以至于朋友们从来不需要为其品行做辩护(247-348页)。总而言之,自传讲述了文人休谟与好人大卫的一生,展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的思想地图,及其经济独立、富有德性、美满幸福的生活。
当然,休谟提供的思想地图和生活拼图尚不完整。就其著述而言,他没有把《自然宗教对话录》纳入其中。就其生活而言,他也无从记录他在告别人世之前最后四个月的时光,而他在此阶段的生活最惹人关注。
鉴于他早已写就对话录,且在积极筹谋出版,那么很明显,他故意避免在自传中提及这部将会令虔信者大为光火的著作。亦即,他在故意为自己的人生“脱敏”,用平实温和的语言引导人们进入他的思想世界。对此,拉斯穆森的评述颇为准确:“至于休谟乐于远离文学争论,以及甘坐冷板凳,献身于研究,休谟的叙述几乎完全忽视了,其著述引发了多大的争议,与所谓的安静多不相关。一位读者如果事先对休谟或他的著作一无所知,那么,在翻阅《我的一生》时,他很少会意识到,他正在在读一个臭名昭著的异端的自传。”(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202)遗憾的是,拉斯穆森对之做出的解读没有说服力。拉斯穆森认为,休谟之所以刻意避免提及他所陷入的文学争端,是想先发制人,避免受到虚荣的指控。拉斯穆森忽视了休谟的曲笔与《自然宗教对话录》之间的联系:他避免在生前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避免在自传中提及《自然宗教对话录》,也刻意回避引发争议的内容,这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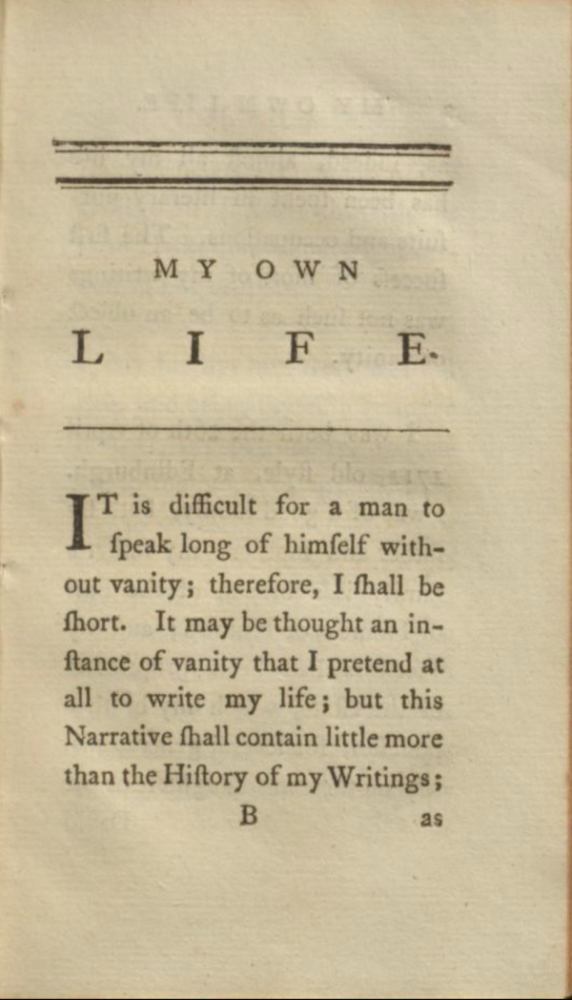
《我的一生》
《我的一生》是休谟的天鹅之歌,无疑是深思熟虑之作。休谟当然无意隐藏自己对宗教的敌意,但在图穷匕见、锋芒毕露之前,他必须让自己死得其所。《我的一生》也是他的死亡之歌,是他为迎接死亡所做的准备。他要告诉世人,他的一生卓有成就,幸福有德,即将到来的死亡也不会令其幸福与德性蒙尘。易言之,他要用死来证成自己的生。“一个怀疑论者也可以平静、优雅地死去。”(287页)所以,对休谟而言,自传写作与对话录出版之间或许形成了某种共谋。他试图用优雅的死亡来震动世人,其人生的幸福与美德也因此变得完满,从而给宗教最有力的一击。正如休谟自己所言,《我的一生》专门记述其“文字生涯”,是写给自己的“葬礼演讲”。言外之意,这篇自传也是为其毕生所学写就的祭礼文。正如苏格拉底选择死亡,成全哲学,休谟的哲学也将因其死亡而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自传亦能为后学者提供指引,使能发现进入思想殿堂的门径。休谟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怀疑论哲学,证明其真理性,他的哲学便因其死亡而获得了更大的生命力。《自然宗教对话录》在其死后出版,对宗教而言,它也就拥有了更大的破坏性力量。所以,他令其墓碑留白,因为他发动的战争并不会因其离世而止息,反而会变得更加猛烈,并且持久。休谟计划好了身后的战争,《我的一生》便是他为身后战事所做的铺垫。
斯密不愧是休谟的至交,他深刻领会了休谟的意图,也充分理解他的遗憾——即难以记述最后时光的遗憾。在休谟离世前的一个多月中,斯密住在休谟家中,陪伴着他。在那段特别的时期里,斯密最为真切地观察着休谟的生活,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大约在休谟去世前第十天,斯密才离开休谟的住所。在休谟去世前第三天(1776年8月22日),斯密向他提议:“如果您同意,关于你对自己一生的论述,我还要补充几行,记叙你在患病期间的言行,以便见证您在世上最后的日子(如果事与愿违,不幸真的发生)。”(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212)对此提议,拉斯穆森做出如下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斯密是在申请完成他朋友的自传,将《我的一生》所记述的内容从4月18 日延续到休谟去世为止。斯密知道公众对休谟是如何走完他的人生有热切的兴趣,他想写下这个故事“得到授权”的版本,向世界表明,休谟以一个哲人应有的方式离开了世界(同前)。
斯密想要融入自己的声音,与休谟合唱其“死亡之歌”。斯密的补充颇为重要。一方面,它向世人讲述休谟如何度过最后的时日,令休谟的自传变得完整。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旁观者视角,印证了休谟自传的真实性,从而使这首歌曲富有层次,变得立体,也更为动人。据拉斯穆森考证,在休谟去世一个月之后(1776年10月7日),斯密就完成了增补内容的初稿。斯密随后征求了休谟亲友的意见,对初稿做出修订,并以信件的形式寄给出版人斯特拉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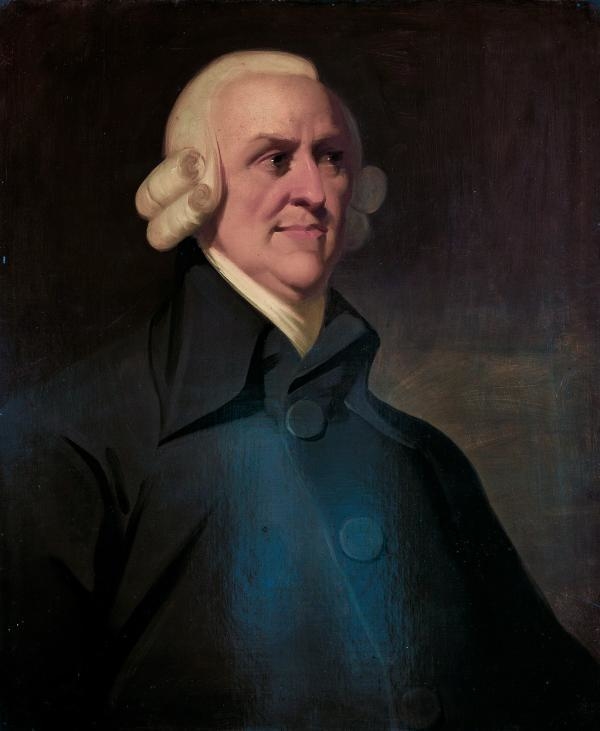
斯密
在这封《致斯特拉恩信札》中,斯密用十分凝练的笔触,记述了休谟临终前的旅行、起居和交谈。斯密告知世人,尽管已经接近死亡之门,但休谟仍旧无忧无惧,保持着一贯的愉悦和乐,甚至还不忘与朋友调侃逗趣。斯密颇为详细地复述了他和休谟的一次交谈。他们谈到了死亡,休谟确信自己时日无多,并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开起了玩笑。休谟模仿琉善的《死者的对话》,想要为自己提出几个搪塞冥河渡神的借口。他想到的一个借口是:“仁慈的冥河渡神啊,再宽限几日吧。我正在修订新版的著作,我想看到公众将如何被我改变……我正在致力于开启民众的心智。如果我再多活几年,我或许能心满意足地看到某些盛行的迷信体系倒台。”可他随后又说,渡神一定会失去耐心,勃然大怒,催他登船,“你这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几百年后都不会发生这种事。你以为我会让你再拖延那么久吗?赶紧上船,你这个懒散的、游手好闲的无赖!”(351页)
这封信札颇为简短,但斯密仍然不惜笔墨,细致刻画休谟的笑谈,自然用心良苦。借助休谟对自身死亡的调侃,斯密既能展现其无所畏惧的豁达心态,也意在强调他念念不忘的志向——开启民智,破除迷信。拉斯穆森注意到,在这封最终公开发表的信札中,斯密修改了休谟的原话。在斯密写给韦德伯恩的私人信件中,他写下了休谟对其志向的原原本本的表述:“我一直致力于让人民睁开慧眼,仁慈的渡神啊,请稍多一点耐心,让我能够愉快地看到教会关门,牧师歇业。”(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209)斯密当然欣赏休谟对宗教的批判,否则他不会讲述这场交谈。但是,他又要采取审慎的策略,尽量避免以尖锐的方式刺激虔信者,激起他们的愤怒。于是,他用“迷信体系倒台”取代“教会关门,牧师歇业”,以弱化休谟的异端形象,突出其对智慧的不懈追求。
在信札的最后一段,斯密妙笔生花,总结了休谟的高尚品格。斯密认为,与大多数人相比,休谟的性情“具有更加幸福的平衡”:他大度而节俭,温柔且坚毅,他的乐天性格融合了审慎与善意。在《道德情感论》中,斯密刻画了一个具有完美德性之人的形象,休谟则是其现实原型。“具有最完美德性之人是我们自然而然地最热爱和最敬重的人。他能最完美地控制自己原初的、自私的感情,在此之中,他又加入了对他人的原初情感与同情性情感最为精细的感知。如果一个人能够将所有伟大的、勇毅的、令人敬仰的德性与所有柔软、温和、温柔之德性结合在一起,那他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合宜地获得我们最高的热爱与仰慕。”(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iberty Fund, 1982, P.152)所以,在信札的结尾,斯密赞颂道:“总而言之,我总是认为,无论在其一生之中,还是在他死后,他都尽可能地接近脆弱人性所能实现的具备完美理性与德性之人的理念。”(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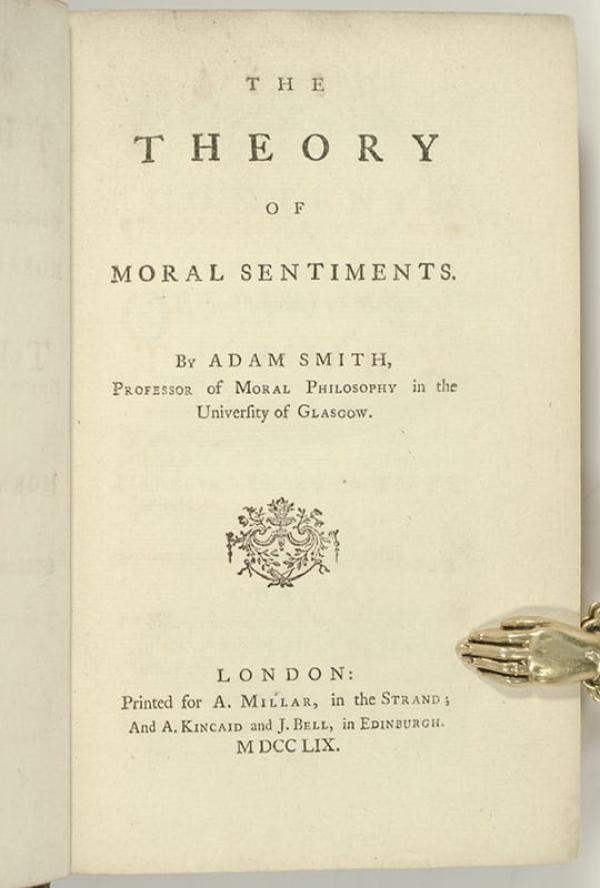
《道德情感论》
拉斯穆森提醒我们,斯密的信札与柏拉图的《斐多篇》存在某种呼应。信札的结尾“显然与《斐多篇》的最后一句里,柏拉图为苏格拉底题写的墓志铭遥相呼应”。在《斐多篇》中,讲述者斐多断言,“在这个时代我们认识的所有人中,苏格拉底是最勇敢、最明智和最正直的人”(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220-221)。在某种意义上,斯密在效仿柏拉图,《致斯特拉恩信札》则在效法《斐多篇》。斯密记录下休谟的最后时光,省察他的一生,志在告诉世人:休谟就是现代社会的苏格拉底,是世人应当追随的老师、哲人与贤人。
三
围绕休谟之死,斯密与休谟完成了他们的合唱。这既是对休谟一生的歌唱,也是对其道德哲学的歌唱。他们共同咏唱的死亡之歌也表明,关于道德与宗教的理解,休谟与斯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亦即,这首“死亡之歌”不过是其思想合唱的最后一个乐章,当然也是最凝练最精彩的乐章。他们用著作呈现了一曲更为恢弘的思想合唱。《异端与教授》便是丹尼斯·C. 拉斯穆森对其思想合唱所做的注解。在这部著作中,拉斯穆森以传记的方式,论述了这两位现代哲人思想的发展历程,着重探讨了他们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乃至宗教观点上的共识与共鸣。这部作品最独特之处在于,拉斯穆森同时为两人作传,呈现两人在思想上的影响、互动与融合。细究之,拉斯穆森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原因还在于斯密与休谟的哲学拥有共同的主题与基调。所以,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言,他是在为两人的友谊作传,为他们合力歌唱的道德与政治学说作传。
在《异端与教授》之前,丹尼斯·C. 拉斯穆森另著有《商业社会的问题与承诺》(The Problems and Promise of Commercial Society),它们构成某种互文关系。在《商业社会的问题与承诺》中,他也论述了两位启蒙哲人之间的理论对话。只不过,相比起斯密与休谟之间的友谊,在这本书里,他着重刻画了斯密与卢梭之间的论战。后者当然没有也无法采取传记的方式写作,而是依据他们争辩的问题,一层一层揭示其思想结构。卢梭对商业社会提出三大批判:“劳动分工”批判、“意见帝国”批判,“追求不幸”批判。斯密充分意识并理解了卢梭的批判,并对之做出有力回应与辩护。在这本书中,拉斯穆森就按照“问题与承诺”的结构,向读者呈现斯密与卢梭围绕商业社会展开的理论对话。但是,这两本书都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不同哲人在同一时代进行的批判与辩护、争论与共识,思想的时代情境就自然浮现出来,我们也能更清晰地把握时代的主题与精神。当然,我们也能更真切体会到苏格兰启蒙哲学的革命性意义。毫无疑问,商业社会的道德与政治是休谟、斯密、卢梭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拉斯穆森这两部著作中试图处理的焦点之一。所以,论及《国富论》的要旨,他才特别强调时常被人忽视的第三卷。在他看来,《国富论》最重要的段落就出现在这一卷:“商业与制造业逐渐引入了好秩序与好政府,并在乡村居民中引入了个人自由与安全。在此之前,乡村居民几乎生活在与邻居的战争状态中,也处在对其上司的严重依附状态下。这一效果最为重要,却最不为世人注意。”(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162)斯密这一论断既是对休谟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卢梭的回应与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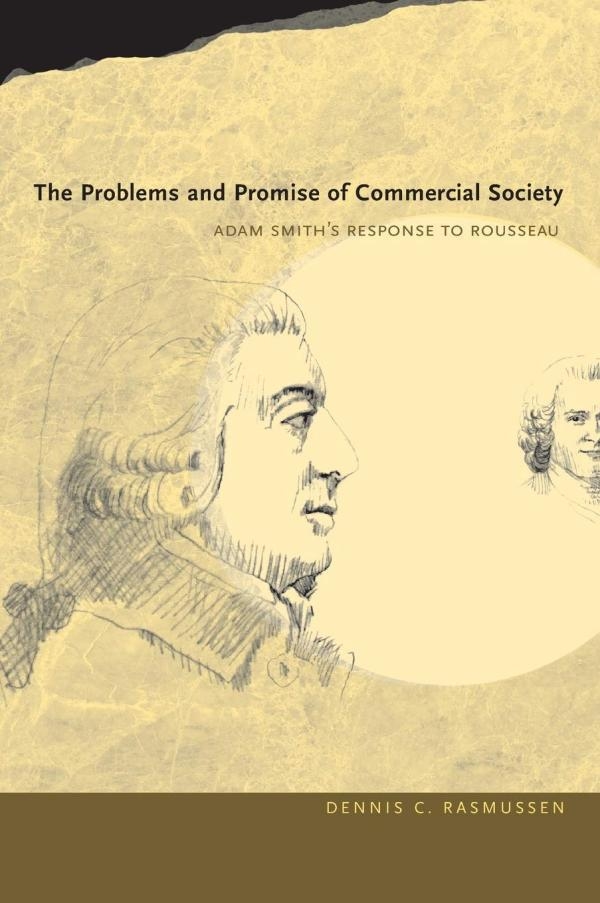
丹尼斯·C. 拉斯穆森:《商业社会的问题与承诺:亚当·斯密对卢梭的回应》
在《异端与教授》这本书中,“异端”指大卫·休谟,“教授”则指亚当·斯密。异端与教授的对峙展现出一种扑面而来的戏剧性张力,也似乎暗示,休谟与斯密在思想品质上存在差别。尤其是,当斯密拒绝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时,他们之间的差异仿佛得到进一步的确证。然而,斯密对休谟自传的补充,他们合唱的死亡之歌表明:哪怕是在宗教问题上,“异端”与“教授”也相互认同。斯密与休谟一样,从来不认为宗教是德性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斯密心中,智慧和美德的榜样不是基督教圣人,而是圣大卫街曾经的住户。
所以,“异端”与“教授”的对峙不是来自学理上的差异,而是源于两人性格上的区别——休谟更为率真,斯密更加谨慎。休谟的率真使他遭到排斥,被教会指斥为毒害青年的“大异端”,被大学拒之门外,无法获得教授席位。斯密的谨言慎行令他为公众称颂,荣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可是,公众似乎没有看到,教授心中的英雄却正是那个异端。所以,标题蕴含的张力实隐含着某种反讽的意味。
《异端与教授》书名中隐含的戏剧性张力很能激发出读者的兴趣。甚至,读者很可能因此认为,这是一本相对浅显,具有较强故事性的文化普及读物。或许,译者正是出于这种理解,将之看成畅销书,而非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从而采用意译的方法,着力追求译文流畅。实际上,丹尼斯·C. 拉斯穆森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是因为他具有常年研究休谟与斯密的学术积累,对其著作、书信有精深的理解,对其时代争论乃至精神世界有准确的把握。就此而言,本书也当是一部严肃的,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学术著作。译者缺乏对休谟与斯密的专门研究,因此,倘若他们对相关论述推敲不够,就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错译。例如,在解释“同情”的原理时,斯密使用了四个同情互动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斯密注意到,一个行为粗野的人完全意识不到他所造成的冒犯,我们却时常为他感到难堪。这一句的英文原文为:Smith notes that we sometimes cringe on behalf of an individual who is acting rudely even if he is completely oblivious to the offences he is causing.(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92)译者却将之翻译为:斯密指出,我们有时会对一个举止粗鲁的人的行为感到厌恶,即使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所造成的冒犯(131页)。如果你熟悉斯密对同情的讨论,那么你就会看到,此处的错误颇为明显。在这里,斯密并不是说我们厌恶这个举止粗鲁的人,而是说,当我们想象自己处在他的境地,造成冒犯时,我们会感到难堪——我们会对一种并未实际出现的情感产生“同情”。再如,在斯密的道德情感理论中,merit and demerit意为“功与过”,即某种特定行为致力于产生的效果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译者则将之译为“优点与缺点”(132页)。当然,大家著述总能深入浅出,《异端与教授》当然可以是一本畅销书。如此说来,译文得其大旨,语言流畅,读起来饶有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