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中西马关于人的存在与生成的对话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文章转载自读一YE(ID:sanliansh)
对人的追问,并不限于中西哲学,马克思在从人的视域出发理解世界的同时,也将关注之点指向何为人的问题。
作
者
简
介
上矩形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重点人文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出版学术著作10余种,多种论著被译为英文、韩文,在Indian University Press、Brill 等出版。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际形而上学学会(ISM)主席、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国际中国哲学史学会(ISCP)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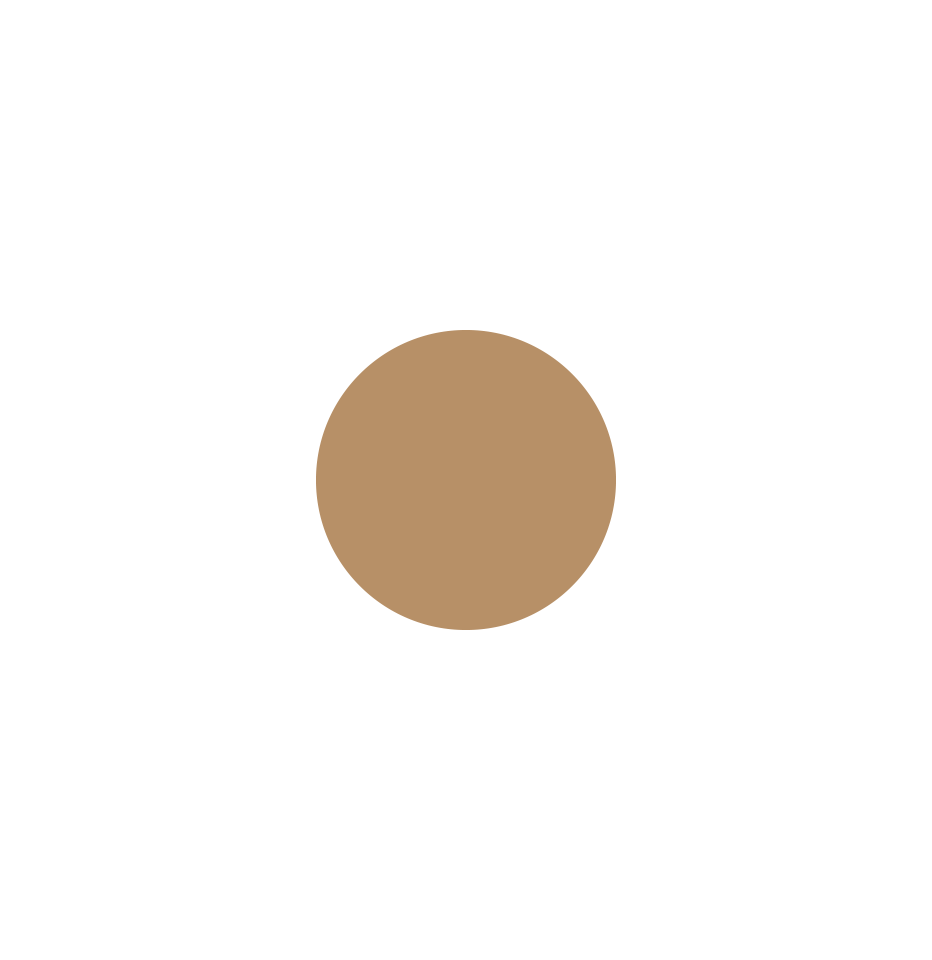
中西马关于人的存在与生成的对话:
基于“事”的统一
现实世界以人为主体,“事”也以人为承担者。作为现实世界的主体和“事”的承担者,人本身同样涉及存在与生成的关系问题。与其他对象一样,人既表现为具体的存在形态,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两者的彼此关联则离不开人自身所作之“事”。
与人相关的存在与生成,在安乐哲(Roger T. Ames)那里曾得到较为详尽的考察。以中西比较为视域,他对“人的存在”或“作为存在的人”(human beings)与“人的生成”或“作为生成的人”(human becoming)做了区分。尽管安乐哲所谓“人的生成”或“作为生成的人”(human becoming)同时涉及人的“关系性”和“互为性”(安乐哲:《安乐哲比较哲学著作选》,孔学堂书局,2018年,第284页),但becoming这一概念本身无疑以“生成”为其逻辑的内涵。在他看来,前达尔文的西方主要关注“人的存在”或“作为存在的人”(human beings);与之相对,“儒家的人基本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儒家对于人所关注的是“‘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是’什么”。由此,安乐哲强调:“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人是‘人之生成’或‘作为生成的人’(human becoming)而不是‘人的存在’或‘作为存在的人’(human beings)。人性就是人的行为;人之潜力是一种特别的关系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在处事中出现并在处事中被完善的,而处事构成了一种人的叙述(human narrative),并且,人之潜力只有在事后才看得清楚。”“从儒家的视角来看,只有公开放弃‘人的存在’或‘作为存在的人’而接受过程性的‘人的生成’或‘作为生成的人’的概念,我们才能重现健全的关于人的智慧的概念。”(安乐哲:《安乐哲比较哲学著作选》,孔学堂书局,2018年,第295—296页。)若干术语的翻译略有改动。
安乐哲的以上论点无疑需要辨析。首先,以“人的存在”或“作为存在的人”(human beings)与“人的生成”或“作为生成的人”(human becoming)来区分西方哲学与儒学是否确切,显然应当再做思考。human beings作为表示“人”的西方概念,并非完全排斥生成(becoming)。从西方哲学的发展看,自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对人的生成之维也并不是毫不涉及。亚里士多德从普遍的层面注意到由潜能到现实的展开过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以思辨的方式考察了人的精神的发展历程。同样,儒学固然注意到人的生成性(becoming)这一面,但并非完全忽略人的存在(being)。孟子肯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这一使人区别于禽兽的“几希”之“希”,即表现为具体的存在规定。从更为实质的层面看,在论说儒学之时,安乐哲固然注意到“做什么”以及“处事”与人的关联,但同时又将“做什么”与“是什么”视为相互对峙的两个方面,认为在关注人“做什么”之时,无须关切人“是什么”。由此,他进而将“人的生成(human becoming)”置于“人的存在(human being)”之上,甚至主张“放弃‘人的存在’而接受过程性的‘人的生成’的概念”,这种看法似乎很难视为理解人的合理进路。如后文将进一步论及的,对人而言,“做什么”与“成为什么”无法相分,而“成为什么”总是引向“是什么”。同时,以“人的生成”或“作为生成的人”(human becoming)取代“人的存在”或“作为存在的人”(human beings),在逻辑上意味着有生成过程而无过程的承担者,它与形而上层面“万物流变”“方生方死”的抽象视域,呈现相近的趋向。
如前所述,在本体论上,存在(being)与生成(becoming)无法相分,作为这种相关性的延伸,两者在人之中也难以分离。一方面,人确实非既成之“在”,其身和心等都处于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人的生成又总是从已有的存在形态出发,由此进而走向某种新的存在形态,离开了具体的存在,人的生成过程就将趋于空泛而失去实际内容。就个体而言,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之时,首先呈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经过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人逐渐获得了多样的社会品格,成为具有社会规定的存在。这里既有以个体的社会化为内容的生成过程,也涉及人的不同存在形态。作为不同存在形态彼此关联的中介,广义的个体社会化过程展开为人的多样活动,后者同时以人所作之“事”为内容。从了解和把握社会的规范并以此为人与人交往的准则,到参与对自然的作用、化“天之天”(本然的存在)为“人之天”(人化的存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人所“从事”的活动展现为不同的形态。可以看到,正如现实世界基于人所作之“事”而呈现为存在与生成的统一,人自身也在做事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并不断超越既成存在而生成为新的存在形态。
从哲学史看,中国哲学对人的理解,既非仅仅执着于既成的存在,也非单纯地指向空泛的生成,而是关注存在与生成的统一。孔子在谈到人之时,已言简意赅地指出这一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里的“性”可以理解为人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可能,这种根据和可能同时表现为人的本然存在形态或潜在的存在形态。“性相近”表明:在本然的存在根据和可能方面,人与人之间具有相通性。“习相远”中的“习”,可以理解为习行,这种习行具体表现为人在后天“从事”的不同活动。这一意义上的“习相远”,意味着正是通过多样的活动过程,人形成了彼此相异的人格并“生成”为不同的存在形态。儒家所说的君子、小人等等,便属于这一类因不同之“习”而“成”的相异之“在”。具体而言,君子是在道德上应当加以肯定的、具有正面意义的人格,与之相对的小人则表现为在道德上应该加以否定的、带有消极意义的人格形态。基于人之“性”而通过后天“习”行以成就君子这一类完美的人格,则构成了儒家的道德理想。在这里,“性”与“习”的互动,同时表现为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成之统一。“性”与“习”的关联在中国哲学的尔后衍化中进一步引向“本体”与“工夫”之辩。“本体”主要被理解为人在精神层面的本然形态或原初存在,对中国哲学而言,正是这种存在形态,为人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内在的根据。作为工夫所由发生的条件,“本体”自身又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生成、发展和丰富,其现实的内容则逐渐既融入理性认知,又渗入广义的价值观念。黄宗羲明确地指出了本体的这种生成性:“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与本体相联系的工夫,主要展开为宽泛意义上的知、行过程,后者同时以“事”为其具体内容。广义的工夫既表现为“赞天地之化育”,也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工夫的以上展开过程中,人不仅改变对象,而且也成就自己,在此意义上,本体与工夫的交互作用作为“性”与“习”互动的延续,也使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成”的统一取得更具体的形式。
对人的追问,当然并不限于中国哲学,马克思在从人的视域出发理解世界的同时,也将关注之点指向何为人的问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人与世界的关系;其二,人自身的规定。与离开人的存在以思辨的方式把握和构造世界不同,马克思首先注重世界的现实品格。世界的这种现实性在马克思看来与人自身的活动无法相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8页)“人的劳动”即人所从事的基本活动,以上看法可以视为基于人的存在及其活动而考察世界。后期海德格尔曾注意到马克思的以上进路,并对此提出了种种批评。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对于马克思来说,一开始就确定的是,人,并且只有人(而并无别的)才是那个事情。这是从哪里得到确定的?以什么方式被确定的?凭什么权利被确定的?被哪种权威确定的?”海德格尔认为,“在这里应当注意到一种惊人的跳跃”(参见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马克思以人为考察世界的出发点,但是,人非既成或现成的存在,他本身处于生成过程之中,并应当成为追问的对象,忽略了后一方面,便意味着思想的“跳跃”。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是否存在以上跳跃。
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既涉及人之为人的存在规定,也关乎其生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其侧重之点在于人的存在形态。然而,在关注人的存在规定的同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人的生成性。前面提及,在谈到现实世界的生成时,马克思曾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紧接此文,马克思写道:“所以关于他(即人——引者)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8页)在这里,现实世界的生成与人自身的生成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现实世界的生成,同时伴随着人自身的生成,两者的共同基础则是人所作之“事”——劳动。
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从人出发考察世界的同时,并没有对作为出发点的人未加追问和考察。在实质的层面,马克思以人的存在和生成的统一,作为人的基本规定,并将人的生成和世界的生成置于同一基础之上,这种思想的进路显然不同于思想的“跳跃”。
广而言之,人“成为”什么,与人“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或做什么样的“事”无法相分。在类的层面,人的“存在”形态总是相应于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作之“事”。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可以视为人基本的“做事”方式,正是通过运用工具以“做事”(劳动),人既改变了世界,也使自身走出自然,成为自然的“他者”。作为人“做事”的基本方式,劳动形式的变化同时规定了人的不同存在形态。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的劳动,构成了原始时代人类的主要“做事”方式,这一时期的人类则相应地处于近乎自然的存在形态。与之类似,农耕或游牧这一类劳动方式,赋予人的存在以早期的文明形态;与近代机器工业相联系的劳动方式,则使人的存在方式获得了近代和现代的形态,如此等等。
同样,在个体的层面,人的存在形态也与其“做事”方式相联系:人“成为”什么,关乎人在现实生活中“做”什么。作为不同于自然对象的社会性存在,人所作之“事”涉及不同领域,人自身也相应地呈现多方面的规定性。在“从事”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经济领域的企业员工、管理人员、投资者;在“从事”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人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谓“政治的动物”或政治生活的主体;在“从事”创作、表演等活动中,人成为艺术领域的主体,如此等等。以上视域中的不同主体,可以看作人的不同“存在”形态,这种“存在”既非前定,也非既成,而是形成于人做多样之“事”的过程;取得相关“存在”形态的过程,则表现为人的多样“存在”不断“生成”的过程。在这里,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成”基于人所作之“事”而相互交融。
现实世界既表现为多样的存在形态,又展开为生成的过程,人自身之“在”也同样如此。从现实世界到人自身,“存在”与“生成”构成了同一过程的相关方面,难以彼此分离。作为世界和人的真实形态,存在与生成的统一既非逻辑推绎的产物,也非思辨构造的结果,而是基于人自身所作之“事”。以成己与成物为具体指向,人所作之“事”展开于不同的领域,“事”的多样性既规定了多重生成过程,也引向了多样的存在形态。世界之“在”与世界的生成、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成交汇于人所作的具体之“事”。
(选自《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第三章,第三节)
相关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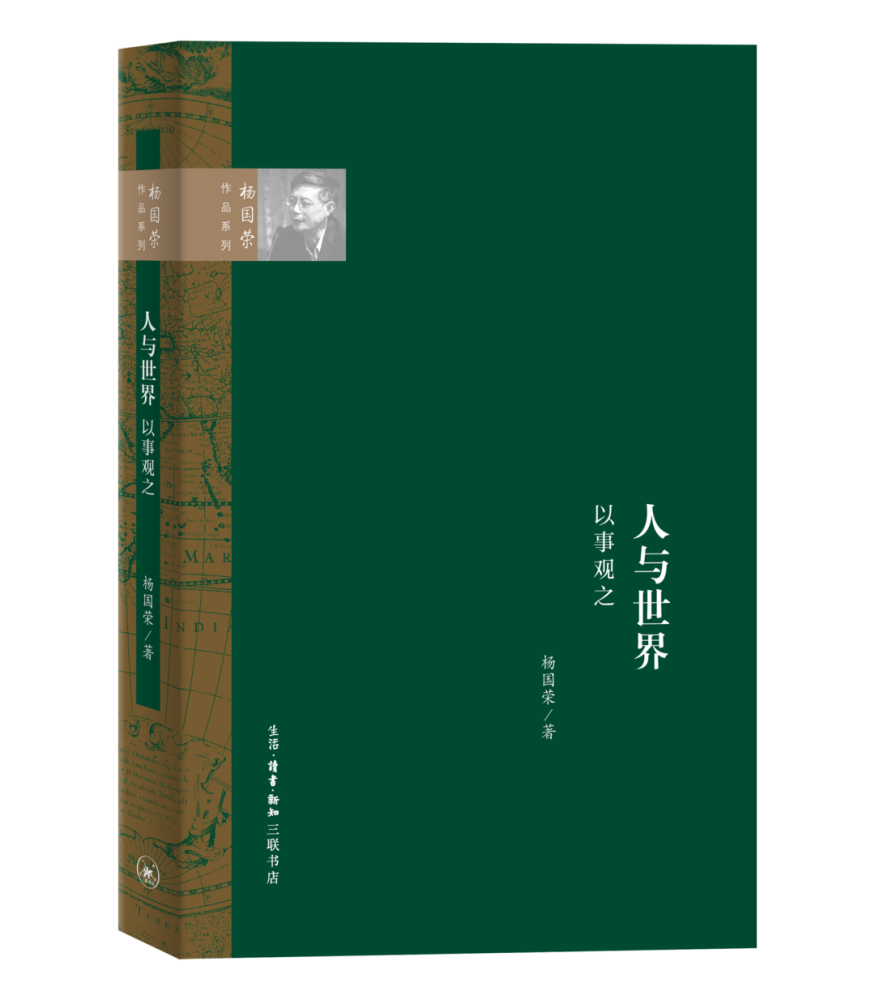
书 名:人与世界
副书名:以事观之
作 者:杨国荣 著
ISBN:978-7-108-07121-7
定 价:68 元
内容简介:
本书可以看作作者此前在具体形上学之域所作思考的延续,就其内容而言,它既与《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引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在理论上相互关联,又与《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前后相承。当然,在人与世界及其相互作用中,“事”具有本源的意义,以“事”为考察视域,相应地意味着从更本源的维度理解人与现实世界。它的出版,将使作者已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具体形上学”更为系统和深入,也将在更广意义上推进哲学领域的理论创新。
目录:
自序
导论
第一章 “事”与现实世界
一 “事”与“物”
二 作为事实之域与价值之域统一的现实世界
三 本然性的扬弃与实然性的确证
第二章 人:因“事”而在
一 人之“事”与人之“在”
二 生成于“事”的交往关系
三 “事”与存在意义
第三章 存在与生成:从“事”的视域看
一 存在、变化与生成
二 现实世界:存在与生成的交融
三 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成:基于“事”的统一
第四章 源于“事”的心物、知行之辩
一 心与“事”
二 心与物:由“事”而相涉与相融
三 知行之辩:以“事”为源
第五章 由“事”思“理”
一 “事”与“事实”
二 “物理”与“事理”
三 “事”中之“理”:“循理”与“讲理”
第六章 “事”与“史”
一 “事”以成“史”
二 “事”“史”“势”
三 “事”的变迁与“史”的走向
附录一 人与世界关系中的感受
一 感受:意义与意味
二 体验与评价
三 人与世界的三重关系
附录二 人类认识:广义的理解与具体的形态
一 认知、评价与规范
二 关联与互动
三 广义认识所以可能的根据
四 以“事”观之:广义认识的现实指向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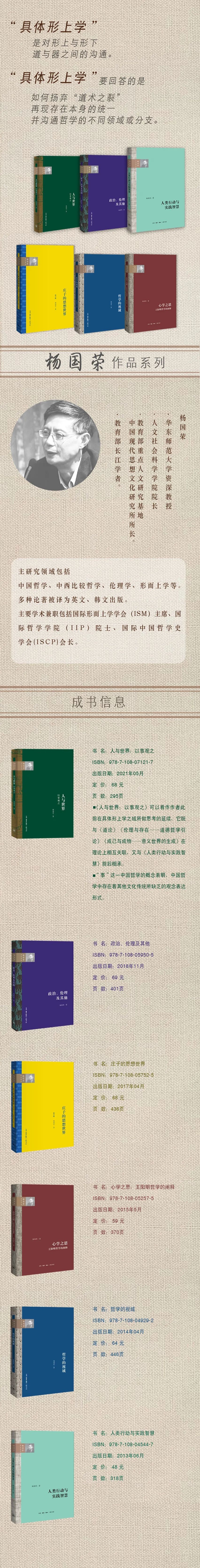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