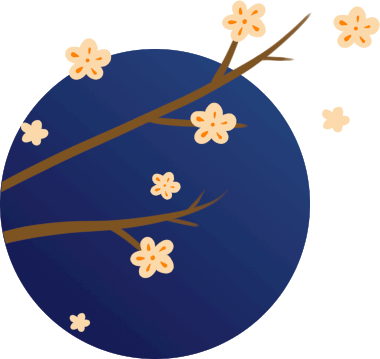王宁老师丨一位满怀责任心的语言学家——纪念胡明扬先生逝世10周年
 2021-07-31
2021-07-31

2021年6月22日,是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逝世10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位对语言学研究和教学有多方面贡献的语言学家,王宁老师把她的3篇关于胡明扬先生学术介绍的文章综合为下面的文章,由“章黄国学”发表。
一位满怀责任心的语言学家
——纪念胡明扬先生逝世10周年
文丨王 宁
北京师范大学古汉语研究所
10年前,胡明扬先生在病后的很短时间里突然辞世,这位为中国语言学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是带着他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深切思考离开人间的。他去世前一年的春节,胡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者一年一度的聚餐会上谈笑风生,述说自己最近关于语言学发展的思考;11年过去,参加那天聚会的年轻学者恐怕早已不记得他说的那些话,但我却很难忘记。他一再说起如何促进黎锦熙先生全集的出版,说起关于海宁方言志的校对,说起他要修订自己主编的《语言学概论》教材,要我参与,突出汉语,还要加上最典型的汉语与汉字的关系,还说起北京口语语法问题……这些就是胡明扬先生心中的牵挂。他带着这些问题去了另一个世界。

胡明扬先生
我80年代初回到母校北师大任教,做颖民师的科研助手,跟着老师拜见各位语言学界的前辈师长和同辈先行者。在边疆教语言学和汉语课时,读过很多学者的论著,到这时才有机会一一谋面请教。那时学坛复苏,北京语言学会组织了一个语言学的系列讲座,其中有一讲是请颖民师介绍黄季刚先生的文字训诂学。老师派我带着发言稿去联系,在张志公先生处见到胡明扬先生。交谈中胡先生知道我是海宁人,之前海宁和海盐曾合为一县,而我家族的陵园就在海宁和海盐交界的水北,胡先生便认了我这个“老乡”。当时我正在恶补普通语言学,几部重要的论著都刚刚读过,对胡先生的名字是不生疏的,但真正见面,这是第一次。以后渐渐联系多了,我对胡明扬先生的学术也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和了解。
胡明扬先生从195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起,就跟语言教育与语言学理论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胡明扬先生在语言学界教书育人、研究应用、主办学会、主持评审、访问讲学、出国外交……他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贡献非常全面,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胡明扬先生在语言学界“摸爬滚打”的半个多世纪,正是中国语言文字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60年;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在改革中崛起,寻找自己道路的60年;也是中国语言学逐步有了自己的流派、自己的理论、自己的队伍的60年。胡明扬先生是这60年中国语言学的见证者,也是这60年中国语言学的推动者,他是走在语言学队伍的前列的。
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前身是“小学”,“小学”积累的语料以文言为主,缺乏理论通论与总结成熟的方法论,没有语法这一分支。因此,汉语研究走入现代的标志应当是传统“小学”的理论化和现代转型,以及现代语言学门类的完善。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便成为其中最明显的标记。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语言学向普通语言学索取理论的年代,汉语作为分析型语言,如何与国外语言学的“语法范畴”理论交流对话,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话题。胡明扬先生在阐述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关系和必要条件之后,针对汉语的特点,提出了“无形形态”这一概念,把语序、语调和重音列入无形形态,使汉语语法可以纳入普通语言学来讨论。[1]之后,他又在海盐通园方言中发现,连续变调群中具有明显的语法意义,由此将汉语语法意义的研究进一步推进。[2]胡明扬先生关于语法意义的研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关注点,那就是他对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的分辨和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他通过各种现象说明,同一语法形式本来应当只有一种语法意义,但是由于受语汇成分的影响,是可以产生不同变体的。
上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语言学拓宽领域的时期。胡明扬先生对语言学的关注有了很多新的角度:首先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方言研究,这种研究是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进行的。他从语音出发,探讨了北京方言的语法和词汇,探讨了上海话100年的变化,探讨了海盐方言的句式和词汇。那时候,一般的汉语方言调查都在总结各个方言统一的语音结构系统,胡明扬先生关注的却是同一方言中由于年龄、性别、家庭环境、文化水平不同而产生的内部分化。他的成果从本体研究到了社会条件的研究,从静态的描写到了发展的动态解释。其次,胡先生开始关注近代汉语研究,为了甄别近代汉语的语料,他注意了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互相渗透的关系,描述了汉语书面语的复杂情况,对此作出了十分求实和清晰的结论。如果和西方的社会语言学比较,可以看出胡先生在认真发掘中国历史和现代社会的语言生活给汉语带来的特点。第三,胡先生开始关注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词典编纂等应用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新的创见。

《北京话初探》,胡明扬先生著
商务印书馆 ,1987年
20-21世纪之交,中国语言研究正在进入自己方法论的探讨,走向共时和历时的结合、描写和解释的同步、结构和意义的一致,这些结合汉语特点的研究,从向普通语言学索取理论到向普通语言学输送理论,这是主流。但盲目西化的暗流也在涌动,用西化代替现代化的倾向在无形泛滥。许多西方语言学流派的方法对汉语明明是削足适履的,却被分别和混合地运用到汉语上,西方语言学的模仿和“汉证”以多种形式排斥传统,甚至连早期立足汉语、学习西方的探索也给否定了。但是,胡明扬先生却冷静而理智地分析了半个世纪语法研究继承与借鉴的互补,看到在汉语进入应用领域后日渐突现的个性和特点,提出了“兼收并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3]的主张。跨入21世纪,胡明扬先生最令人瞩目的创建是通过对黎锦熙先生《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锐敏地提出了“向传统语法回归”的问题。
从这些最简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明扬先生的创新精神。他的创新意识是自觉的。在他的《语言学论文选》自序里,他说:
“从50年代起我就想寻找一条研究现代汉语的新路子,但是很难找到,所以只得打外围战,从研究方言、近代汉语、北京话搞起,想从这些领域的具体研究中找到一条新路子。”
这段话让我们明白,胡明扬先生是想从实际语料中找到汉语的语法形式,并从中总结汉语的语法意义。他费了那么大的工夫去做汉语口语语料的调查,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只有从口语的语音事实中,才能找到汉语语法意义赖以存留的语法形式。所以他说:
“其实我心中的新路子对谁来说都一点也不新,那就是我一贯主张的形式和意义密切结合的路子。”
胡先生的探索究竟是不是创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是符合“创新”定义的。

《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
语言学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创新与科技发明是完全不同的,绝对不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一种创新的汉语研究到了大多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仔细钻研都听不懂的地步,到了理论框架无法容纳汉语语言事实的地步,到了越细越远离汉语多数语料的地步,到了号称“普遍”却与自己的母语相左的地步,“新”则“新”矣,那还能是“真”的吗?
胡明扬先生的书和文永远那么平易、清新,说得明明白白,这和今天“越难懂越深刻”的时尚是完全不同的。胡明扬先生的创新是从大量事实出发,经过调查而走向理论的,不是从理论推到另一个“理论”而背离事实的。要研究哪种语言,先学习那种语言,一句藏语都说不来,用藏语字典去研究汉藏语对比,恐怕很难令人放心。仅仅会几种语言的皮毛就说自己的结论是“普遍的”,也很难让人信服。胡明扬先生研究口语用的是自己最熟悉的语料——海盐话和北京话,而且仍然去做社会调查。他说:
“我觉得没有足够的资料写出来的文章很可能是空头文章,那样的文章我不想写。”
胡明扬先生1944-1948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并获得学位,主修西洋文学,辅修中文。又做过多年的翻译工作。从事语言教学工作后,介绍过很多西方经典的语言学论著。但他对西方的理论方法领会得非常透彻,找到了其中的精髓,“食洋而化”之后,用于汉语研究,而不是刻意模仿其中的具体框架和运作程序。他不把眼光放到去证实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普遍性,而是把眼光放到用汉语的事实中总结的理论去丰富普通语言学。胡明扬先生的论著里搬用西方概念很少,但得其精神很多,他是真正在借鉴,也借鉴真正的东西。
胡先生在借鉴前苏联和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同时,非常尊重中国的传统,他在《说“打”》[4]一文里引用了那么多古代汉语的资料。他从来不把古今对立起来,也从不把自己寻求新路子建立在菲薄传统、鄙薄自己民族悠久历史的基础上。一门人文科学不管是否有意识,都会从自己的传统起步,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又去否定前人,发展了前人后反过来标榜前人不如自己,这是不道德的。我们在胡先生的论著里丝毫也看不到这种荒谬的态度。胡先生在对《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时,十分清醒地叙述了50-70年代中国语言学大批判的原因和所向,说得那样透彻,那样实事求是!可以看出,他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时候,对走过的弯路充满惋惜和遗憾,也充满吸取教训引导今天的热情,他是丝毫没有那种用前代的“旧”来衬托自己的“新”的虚荣心的。
也许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那些特点,胡明扬先生的创新让他自己觉得“不新”,但是我以为,新,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动,每个人所能推动的,不过是一分半分。人文科学的创新不可能完全脱离前人、脱离历史,“新”中如果完全没有了“旧”,那只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产物,对这个世界未必有用。

胡明扬先生
2008年,为了给“黎锦熙先生诞生120周年纪念会”做好学术准备,我们请胡先生到北师大连续六周开设“现代中国语法”的系列讲座。筹备讲座时,胡先生对我们申明自己的理念说:
“我没有虚荣心,不怕被人说成是‘保守’,我的讲座是前详后略,中详西略,实(符合实际)详时(时尚时髦)略。被大家遗忘的恢复记忆;被大家忽略的提醒注意;被不合理批判的也要有一点抱打不平。”
开讲后,他从传统语法一直讲到计算语法,对每一个语法流派,在全面介绍、指出局限之后,重点是详细说明哪些是精华,值得我们吸取借鉴;特别是对当前已经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的中国传统语法和教学语法,介绍得更为详尽,分析得更为透彻。讲座以后,我对胡明扬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态度有两点更加深了印象:第一点是他各取所长的公允态度。听讲座时,我不断想起《老子》的两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固然说的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但对学术的评价和取舍也是如此。我在6次讲座结束时发表感想说:“胡先生,您在行天之道。”其实,我心里想,他在介绍各个流派以供语言学研究者吸收时,并不是损有余来补不足,而是做到了充分弘扬有余来补后学者的不足,让前人研究成果的精华,都成为后人研究的滋养。没有学术客观的态度和对各种流派深入的理解,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第二点是他求真求准的学术品味。那次的讲座在北师大艺术楼的大阶梯教室举行,不止是中文系师生,外文系、哲学系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一百多人来听课,我和古汉语的年轻老师也次次不落。他凭借古今汉语和极为熟练的英语,阐释问题深入浅出而能鞭辟入里。听完胡先生的讲座,学生们几乎众口一声:“真的懂了!”这是对高端讲座很少有的评价。要知道,不少的语法文章和有一些语法讲座被学生们评价为“越听越玄”“弯弯绕”,介绍语言学流派特别是西方语言学流派,即使是基础理论,也是很难懂的。唯有丰富典型的语言事实和清晰准确的表达水平,能获得一个“懂”的评价。在以不懂为“深刻”的现时代,一个“懂”字,是有千金重的。
2009年在杭州开会,胡先生要我陪同他到我的家乡海宁去。胡先生是海盐人,海宁硖石镇是他青少年时代生活多年的地方。他说,看到过有人写的《海宁方言志》,不但与他的记忆不同,而且记音也有很多错误,他要去说明情况,让他们不要把错误的东西写进地方志里。海宁是个小地方,没有大学,市长带领宣传部、文联和文史馆共同接待胡先生。第二天,当我从家里到宾馆去时,他已经在和六七位年过七旬又没有出过海宁的老人座谈核实材料了。在回来的火车上,胡先生挑出100多个词,放到句子里,问我用海宁话怎么说。我说:“我的海宁话是跟着父亲学说的,父亲从家乡出来到上海上学,在山东、四川修路,转至武汉、贵阳工作,他的海宁话还有什么准头;我在家乡仅仅是小住,说话的语感来自父亲,更是南腔北调,已经毫无价值了。”可胡先生说:“我就是想知道一种方言与其他方言在个人身上层层接触其他方言后,可以变异到什么程度;也想弄明白他们原来写的《海宁方言》是记音的错误还是语言的变迁。”回北京后,又是他认真校对了《海宁方言志》。我体会到,胡先生对现实的语言问题一直在关注,他解决问题的习惯是立足语言现象,针对实际材料,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到寻求答案。对他来说,是习惯,是兴趣,更是责任。孔子曾经感慨:“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常常被今人误解。胡明扬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对这两句话做了很好的诠释:“为己”,是出于己心,迫于己任;“为人”,是做给人看,媚世媚俗。
2004年,胡明扬先生80岁寿诞的时候,我说过:
“我钦敬胡明扬先生半个多世纪对中国语言学作出的贡献,希望也相信胡明扬先生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对中国语言学有更大的贡献,特别是希望更多的人理解他创新的意义和价值。中国语言学又面临着继承与借鉴的抉择,面临国外语言学的尖锐挑战甚至挑衅,我自己,要好好学习胡明扬先生和其他很多先行者合乎人文科学规律的创新,并祝胡明扬先生健康长寿。”
没有想到,不到10年的时间,突然之间,胡先生就带着正在思考的问题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一位满怀责任心的语言学家临终的牵挂和遗憾。
现在,又是10年过去了,胡明扬先生和诸位前辈师长们的牵挂和遗憾可以放下了吗?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航船拨正船头了吗?我们的基础教育真正引导青少年具有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理解、热爱和充满自信了吗?汉语汉字这种与印欧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被世界了解和认可了吗?许多尖锐又迫切的问题,我们是不能不回答的。
2021年7月20日 改定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 《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中国语文》1958年3月号)
[2] 《海盐通园方言中变调群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1959年8月号)
[3] 《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性著作——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语言科学》创刊号)
[4] 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选》314页
作者简介

王宁,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之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辑:花蕊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我知道你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