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今天(2021年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诞辰110周年。季羡林先生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先生生前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着深厚的情谊。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 | 季羡林
来源 | 《季羡林散文》
一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心头就涌起一种温馨甜蜜的感觉。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根源的,我这种感觉的根源大概就是“文学”二字吧。有作家才能有文学。谈到作家,我对“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句舶来品气味很浓的话,颇不怀好感。我自己的灵魂还没有治理好,哪里有本领和闲情逸致去关心别人的灵魂呢?
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什么作家,这样崇高的名称,我担当不起。可是天公偏又作美,或者是偏不作美,让我在中学时就遇上了几位极其优秀的国文教员:教文言文写作的是王玉先生,教白话文写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和胡也频先生,于是我就同写作结上了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写点短文,搞点翻译。我一生治学虽多变化,总之是没有出语言、历史、宗教的大范围。可是,不管我变向何方,写散文、搞翻译则始终没变,可谓一以贯之了。
在清华读书时,我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竟同系别不同的林庚、吴组缃、李长之等三人结成了一个小集团,难道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当时还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后来形成的。四个人都对文学有兴趣,也都在写点什么,翻译点什么。由于趣味相投,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粪土当年万户侯”,而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信口雌黄,说话偏激,又由于郑振铎先生之吸引力大,我们都被他吸引到他的身边,成为由他和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出过集子。在我赴德国前,郑振铎先生曾想出版我一本散文集,可惜文章写得还不够多,编不成一本集子,就此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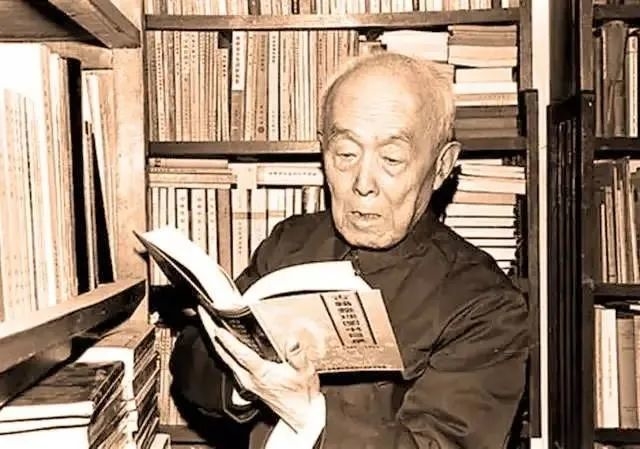
在德国十年,天天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等拼命,没有时间,也没有情趣,写什么散文。十年之内,总共写了两篇。一九四六年回国以后,在南京和上海闲住了一个暑假,在打摆子之余,天天流连于台城和莫愁湖、玄武湖之间,初回到祖国时的温馨,旖旎的湖光,在胸中激荡,诗情画意,洋溢汹涌,本来应该写出点好文章的,然而政治气候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致。结果,除了用假名发表了两篇类似杂文的东西以外,空辜负了金陵胜景。
回到阔别十一年的北平以后,不几年就迎来了建国。当时颇昏天昏地地兴奋了一阵。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就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复回还,一搞就是十几年,到了十年浩劫,算是登峰造极。中国知识分子脆弱性,显露无遗。人家说你是黑,你就自己承认是黑。人家说你是白,你就承认自己是白,完全是心甘情愿,毫不勉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之不暇,哪有闲情逸致来写什么劳什子文章呢?一直到改革开放,脑袋里才开始开了点缝。这三十年是继德国十年之后写东西最少的时期。
跑了半天野马,现在该轮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了。同人民文学出版社打交道,当然离不开文学。文学所包含的不外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当然也在其中,但所占比例不大。谈到文学创作,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好像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生平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曾带给了我极大的欢乐。至于第一本翻译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集》,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槛公认是相当高的,大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之势。这本书带给我的欢乐就可想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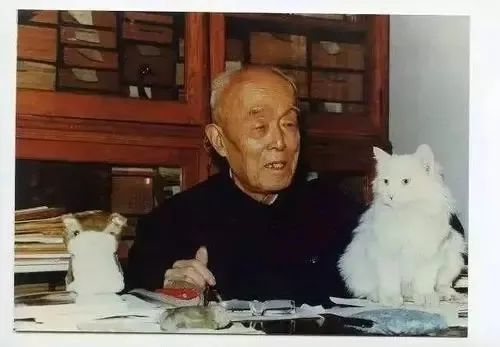
从那以后,在颇长的时间内,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出的书都是翻译作品,而且都是印度古典梵文作品,如《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等等。这些名著久已蜚声世界文坛,很多国家都有译本,在中国却都是初译。我以微薄的力量,给中国文学界做了点拾遗补阙的工作,颇感自慰。
我在这里想专门谈一谈世界名著,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的翻译问题。这一部书,数量大,翻译难度高。在十年浩劫以前,我无缘无故地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是国际活动家,这与我内向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终日忙忙叨叨,极以为苦。对这样艰巨的翻译工作,我是决不敢尝试的。幸亏来了“文化大革命”,幸亏我自己跳了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罪行累累的“老佛爷”,幸亏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幸亏在牛棚里被折磨,被拷打,被戴上了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许多帽子。到了“文革”后期,所有的“罪犯”几乎都被“解放”了,我却是“欲摘还戴时候,最难将息”,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游离于人民与非人民之间,徘徊于友人与非友人之际。昔日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而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我除了被派去看大门,守电话以外,什么事情都没有,自谓是今生已矣。但我偏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找一件旷日持久而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工作,想来想去,想到了翻译《罗摩衍那》。这活儿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晚上回家,翻读全书,译成散文。白天枯守门房时,脑袋里不停地转动,把散文改成了韵文。总之是一句话,我“感谢”十年浩劫,没有这场浩劫,就决不会有《罗摩衍那》的译本。世事纷杂混乱,有如是者!最后终于是妖氛扫尽,天日重明,我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颇可接触者”。不知怎样一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了我翻译《罗摩衍那》的事,于是,派刘寿康先生同我联系。出版此书是我从来没有敢梦想的事,现在简直是喜从天降,我当然一口答应。这部史诗长达二百多万字,我同刘寿康先生亲密合作,忙了一两年,终于出书,算是给中国文学界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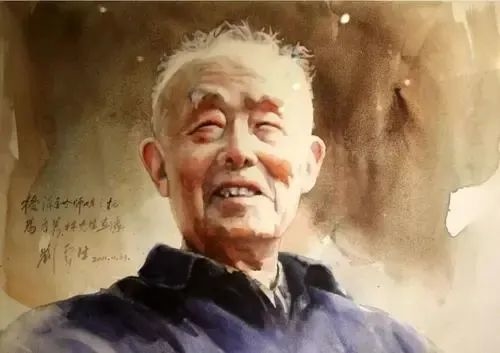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件有关《罗摩衍那》获奖的花絮。1993年,由新闻出版署主持召开了全国图书评奖大会。这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图书评奖活动。一般的手续是,先由出版社自选,报请省市出版局审查,经过筛选,再报请中央新闻出版署审查,主要是检查出版质量,重点是统计错误率,以万分之一为合格,否则名落孙山。最后由新闻出版署送交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科的评审组,经过各组内的仔细审阅和讨论,然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由小组通过,最后再由十几个小组组成的全体评委会审查,无记名投票做最后决定。手续是慎重的,评审是公正的。
我属于文学组,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都包括在内。我们组第一次开会是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把新闻出版署已经检查过的几百本书搬到会议室内,陈列在那里,供评委们阅读,不知是哪一个工作人员,由于一时疏忽,从书库中向外抱书时,将三册颇为破烂的平装本的《罗摩衍那》夹在书中抱了出来。全书是八册,不知为什么只留下这三册。就是这三册书无意中被柳鸣九教授发现了,他大为兴奋,说:“社科院评奖时,此书已经得过奖。”他坚持将此书纳入评选对象中。我作为组长,坚决反对,认为这不合手续,因而是不合法的。但是经过在我回避下的全组讨论,一致评为获得大奖的仅有的几种书之一。后来,在一次有副署长参加的小组会上,我又提出撤掉的建议,没有得逞。终于被搬进了全体评委大会的大礼堂中,但“赫然”摆着的仍是那三册颇为破旧的《罗摩衍那》,在众多富丽堂皇、装帧精美的大部头书旁,寂寞、寥落,宛然像一个小瘪三。最后竟以很高的票数通过,成为十几年来中国东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全权代表。
顺便说一句,在这同一次会上,我们小组还通过了中华书局根本没有上报的钱锺书的《管锥编》。从这两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来,小组的评选是公正无私的,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从来都是尊重评委们的意见的,从来没有妄加干涉过。
花絮讲完,我这篇文章应该打住了。我本来只想写上几百字,应付一下差事,不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三千来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并不复杂。在本文开头时我就讲到了温馨甜蜜的感觉。在这里,这种感觉竟起了作用。我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蒸蒸日上,越办越红火。我也希望,我这种温馨甜蜜的感觉能永久保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