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漪:声音介入建筑

「 我希望能够去打破边界以及我的跨界思维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转化出来,提供给更多的人作为一种养料的备份,看到更多的组合与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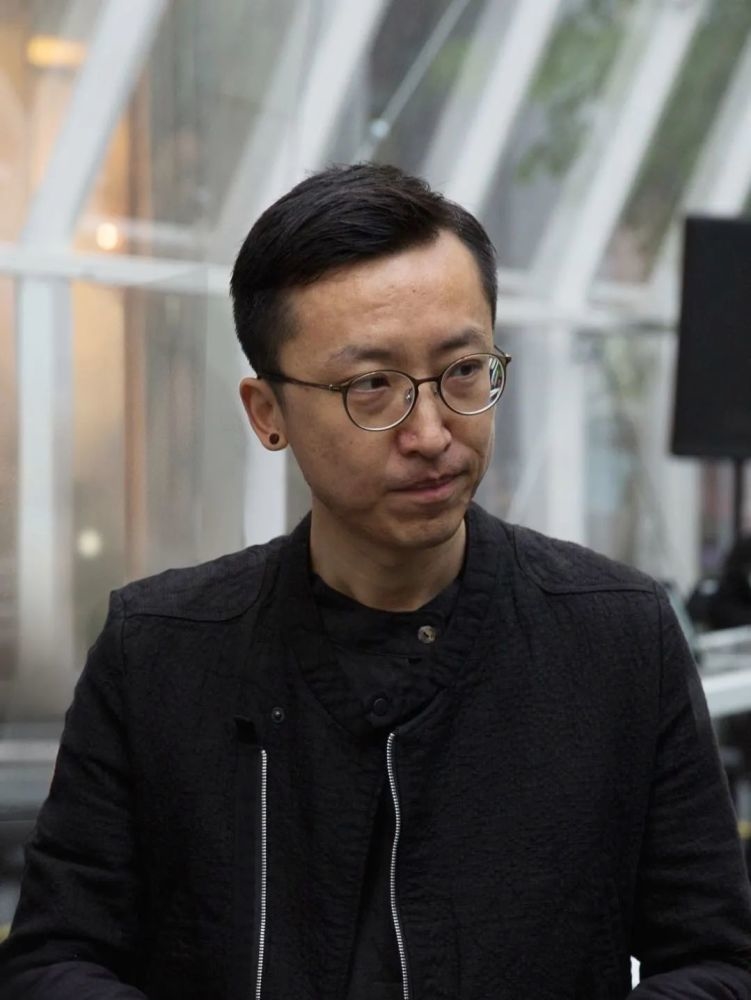
殷漪人物照 唐煜
殷漪,音乐家、艺术家、策划人。1978年出生于上海。1998年组建慢核乐队“死亡诗社”,担任贝司手兼主唱。2001年转向数字音乐创作。殷漪早期的音乐创作领域包括:音乐表演、现代舞、肢体剧场。
近年来的音乐实践主要集中于个人现场音乐表演以及音乐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探索。基于对“聆听”与“声音”深度的思考和研究,殷漪展开其跨媒介的艺术创作,作品形式包括表演、声音、影像和装置。感知、身份、文化、媒介性成为其创作焦点。对于他来说,艺术是自我治愈的良方,也是思考与行动的试金石。
AP/请问您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与正在做的事情?
殷漪
我现在最主要的社会身份还是艺术家,偏当代一点。我曾经收到这样的疑问——我的作品是否不应算作是声音作品,而是当代艺术作品。之所以这样提问,是因为大家还是习惯从材料的角度去认知和分类艺术,比如新媒体是数字化综合类的材料,舞蹈是用身体,音乐则是用声音或是乐器。但在我看来,当代艺术不应以材料的方式去划分。
我们在谈“声音”的时候,更多地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对象,其实很少会谈论听觉。针对个人而言,我更愿意使用“听觉-声音”。声音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其实和受众的听觉习惯、文化教育、生理特性等都有关。在音乐学领域中有些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真正做创作的人却不太会去关注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听”“我们为什么这样听”“我们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听”。
作为一个声音艺术家,我不仅仅是把声音当做一种材料,我的工作也不只是想着如何把声音做得更好、更精致、更有技术性,而是在整个听觉文化的构建下,去讨论声音的可扩展性和可连接性。
AP/建筑作为空间艺术,一直以来涉及到更多的是视觉方面的设计,您是如何想到通过“声音”来介入建筑设计的?
殷漪
我很早之前与建筑师朋友庄慎(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谈论过,建筑师对空间设计的理解应该如何不局限于物理空间设计,不只落在视觉层面上。从对建筑感知的角度来看,建筑设计是更加综合性、通感性的内容,包括空间、光线、声音等。
举一个例子,在咖啡馆及相类似的场所中,背景音乐其实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即能够在共享的物理空间里建立私人的听觉空间。当我们在交谈时,如果旁边有一些人在聊天,我们会受到干扰,因为我们听到的是大量的语言信息。
但音乐会冲淡那些声音中的信息,这样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于我们当下的行为,不易被外部打扰。同时,在这种场所里的音乐本身不是一种信息化的东西,你可以很自然地把它当成背景。

咖啡厅场景 ZHOU
依据以上的例子,声音空间和物理空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声音空间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不是无形的,只是不可见。那么这类“空间”是不是也可以进入建筑设计的工作范畴之内?如何进入?怎样建立方法?也许声音艺术家可以参与的。
另一方面,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如果听觉美学的具化物仅仅出现于美术馆或是当代艺术领域中,那么就限制了其被认知的广度。如果将声音艺术美学转化、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中,这个过程虽然可能是冗长、缓慢的,但是持续下来,它的认知广度会极大地扩展。
我在想象一种可能——把“听觉-声音”的美学形式与日常活动空间、生活场景结合起来,不以艺术作品视角对待它,而是潜移默化地为人们带来细微的影响,或许能够让人们意识到更多的可能性,不仅是文化生产,还包括商业等。
AP/您提到的听觉空间优化方案,是用声音来消灭声音吗?
殷漪
不是用一种声音消灭另一种声音,而是一种调和。通常我们会从生理、心理和意识形态方面感知和理解声音,并自然地去区分哪些声音是值得听的,哪些是不值得听的,自认为可以对声音进行清晰的边界划分。这种边界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也比较简单。
但如果我们更多地去感受、认知和思考,会发现不存在固定的边界,或者说存在很多不同的边界,这些边界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而不断流动。所以并不是用一些声音去消灭另外一部分声音,而是通过调和让这些声音共存,或许产生一些新的声音。
这种调和方式来自电子音乐作曲中的调制(Modulation)。但这样的工作不能又落回到音乐创作中,而是应该更多地吸纳人文社科中对于人的研究与思考。
AP/在“露台计划”中,您通过发起在法国领事馆露台播放音乐这一行为(作品《露台上的音乐》),将原本的私人空间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公共空间,这是否论证了声音能够改变空间的属性?
殷漪
空间的属性在于我们如何去使用它。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一概念,如果追溯历史,其最早是政治用语,在古希腊时期,公共空间是交流城邦事宜、公民生活问题的场所。但在今天,特别是在中国多数的城市空间里,“公共空间”已经嬗变成了“共用空间”。
这类“共用空间”又隐含经济成本最小化原则。我会把共用空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性共用空间,另一类是社会性共用空间。商业性共用空间与我们的关系比较简单,就是消费;社会性共用空间则为我们提供某种保障性功能。那么,如果我要把法领馆的私人露台变成一个公共空间,而非共用空间,应该怎么做?
公共空间的标志是在其中发生的公共生活,而公共生活的标志之一就是要发声。当我们就某些事件进行交流并发声时,就是对空间再造的一种排演,或者说实验。当然,我并不是真的要大家在法领馆的露台上讨论什么事情,而是希望通过艺术的方式,比如说音乐,引发一种公共思考。因为在那样的场合里,没有一个人会简单地、不加思考地随意播放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他一定会想“什么样的音乐适合这个地方”,这就是一种公共意识。公共意识往往是被激发出来的。
然后,当你在公共空间发声之后,你总是希望得到回应的,没有回应怎么办?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当你放了音乐,之后别人放音乐是不是对你的回应?别人的回应是一种正面的,还是一种负面的反馈?我是否还要做出回应?这也反映出了另一个问题——人在公共空间的自我选择。
在场的嘉宾或许从衣着外表看上去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从播放的音乐来讲,其实个体的差异是很大的,仔细想来存在某种相互排斥。这种排斥不一定非常强烈,或者说因为音乐作为符号而变得非常细微。这也关联到这个作品的背景:汉堡火车站通过播放古典音乐来驱赶在广场上停留的流浪汉。古典音乐能驱赶流浪汉吗?可能。因为在这里,音乐代表着文化意识形态。

“露台上的音乐”海报
AP/在这个活动中,您是否有目的性地邀请不同专业领域的人营造一个多元的社群?
殷漪
不同于“露台计划”中的其他场次,这一期(第四期)更像是我邀请大家一起完成一场表演。我们改变了邀请机制:一共16人,我与主理人Alice陈各自邀请8位。我们事先并未商量,而这两部分人事先也并不认识。
就个人而言,我希望有不同的人参与进来。我们邀请的朋友里包括了建筑师、规划师、学者、艺术家、画廊、美术馆或者其他文化机构的工作者等。对我和Alice来说,我们邀请的人都是值得来的人——他们能够意识到并主动来参与到这件事情中。
很多时候,我们把认知和感受交给一套系统。社会被画了很多小格子,人们在自己专属的格子里追求一种纵向的专业性,却缺少横向的了解和交流。而当不同专业的人因为艺术进入到彼此的场域中时,不是为了来“消费”,把你当一个对象消耗;也不是在经济效率的前设下享用生活的保障性功能;而是为了观察和交往,从中获得数据、信息,或者说“养料”。这种不同领域的人之间的交流,给到我启发。
对我来说,艺术不是一个职业,或者说至少职业不属于第一优先级。艺术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治愈的途径,这种自我治愈既包括了一种精神状态,也包括了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感受方式。

露台上的音乐01.2021,法国驻上海领事馆
(感谢正艺会惠允)
AP/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中,为什么会选择与建筑师进行多次合作?
殷漪
最初是因为朋友中有建筑师,彼此有共同的话题,平时生活走得比较近,于是通过这位朋友结识了庄慎。再后来我就和庄慎以“建筑师+艺术家”跨界合作的形式一起参加了上海当代艺术馆的“生活演习——2012建筑空间艺术展”,就此开始慢慢接触建筑师。
之后被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邀请参展(2015),基于当下建筑展的专业性为普通观者带来的门槛,我们提出以艺术的方式去看待空间,尝试在生产性空间中嵌入声音与舞蹈影像,邀请观众在展览现场用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去构建出在时间空间重叠中溢出的城市场所(作品《呼唤》)。

电子工业学校

韩天衡

老白渡

创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