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后疫情时代,如何在旅行中抵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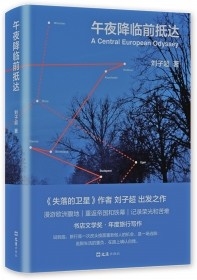

布达佩斯。组图/刘子超

的里雅斯特。

刘子超。
一章是“夏”,一章是“冬”。
从奥地利、捷克到匈牙利、意大利,从布达佩斯、维也纳到克拉科夫、布拉格。
独自踏上旅途的刘子超,就像一个幽灵,深入中欧腹地。
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的中欧,即便是在历史的长河撕扯和游移,依然保持着永恒不变的特质。
奥地利山间雪松林的松脂味,摩拉维亚啤酒的爽朗口感。人的生存经验就像历史河流中的卵石,从当下向着未来延展。
以《午夜降临前抵达》为起点,刘子超用旅行和文字,见证世界的流动:不时唏嘘于它们的变化,同时也试图发现那些被时光留下的永恒之物。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我想成为中国的海明威”
文坛硬汉海明威影响了几代美国人,也影响了刘子超,乃至成为他创作上的目标——“我想成为中国的海明威。”
海明威说,一天只要写1500字就好了。刘子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文学社。那时候,他在学校BBS上写诗歌也写小说,往往是每天写1500字就停笔,以便第二天可以接着写下去。这样的写作习惯,也在《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写作过程得到了延续--结束中欧之旅回国之后,每天按照1500字的速度,用两个月的时间写了6万字的游记,字斟句酌,构成了《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前半部分:“夏”。
海明威说,如果你想当作家的话,先当几年记者挺好的。刘子超遵循了海明威给年轻人的建议,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南方报业集团当记者,之后在《南方人物周刊》《GQ智族》等杂志的采访写作历练,给了他更多打量这个世界的机会和沉淀。踏上旅途,游历欧洲,去见识风景和人间,去见证希望和苦难,去发现世界上其他人的别样生活,刘子超觉得自己的最好选择,就是成为一位旅行作家。
传统的旅行作家,习惯于开门见山:“我们坐在万德罗博猎人们在盐碱地边用大小树枝搭成的埋伏处,听见了卡车驶来的声音。”海明威在记叙东非狩猎之旅的《非洲的青山》里,如此开篇。令刘子超比较好奇的是,海明威是如何抵达肯尼亚的呢?因为,旅行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按照刘子超的设想,如果海明威把他如何抵达的过程写出来,会和抵达后的经历一样有趣。或许,旅行与人生,都是一次次解决如何抵达的生命过程。
对于这样的人生与自我的追寻,刘子超选择了“以肉身进入现场,用文学再现旅途”。
于是,很多年后,刘子超依然记得那个阴雨绵绵的午后,那个即将开始独自漫游的午后,他很快写下了《午夜降临前抵达》开篇的第一个句子:“我离开柏林那天,下着小雨,天空阴沉得像一块陈旧的大理石。”
《午夜降临前抵达》推出之后,不仅获得了2015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奖,同时入选了当年豆瓣年度好书的榜单。
这样的旅行写作,也正如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所指出的那样:“他所见证和书写的人的境遇,刷新了我们观看今日世界的坐标和视域。而那些处在世界的边缘与夹缝中的陌生地名,也因一位中国作家的在场,与我们有了联系。”
之后,刘子超又创作了《沿着季风的方向: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程》《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还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漫长的告别》等书。
一位“当代游牧民族”的中欧之旅
在《午夜降临前抵达》里,没有“春”和“秋”,只有两个季节——“夏”和“冬”,分别记录了刘子超在欧洲大陆的两次漫游,“夏”是以搭火车的方式,“冬”是以自驾的方式。
正如美国爵士音乐家约翰·科尔特兰的著名唱片《蓝色火车》那样,一辆行驶在空濛夜色中的火车,总是令人充满遐想。作家和音乐家乘着火车旅行,由此催生了大量的音乐和文学作品。
与许多80后城市少年一样,刘子超在北京读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看火车。刘子超家附近不远就是北京北站,每次听到火车尖锐的哨声,他就希望自己能跳上那列火车,去往陌生的城市,远离熟悉的一切。长大以后,他也爱上了火车旅行。在他看来,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个场所,是出发和抵达城市的一部分,它总能以最小的风险,提供最多的可能。
乔治·西姆农的小说《看火车驶过的男人》,也深深影响了刘子超。从捷克布拉格踏上去往波兰克拉科夫的过夜火车时,刘子超甚至还回想起《看火车驶过的男人》里的一段话:“比如说,火车情结。他早已过了男孩儿那种幼稚地迷恋蒸汽车头的解读,但是火车,尤其是过夜火车,仍然对他有一种致命的吸引,总会把一些诡昧不清的念头送进他的心里。”
在夜行火车上,刘子超总有一种幽灵的感觉。因为,时空的转换具有一种魔力,而火车就是转换的载体:“午夜时分进入一座陌生城市,就像在玩一场捉迷藏游戏。有时,我甚至觉得一座城市的地图在午夜都会悄然变异:小巷折叠,大路转弯,一些建筑凸现出来,一些建筑则暗自隐去。”
一段不赶时间的旅行,漫不经心的自驾游是自由自在的。翻越那些山林,穿越那些平原,穿行那些城市,刘子超有了更多的感悟:“在旅行中,我收获喜悦,却不必害怕乐极生悲;我见证苦难,却不必担心承担重负。没人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这种自由自在的身份、若有若无的归属,大概正是如今社会最为稀缺的东西。”
很多时候,刘子超都喜欢把自己称作“当代游牧民族”。可能跟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有点像,没有固定职业,虽然自由却没有特别的保障。总在移动的古代游牧民族,每年都要带着简易的行李,从一个夏牧场移到冬牧场。而刘子超,则是带上一个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拉着一个行李箱,就独自踏上旅途,深入欧洲腹地,展开一场逃脱和寻找的漫游。
在意识流里追寻大师的脚步
有些城市会不断衰老,有些城市永远年轻。
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在简·莫里斯的《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的书里,被称为“流亡之地”,普鲁斯特、乔伊斯、弗洛伊德……在这座城市逗留、游荡过的作家、艺术家可以开出一串很长的名单。
“早上潇潇洒洒,下午忙忙碌碌,晚上乱乱糟糟。”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曾在此煎熬了近10年,潦倒中写就《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日后他追忆道:“的里雅斯特啊,吞噬了我的心肝。”
的里雅斯特虽然历经沧桑,依旧保留了众多的历史建筑,犹如时光倒流,犹如时代琥珀。
刘子超在的里雅斯特的大运河边,遇见了乔伊斯的铜像,还经过了乔伊斯住过的一处公寓。这处公寓已经变成了以乔伊斯命名的旅馆。刘子超想看看乔伊斯住过的房间,却发现被一位美国作家长租下来了,据说他要在这里过冬,写一本书。或许,乔伊斯的故居,能够给美国作家更多的灵感吧。
皮罗纳蛋糕店,早在1905年的时候,乔伊斯就喜欢来这里买杯最便宜的咖啡,翻阅报纸,看看新闻和招聘启事。令人称奇的是,这家蛋糕店还在营业。于是,刘子超也进去点了一杯咖啡,要了一份奶油蛋卷,感受乔伊斯在这里开始写作《尤利西斯》的氛围。朝圣之旅还可以延续至圣马可咖啡馆,当年也是乔伊斯和一众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
乔伊斯被誉为意识流小说的鼻祖。还在读高二的时候,刘子超就深受乔伊斯的影响,借鉴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写了一篇意识流的作文《一个青年作家的画像》,参加了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那次新概念作文大赛,刘子超拿到了二等奖,郭敬明拿到了一等奖。
对话
“我想回到14年前的长沙冬天”
“穿越波兰边境,进入塔特拉山,此地到处是毛榉和冷杉。一个斯洛伐克人说,夜幕降临后,会有鹿群经过。”《午夜降临前抵达》里提到的这条微博,常常被读者打卡。
为这种好运感到惊喜的刘子超,借助《午夜降临前抵达》再版的机会,重新审阅并修订了书稿,特制精美手绘路线地图,新选26张实地摄影,图文呈现立体旅程。新增2021版后记,在后疫情时代反思旅行的意义:从广阔的世界汲取经验,用文学的方式加以呈现,在旅行和写作中确认自我。
潇湘晨报:恭喜刘老师,“豆瓣年度好书”《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获得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的荣誉之后,10月17日又被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评为非虚构作品双子星奖。刘老师今年是拿奖拿到手软啊。对于自己的作品,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刘子超:情感上最看重的是《午夜降临前抵达》,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本书,就像长子一样,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是从那本书开始对旅行文学这一文体的探索,书里的很多情绪和思考,是那个年纪才会有的,现在来看十分怀念。写作上更成熟的是《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为这本书花费的精力也最大。
潇湘晨报:《午夜降临前抵达》是你的出发之作,如今重新修订增补,主要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这些年来,对于旅行意义的反思,对于自我的寻找,是不是有了新的发现?
刘子超:重新修订是因为恰好版权到期,可以出一个更完美的版本,希望它依旧能够陪伴读者度过漫长的时光。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机会重新思考这些年来的旅行和写作。我想,对我来说,旅行和写作都是一种对抗虚无、确认自我的方法,人生意义在其中自然而然地展现。
潇湘晨报:你的文字为读者揭开了世界各地的神秘面纱,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世界的窗口。如果故地重游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城市?如果长期居住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城市?
刘子超:14年前的冬天,我在长沙待过一个月,在新华社实习。那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挺怀念那种感觉,也挺怀念那个时候的长沙。如果可能的话,我想重新回到那时的长沙看看。长期居住的话,我想选择柏林、东京、上海、大理、曼谷。
潇湘晨报:你一直认为,旅行作家应该“以肉身进入现场,用文学再现旅途”。写东西的旅行者和去旅行的作家,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刘子超:旅行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写作让我发现大量的世界经验还鲜有中文严肃表达。我希望用文字再现旅程,我希望带领读者进入一种“双重叙事”:一个是作为叙述者的“我”,另一个是更庞大的外部世界。写东西的旅行者和去旅行的作家,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你的第一身份是什么。前者兴之所至,后者则有更高的文学追求。我希望自己成为后者:从广阔的世界汲取经验,在旅行和写作中确认自我。
潇湘晨报:你去过那么多国家,主要是用哪些语言跟当地人交流?出现在你作品中的人物,有没有经常保持联系,乃至成为朋友的?
刘子超:英语是最主要的交流语言。我也会学一些当地语言,学过法语、俄语、乌兹别克语、韩语等。我和作品里写到的很多人都有联系,有时候会在社交网络上聊聊彼此的近况。比如《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里写到的塔吉克小伙“幸运”,我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认识了“幸运”,他给我当导游也跟着我学汉语。后来,他来到中国读书。去年我跟他吃了顿饭,聊了疫情,也聊了近况。今年他离开中国,去了俄罗斯,还交了一个俄罗斯女友。不过,他还在学习汉语,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回来。
潇湘晨报:旅行是一件消耗很大的事情,不仅仅需要时间和精力,还需要金钱的支持。作为自由职业者,你的旅行,会有费用方面的担心和考虑吗?
刘子超:当然会有。所以必须建立与自己工作相配套的生活方式。我从游牧民族身上得到了很多启发:他们在生活中只保留最重要的东西,不会有那么多的奢侈品,这样才能保持移动的便捷性。我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潇湘晨报:你曾经从事过新闻传媒行业,调查记者的工作经历,对于你的旅行和写作,有没有特别的影响或者说帮助?
刘子超:我很感激十多年的记者经验,它给了我很多其他作家所没有的阅历。怎么样倾听,怎么样与人交谈,怎么样获取信息,来到一个陌生之地后怎么样找到突破口——这些都是记者的经历教会我的。
潇湘晨报:某种程度上,你的经历跟海明威有点像,他当过记者,也当过旅行作家。以后,你会不会像他那样写虚构类小说?
刘子超:是的,会有写小说的可能。我想写与众不同的小说,无论是语言上还是经验上。旅行给了我很多启发,见识了很多平时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些东西最终沉淀下来,会转化成小说的素材。我在关注着那个沉淀的进度。
潇湘晨报:在新冠疫情仍旧肆虐的当下,作为旅行作家,你近期会有外出旅行的计划吗,在个人防护方面,会不会有特别的准备?
刘子超:今年4月份我来到了西藏,计划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一年,如今已经过半了。这段时间大都在藏地行走,了解了很多以前完全不了解的历史和文化,也见识了很多壮美的风景。个人防护方面,我已经打了疫苗,在公共场所会佩戴口罩,随身带着洗手液。
潇湘晨报:接下来有没有新的写作安排,在题材领域或者写作手法方面,会不会有新的突破?
刘子超:应该会有突破,敬请期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