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纸上》:美的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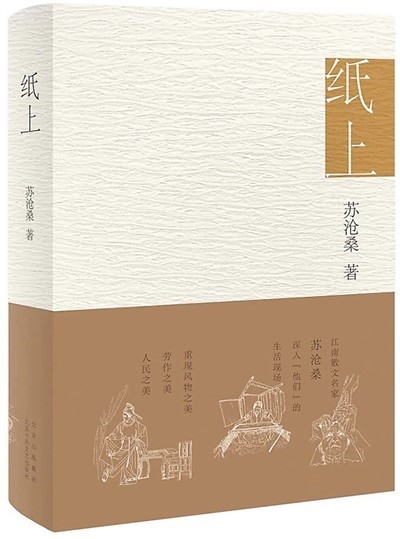
作者:行超
沧海桑田,“苏沧桑”这个名字,似乎天然地赋予了作家一种如影随形的独特气质:柔软的、优美的、抒情的,却自有一种生命的慨叹贯穿其中。《千眼温柔》《银杏叶的歌唱》《一个人的天堂》《风月无边》《所有的安如磐石》,这些散文集的名称,一次次昭示着这位江南女作家对于“美”的追求,也正是在这种追求中,苏沧桑的散文逐渐成为当下美文写作的典型代表。
苏沧桑的散文新著《纸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以中国南方珍贵的“非遗”文化、手艺行当、风物人情为基本元素,写丝绸、茶叶、戏曲,写纸、写蜜、写酒、写船娘……所写之物,自带一种中国古典之美。苏沧桑的文字不疾不徐、典雅蕴藉,正如她所塑造的那个物质世界一样,“充盈着水汽和灵气”,融汇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审美世界。
探究《纸上》之“美”,不难发现,苏沧桑笔下事物的“美”并不仅限于自身,更包含了人的主观因素,是“自然的人化”。通过人的劳动,蚕丝抽织成丝绸,毛竹变为了纸张,蜂箱中酿出了蜜,千亩茶园一片清新的嫩绿……作者耐心描摹了“美”的产生过程,注目于创造美的过程中那些普通劳动者所倾注的巨大心血与付出。于是我们看到,为了造出失传已久的开化纸,朱中华尝遍人间艰难,捞纸师傅徐洪金在纸浆水中浸泡了45年的手掌,“比白纸更白”;经年累月的采茶,让祝海波的岳母、黄建春的妻子练出了“一双蝴蝶般在茶尖上飞舞的手”,“每一个指甲都被茶汁浸染成了黑色”;靠天吃饭的养蜂人,如吉普赛人般流浪天涯,步步惊心。沈建基曾经被酷暑中暴躁的蜜蜂蛰了100多个包,险些丧命;郭靖曾被蜜蜂蛰进脖子上的一根血管,中毒昏厥……“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向往,对于美好事物的描摹,更是一代代作家共同的追求。只是大多数时刻在“美”的面前,我们一味地欣赏、享用,无心探究“美”的来路,更不知在“美”的背后,竟然蕴藏着如此的惊心动魄。
朱光潜先生在谈及“美的本质”时曾说:“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态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性质。”的确,真正的“美”必然灌注着某种让人产生共鸣的主观精神,如此,“美”才有可能恒久、才有可能富有力量。《纸上》跳出了单纯对客观“美”的欣赏,而是深入阐释其背后的主观成因。在苏沧桑笔下,比蜂蜜更甜、比清茶更香、比开化纸更珍贵的,是无数普通人的劳动之美、人性之美。
《跟着戏班去流浪》一文聚焦基层越剧演员和戏班,苏沧桑“跟着”的不是被舞台光环照亮的著名演员,而是一辈子都可能生活在光环之外的小演员,他们是越剧世界中“沉默的大多数”,但正是他们,聚合成为越剧的根基。演员杨佩芳,生于绍兴一户贫寒人家,10岁不到就跟着戏班流浪,初衷不过是“吃饭不要钱,还天天有戏看”。多年之后,杨佩芳成了当红小生,然而“从那时起,一杯咖啡跟了她一辈子,胃痛跟了她一辈子,孤独也跟了她一辈子”。因历史的误会,她被剧团开除,一代名伶最终成了营业员、收电费的。多年后,对于曾视如生命、又让她遭遇命途坎坷的越剧,她似乎只是变了爱的方式,而“越剧不失传,是她最大的梦想”。《跟着戏班去流浪》中,苏沧桑着力探究的是被越剧之美所遮蔽的人们。正是在这些籍籍无名的演员身上,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磨砺中,我们看到了更为坚韧、更为恒久,也更令人动容的美。
中国文学的美文传统其来有自,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梁启超提出,中国的美文传统有两大起源:一是古代歌谣、汉魏乐府等民间创作,二是《诗经》到建安之前的诗。古典文学中的韵文、诗歌尤其集中体现了美文的特点。五四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现代白话美文更以其抒情性、审美性,构成了“文以载道”理念的补充与反叛。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一些美文作家越来越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甚至走入了学者解志熙所说的“唯美化的偏至之途”。这些作品中,“美”是虚浮、单薄、脆弱的,美成了一道枷锁,束缚住了作家的思想和手脚。与之相比,散文集《纸上》不仅写出了丝绸的精美、越剧的动听、茶叶的清香,更写出了美的“反面”:那些艰辛的付出、粗糙的皮肤、患病的身体、坎坷的人生,它们看起来是“不美”的,但正是这些“不美”的瞬间,才让真正的“美”有了根基,变得可触、可感,进而可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散文集《纸上》完成了美的突围。
(作者:行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