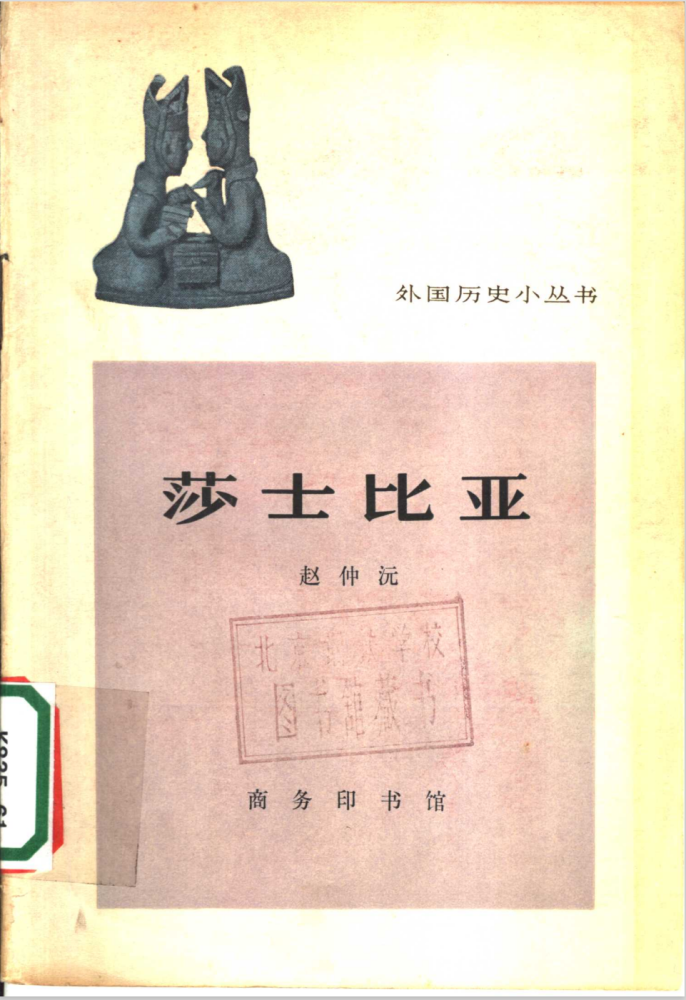洪子诚|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编者按
1964年是莎士比亚诞辰的400周年,但当时的重读莎士比亚不止于纪念的意图,更大程度上成为各种解释者的政治发挥场所,折射出冷战和国际共运分离的深刻印痕。在“保马”今天的推文《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中,洪子诚老师揭示出,面对国际混乱的意识形态大局,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做出“两个批示”,因此1964年后,当代中国没有延续之前莎学等外国作品研究的发展路线,而是终结了相关的纪念制度,以社会史分析的批判文本与新批评、人道主义批评等划清界限,强调历史规律下莎士比亚的局限性。
这一“以当下看过去”的方法不幸陷入僵化的解读模式,不过有趣的是,它在80年代被同一批使用者立刻翻转,强调以过去看当下,莎士比亚屹立于高峰,予当下以知识。现在的我们便与他们、与莎士比亚隔着这层层历史的迷雾,为此重返1964年,重返主席的批示亟需展望,而其中的根本基点在于,“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这是胡说八道”!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感谢洪子诚老师授权“保马”转载!
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文|洪子诚
1964,莎士比亚年
莎士比亚1564年4月23日出生于英国沃里克郡斯特拉福德镇。1964年是他诞辰的400周年,世界很多地方的文化界称这一年为“莎士比亚年”。法国《费加罗文学报》摩尼叶[1]的文章《莎士比亚年》中说:
“毫无疑问,从墨西哥到日本,从西班牙到苏联,从澳大利亚到人民中国,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庆祝他的生日。也许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里只要那里沾上一点戏剧的味道,也需要庆祝这个点燃四百支生日蜡烛的周年。这个光荣超越国界,超越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界限。”[2]
这一年的4月,许多国家都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在他的故乡斯特拉福德镇,由多个国家捐款成立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心在他的故居旁边建立,此后成为莎士比亚重要的研究机构。纪念活动期间,各国剧团在斯特拉福德和伦敦,连续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英国报刊也刊载相关的文章和研究论文。据周煦良辑录的信息称,英国三个文学杂志《英国文学评论》、《论文与研究:1964》、《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都推出了纪念专辑,刊登论文和书评超过30多篇[3]。苏联文艺界也表现了极大热情。文艺报刊如《戏剧》、《涅瓦》、《星》,以及《文学报》和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都发表一系列纪念文章和学术论文。

《莎士比亚戏剧集》,朱生豪译,作家出版社,1954年。
中国文艺界在纪念的筹备上也不例外。自60年代初开始,相关机构出版、演出和研究论文的撰写计划就开始进行——这延续了1949之后文艺界对莎士比亚的重视。1949之后,文艺界虽然推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特别是俄苏文学,但对西方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艺并未采取隔离、排斥的态度。相反,比起三四十年代外国古典作家翻译、研究上,“当代”取得更大的进展;莎士比亚的翻译和研究也是这样,以至有的研究者称1949年到1965年为“中国莎学”的“繁荣期”[4]。这个时间,除了大家熟知的1954年朱生豪12卷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之外,单行本的莎士比亚戏剧、诗歌也有数量颇丰的印数。如曹禺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方平的《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威尼斯商人》、《亨利五世》,吕荧的《仲夏夜之梦》,卞之琳的《哈姆雷特》、吴兴华的《亨利四世》,方重的《理查三世》,还有曹未风译的11种——《安东尼与克柳巴》《尤利斯·该撒》《罗米欧与朱丽叶》《凡隆纳的二绅士》《奥赛罗》《马克白斯》《汉姆莱特》《第十二夜》《错中错》《如愿》《仲夏夜之梦》。诗歌方面,有方平的长诗《维纳斯与阿董尼》,屠岸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这个期间的研究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孙大雨、顾绶昌、方平、卞之琳、李赋宁、陈嘉、吴兴华、方重、王佐良、杨周翰、戴镏龄、赵澧等都有多篇研究论文发表。舞台演出方面,从1954年到1962年,先后有《无事生非》、《哈姆雷特》、《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出现在京沪的话剧舞台上。而电影译制片则有《王子复仇记》(英,1948)、《奥赛罗》(美、意、法、摩洛哥,1951)、《第十二夜》(苏,1955)、《仲夏夜之梦》(捷克斯洛伐克,1959)、《理查三世》(英,1955)、《罗密欧与朱丽叶》(意、英,1954)等;其中《王子复仇记》影响最大[5]。1954年莎士比亚诞辰390周年的时候,中国有相当规模的纪念活动开展——出版朱生豪12卷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刊登了曹未风、熊佛西、穆木天、方平、施咸荣等的纪念文章。因此,可以预想1964年将会有纪念的盛况出现。

1958年,电影《王子复仇记》(Helmet,1948)由上影译制片厂译制。视频为孙道临配音的哈姆雷特独白片段。
纪念计划受挫
一般说来,文学艺术家的纪念项目,无非是著作翻译出版,纪念会和展览,还有研究、评论文章的撰写。莎士比亚400年纪念的筹划也大体这样几项。其中最重要是全集的出版。朱生豪由于贫病,莎剧在未及译完时于1944年12月辞世。1961年,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翻译家施咸荣[6]向社里提出,应借莎士比亚周年纪念之机出版莎士比亚全集[7]。出版社同意并很快付诸实施:聘请吴兴华、方平、方重校订朱生豪已译的31个剧,增补未译的六个历史剧:方重译《理查三世》,方平译《亨利五世》,张益译《亨利六世》(上、中、下)、杨周翰译《亨利八世》。除戏剧外,并计划将中译的诗歌编入,拟收张若谷的《维纳斯与阿都尼》,杨德豫的《鲁克丽斯受辱记》,梁宗岱的十四行诗,以及黄雨石译的四首杂诗。[8]

《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1964年,戈宝权在《世界文学》上预告新编全集即将出版[9]。但由于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这一预期最终落空——全集推延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得以问世[10]。各地原先的莎剧演出计划也大多取消。1962年底,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开始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纪念节目,不久就中止,黄佐临转而投入他认为更需要“全身心地”投入的《激流勇进》的排演——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创作的表现工业跃进的现代题材话剧[11]。1963年1月4日,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在新年文艺界座谈会上,请柯庆施(上海市第一书记)到学院看戏被拒绝,说“你们戏剧学院再演名、洋、古,我不看”;在这次座谈会上,柯庆施提出“写十三年”的著名说法[12]。1963年年底,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决定取消演出《威尼斯商人》的纪念计划13。复旦大学外文系林同济排演全本《哈姆雷特》的设想最终也未能实现。据相关资料,在1964年4月,只有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的外文系师生,在学校内部演出莎剧片断,举办小型的展览[14]。
与50年代和60年代初纪念文化名人的惯例迥异,1964年4月,既没有纪念会的召开,除了学术研究刊物(如《文学评论》和大学学报)外,《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主要报刊均没有正面的莎士比亚纪念的报导、文章。《人民日报》和两份内部发行的资料性刊物(《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只有批判性的文字。《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8期选登英、法学者的两篇文章时,有这样的编者按语:
今年是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发表了大量“纪念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们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正在竭力宣扬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文艺理论,例如宣扬文艺不是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作者感情的表现;宣扬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伟大”在于他的剧中人物的“人性基础”,等等。……我们将在这一期选译了两篇“纪念文章”,让读者研究批判[15]。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1964年,第8期。
《人民日报》3月12日的《莎士比亚的生意经》[16], 则揭露资产阶级如何借纪念敛财致富,将莎士比亚当作摇钱树。在引了《雅典的泰门》“要是我们放过有利可图之机,那就未免太对不起我们自己了”的台词之后,说莎士比亚在他逝世三百多年之后,哪里会料到不是在雅典,而是在英国,“那些所谓‘莎士比亚企业’是怎样准备利用这位伟大诗人诞生四百周年的机会大发其财”:
据说,“莎士比亚企业”中最主要的企业——斯特拉得福的“莎士比亚故里托拉斯”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先是收购了诗人出生的房屋,接着又陆续把一度属于诗人的岳父、诗人的女婿甚至诗人母亲的祖父的房屋也买了下来,作为摇钱树。另一家有关的企业是哈佛大厦,它抢购了诗人外祖父的房屋,进行同样的业务来同这个“托拉斯”竞争。他们用尽各种商业招徕术招引游客,在1961年中来自海外的访问者就有十七万。围绕着这个“主要业务”,其它“莎士比亚企业”在诗人的故乡及其附近地区也应运而起。从旅舍车行,到饭馆酒楼,甚至是杂货店、裁缝铺,纷纷把莎士比亚作为自己的财源。整个“莎士比亚市场”每年的收入,看来是相当可观的;《经济学家》杂志只公布了其中的外汇收入部分,数字就达五十五万英镑之多。
……

袁先禄,《莎士比亚生意经》,载于《人民日报》,1964年3月12日。
诗人的生日大受“重视”,而诗人的作品却遭到冷遇,这种现象在目前的英国出现倒也并不令人奇怪。……莎士比亚如果泉下有知,对于这些情况将会说些什么呢?《雅典的泰门》一剧中的另一句台词,好像是诗人专用来呵斥目前那些别有用心地要“纪念”他诞生节日的逐利之徒的。那就是:“滚开……你们这些奴才,你们是为着黄金而来。”
周年纪念“制度”的终结
在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中国也没有举行纪念会,而按照50年代的惯例,本来应该有相当规模的会议召开。这里说的“惯例”,也可以理解为自50年代初形成的不成文“制度”:世界著名作家、艺术家的诞辰、逝世周年由国家相关部门举办纪念会。这一“制度”的形成,基于当时扩大国家世界影响,通过文化交流以增进与各国的关系方针,也与五六十年代文艺界领导者的西方古典文化素养有关。这个“制度”的形成,又直接关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文化措施。1950年在芬兰赫尔辛基成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外围组织,虽说主要由苏联共产党中央控制,由于目标在于广泛团结世界进步、爱好和平的人士,组织构成和工作策略具有一定的包容、开放性。从1952年起,和平理事会每年根据理事的推荐,确定该年度诞辰或逝世周年的著名文艺家、科学家为“世界文化名人”,由各国的和平委员会主持举办各项纪念活动。50年代初任职于文化部对外联络局的戏剧家洪深[17]当年提供的信息:
1952年11月7日,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关系、利用1952年假期从事和平事业和伟大的文化周年纪念的决议”。其中关于周年纪念的部分,“建议各国举行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茅盾提议),达芬奇(按系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诞生五百周年纪念(爱伦堡提议),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多尼尼提议)以及阿维森纳(按系阿拉伯著名医生)逝世一千周年纪念(许多国家的医生共同提议)”。决议并谓,“有了这许多措施,各国和平委员会就能够使得一地文化界人士和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关心作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的发展。”[18]
世界和平理事会这一决定,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在形成50年代到“文革”之前对西方古典文化开放的格局起到推动作用:这对“当代”文艺面貌必定产生影响;至少是作家和文学读者的得益。某些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理念可能被屏蔽或忽略的作家、艺术家,也意外得到彰显。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如詹姆斯·乔伊斯。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纪念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中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古巴作家马蒂。12月30日,为了配合这次纪念活动,我国邮电部发行一套《世界文化名人》纪念邮票。
从1952到1963 年,中国文化界举办的高规格[19]外国“世界文化名人”(主要由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但也不限于这一范围)的周年纪念会目录是:
1952:雨果(诞生150周年)、达·芬奇(诞生500周年)、果戈理(逝世100周年)。
1953:高尔基(诞生85周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15周年)、哥白尼(逝世410周年)、拉伯雷(逝世400周年)、何塞·马蒂(诞生100周年)。[20]
1954:德沃夏克(逝世50周年)、亨利·菲尔丁(逝世200周年)、阿里斯托芬(诞生2400周年)。
1955:惠特曼《草叶集》(出版100周年)、塞万提斯《唐·吉诃德》(出版350周年)、席勒(逝世150周年)、 密茨凯维支(逝世100周年)、孟德斯鸠(逝世200周年)、安徒生(诞生150周年)。
1956: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诞生130周年)、小田等杨(雪舟等杨,逝世400周年)、富兰克林(诞生200周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150周年)、迦梨陀娑(生卒年不详)、海涅(逝世100周年)、莫扎特(诞生200周年)、居里夫妇(居里夫人1956年逝世)、伦勃朗(逝世350周年)、肖伯纳(诞生100周年)、易卜生(逝世50周年)、弗兰科(乌克兰诗人,逝世100周年)。
1957:格林卡(逝世100周年)、布莱克(诞生100周年)、朗费罗(诞生150周年)、哥尔多尼(诞生250周年)、考门斯基(捷克教育家,《教育论著全集》出版300周年)。
1958:雅沃罗夫(保加利亚诗人,诞生80周年)、米吉安尼(阿尔巴尼亚诗人,逝世20周年)。
1959:穆索尔斯基(诞生120周年)、亨德尔(逝世200周年)、彭斯(诞生200周年)、达尔文(诞生150周年)、斯洛伐茨基(波兰诗人,诞生150周年)、达库尼亚(巴西作家,逝世50周年)、席勒(诞生200周年)、肖洛姆·阿莱汉姆(诞生100周年)、瓦普察洛夫(保加利亚诗人,诞生50周年)。
1960:契诃夫《诞生100周年》、比昂森(挪威戏剧家,逝世50周年)、马克·吐温(逝世50周年)、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笛福(诞生300周年)、缪塞(诞生150周年)。
1961:培根(诞生400周年)、谢甫琴科(逝世100周年)、多明戈·萨米恩托《诞生150周年》、朴仁老(朝鲜诗人,诞生400周年)。
1962:赫尔岑(诞生150周年)、詹姆斯·乔伊斯(诞生100周年)、洛卜·德·维迦(诞生400周年)。
1963:世阿弥(日本戏剧家,诞生600周年)、马雅可夫斯基(诞生70周年)。
自1964年起到“文革”结束,中国就没有再举行过外国作家、艺术家的周年纪念会,“当代”这一周年纪念“制度”就此终结。原因并不复杂,就是1963年开始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和大批判运动的展开。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发表两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开始的文艺界整风,清理、检讨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的热心提倡。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载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28日。
“荒谬”的莎士比亚
《人民日报》的《莎士比亚生意经》指责英国热衷于借周年纪念敛财,而不关心作品(出版、演出、研究),事实并非如此。据梁实秋《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纪念文集》提供的资料,当年许多国家除在本国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外,还选派剧团到英国,在他的故乡的纪念剧院演出一连几个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也在巴黎召开纪念会,由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21]做主题发言。在英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周煦良撰写的文章指出,英国三个文学杂志《英国文学评论》、大英学会的《论文与研究:1964》、《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都推出纪念专辑,发表的论文和书评30余篇,内容涉及作家传记、版本、传播、剧场布景和演出语言等问题。早期版本排字工人和校对人对存世剧本文字产生的影响得到关注。新国家剧院导演威廉 · 盖斯吉尔的《现在的莎士比亚演出》一文,在谈到演出革新时,特别提到柏图尔德·布里希特(现通译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专辑还发表了乔治·卢卡契的《剧院与环境》的文章,讨论了莎剧演出的布景问题[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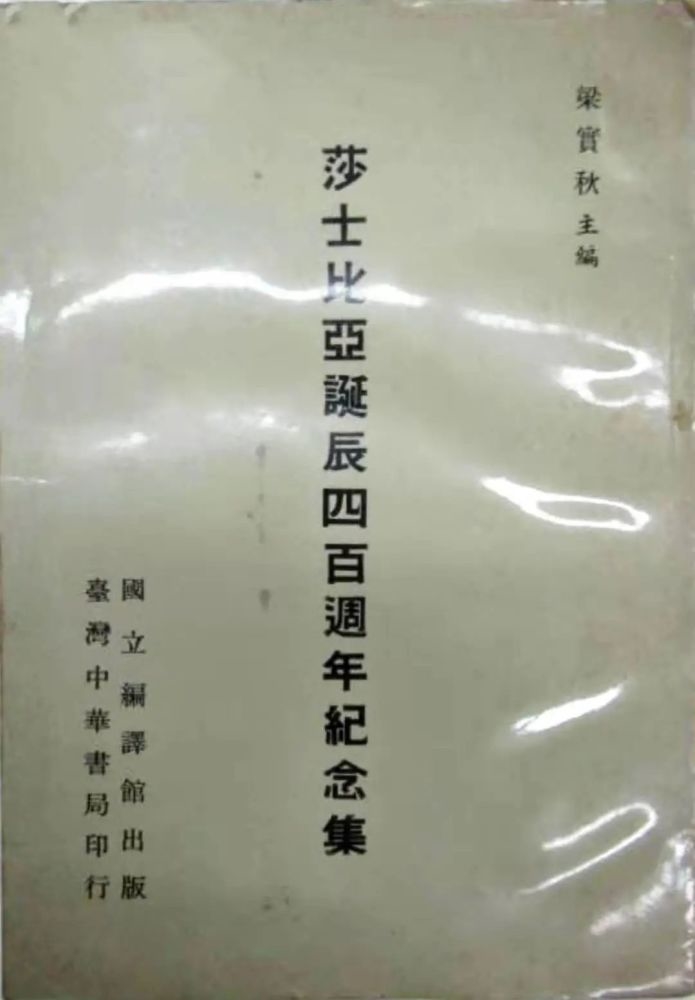

《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集》,梁实秋主编,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
《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译,远东图书公司,1968年。
事实上,莎士比亚400周年纪念时,无论是中国,苏联,还是英国等西方国家,并不缺少论文的发表,问题在于文化、学术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批评所呈现的关注点和阐释方向的分歧。摩尼叶认为,对莎士比亚的热爱、重视超越了国家、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界限。需要补充的是,这种热爱、重视也必定留下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印记;在1964那个时间点,更存在冷战和国际共运分裂的深刻印痕,而莎士比亚戏剧、诗歌的丰富、复杂,也为持各种哲学观点、各种政治立场的解释者提供他们驰骋的场地。正如赵毅衡在《“荒谬”的莎士比亚》中所说,“德国的莱辛用他来召唤‘狂飙’,法国的雨果用他来与古典主义决斗,英国的柯勒律治用他来为浪漫主义张目,俄国的普希金用他来清算前任导师拜伦,而别林斯基用他来为现实主义提供范例。”虽然如此,赵毅衡引用赫尔德的话:他“高高地坐在一块岩石顶上!他脚下风雷暴雨交加,但他的头部却被明朗的天光照耀着!——他的岩石宝座下面,有一大堆人在喃喃细语,他们在解释他,拯救他,判他罪,崇拜他,诬蔑他,翻译他,诽谤他,而他对这些一概听不见。”[23]
关于莎士比亚的地位和作品的“矛盾性”,摩尼叶的《莎士比亚年》也有这样的描述:
他的作品里有诗和散文,喜剧和悲剧,心理学和阴谋,形而上学和政治,通俗悲剧中的凶杀和哀诉,也有对于生命和行动的可能理解和不能理解的意义进行最高超、最隐秘的沉思,有生命力和衰落,平庸和优美,火热的情欲和天使般的纯洁,平民和贵族,小说和神话剧,矫揉造作和粗犷,不可思议和理性,野心,复仇,怜悯,崇拜,最粗暴的自我肯定和最温柔的自我否定,人的意志和来自大地和黑夜的宇宙宿命论,蛇诱惑夏娃的古老传说和对智力的各种最新的诱惑,丰富富饶的生活和摧毁性的嘲弄,“万有”和“虚无”。
这个看法,呼应着雨果在纪念莎士比亚诞生300周年时说的话:“莎士比亚具有悲剧、喜剧、仙境、颂歌、闹剧、神的开怀大笑、恐怖和惊骇……他达到两极,他既属于奥林匹亚神界,又属于市场上的剧院。任何可能性他绝不缺少。”[24]
那么,在1964年这个时间,按照赫尔德说法,各路“为了一种事业或者一个特殊的真理”的人马,从混杂、丰富的莎士比亚那里将挑拣什么,他们将怎样“联合他, 拉拢他, 动员他 , 使他参加自己的队伍呢 ”?
1964,怎样联合、拉拢莎士比亚
英国学者海伦·加德勒[25]试图检讨20世纪莎士比亚研究的主要征象。在《艾略特时代的莎士比亚》[26]中,他描述了1916莎士比亚逝世300周年纪念以来,莎剧研究被艾略特文学批评观念笼罩的情况。他说,这个时代的研究虽然兴趣广泛多样,但也有特出的“学术气候和文学气候”。在艾略特1917年的《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影响下,莎士比亚批评出现两个倾向。阐释离开了作家而专注文本,并转向“空间的研究方法”,在人物、情节下面寻找“意象图案”;另一是对热衷于内心和精神分析。加德勒说,这是将这个时代最高文学成就的象征诗歌拿来评判戏剧:“在象征派诗歌里,所有的人物都只是面具或者是诗人情感的客观化象征”;这种方法“恰恰离开戏剧最远”,
……艾略特先生支配的时代的莎士比亚批评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它忽视了或者低估了任何一个世纪,以及本世纪任何一个普通人所承认的莎士比亚最高才能,那就是他有一种本领使他的剧中人具有独立的生命,他的想象力是无限宽大而慈悲的,以至那些充斥他想象世界的最卑鄙或者最可笑或者最软弱的人都被赋予表达自己的才能和站在自己的地位发言的权利。
这些批评性描述,流露了加德勒对风靡一时的寻求文本内部统一性的“新批评”的不耐烦,表达了从开阔的“文化”地界上探究这个巨人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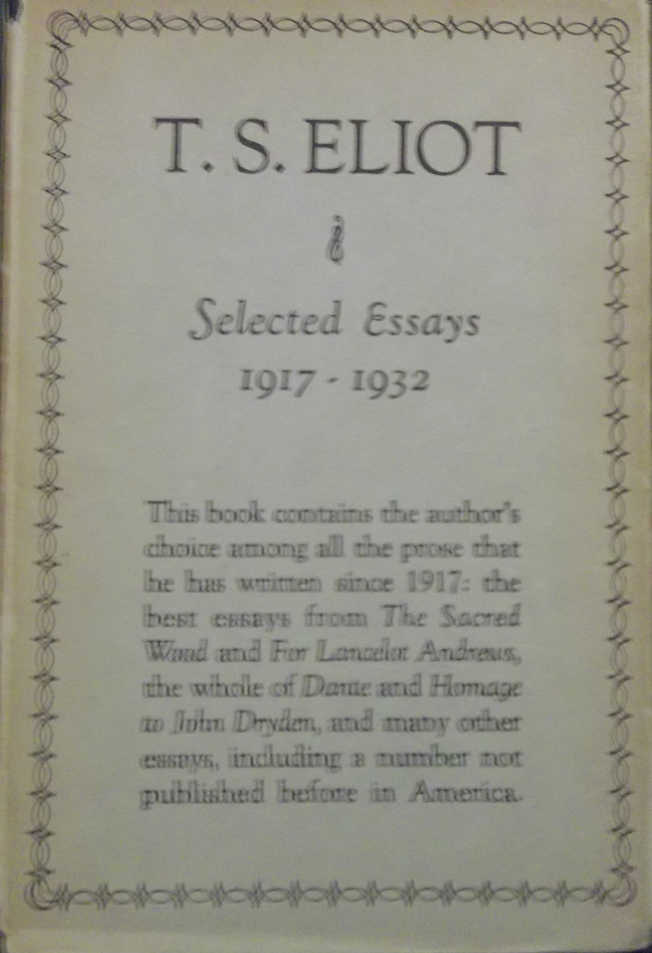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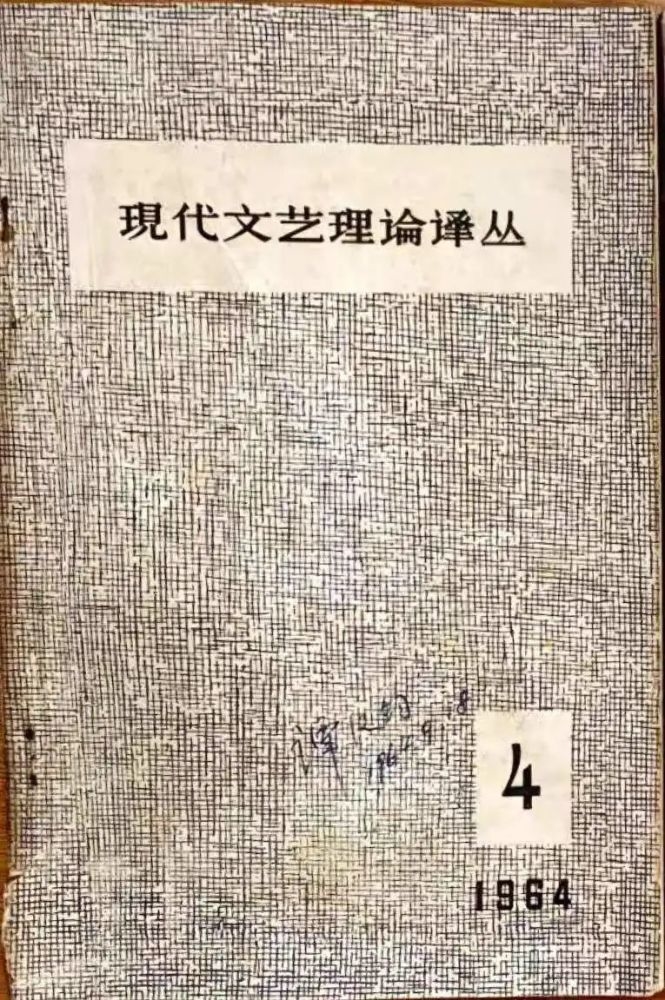
T.S. Eliot,Selected Essays 1917-1932,Harcdourt, Brace and Company,1932.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4期。
法国“右翼学者”的摩尼叶坚持从人性上来说明莎士比亚的价值;对于“东方”将莎士比亚当作“社会的控诉者”这一定位,他笔带讥讽说,如果这样,“人们还是满足于布莱希特的戏剧吧,因为布莱希特的戏剧比较容易上演”。摩尼叶说,“他是街头杂剧作家, 他也是哥尔多尼; 他是卡尔德隆, 也是莫里哀; 他是现实主义作家, 也是浪漫主义作家; 他是埃斯库罗斯, 也是缪塞; 他是皮蓝德娄, 也是贝克特”——
可是莎士比亚的真正伟大并不在于他的作品内容丰富多采, 也不在于他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语言和无限的矛盾, 更不在于他的剧中人以现代的眼光来注视他的不朽剧目的紧张场面和感情。他的真正伟大在于他的剧中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坚强地和人性的基础根连。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 是一对和蔼的青年的高贵热恋, 可是从这件事的几乎是伤风欺俗的本相说来, 从它的绝对普遍性说来, 它也是而且首先是两性互相吸引的原始冲动。李尔王在他的死去的女儿郭德莉亚面前哀恸, 这是人类痛苦达到最庄严的状态 , 可是这也是野兽在被杀害的幼兽面前的悲呜。——还有奥赛罗,麦克佩斯, 在他们倒下去的时刻 , 汉姆雷特面对着杀父之仇的时刻, 他们所提起的是宇宙的诉讼。
这位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的伟大是写出了动物生理本能的“人性”,这在许多从莎士比亚那里发现伟大人文主义的人来说,无异是他的难以容忍的亵渎。
苏联则将莎士比亚塑造为参与现代政治论辩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者。仅从《真理报》、《星》、《戏剧》、《涅瓦》、《文学报》等的纪念文章题目也可见一斑:《乐观的人道主义》、《永远是同代人》、《永生的莎士比亚》、《爱好和平的伟大源泉》、《人的尊严》……《真理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深刻性和丰富性,特别是人道主义精神:无论是奥赛罗、苔丝狄蒙娜、罗密欧、朱丽叶,哈姆雷特,还是其他完美的创造,“都体现出这种关于人的人道主义的观念”27。《戏剧》杂志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说莎士比亚是“过去的事物”派来的参与对现在事物发言的“使者”28;他对于“将人的利益置于所有一切之上”的“我们”来说,是培育博爱精神和社会人道主义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既超越时间,也超越国界和阶级:
不论我们的人民创造着从事着什么事业,不论他在处理什么社会任务,不论苏联人考虑什么问题,不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标志着时代的变化——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一定可以找到例证、类比、讽喻、预见、联想,天才的猜测,鼓励和精神上的帮助,对一切走在人道主义和进步的道路上的人的兄弟般的支持,对一切背离人民、国家、统一、博爱、和平的道路上的人的愤怒的揭露。岁月飞逝,时光流转,社会结构在更替,战争在耳边震响……——可是人们一味在谈论钟情的罗密欧和朱丽叶。[29]
“但是”,之后是“局限性”
中国的批评家当然不能认同苏联同行的上述观点;人道主义、和平共处,博爱,人与人皆兄弟……这些从5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遭遇激烈的批判。1964的纪念活动多数搁浅,但仍有卞之琳、王佐良、赵澧、陈嘉、戴镏龄、戈宝权等的一组文章发表[30]。它们延伸着50年代确立的对外国古典文艺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探究莎士比亚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反映的阶级矛盾、社会关系,评骘表达的政治、历史、宗教、伦理观。在肯定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张扬,对中世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黑暗本质的揭露、批判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也着重指出其时代、阶级的局限。列入“局限性”和可能对社会主义时代读者产生消极作用的,有抽象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爱情至上,有模糊矛盾的阶级调和,有悲观主义的宿命论……中国当代的莎学研究者,在这方面不乏令人印象深刻且富启发性的论述。举例说,王佐良比较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同时代马洛[31]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对希腊海伦的描写,马洛的描写是:
驱使一千条楼船走上海程,
一把火烧毁了古城高塔的
就是这张脸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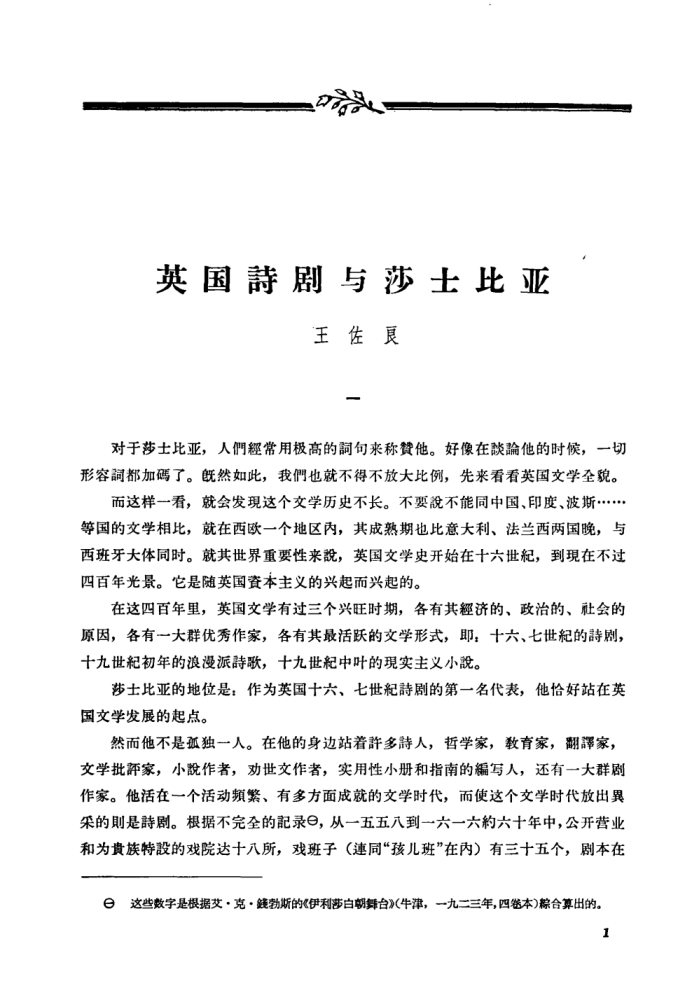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4年,第9册)是莎士比亚专辑。
王佐良,《英国诗剧和莎士比亚》,载于《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莎士比亚笔下则是 :
她是一颗明珠,
它的高价驱使一千条货船走上海程,
黄金冠的君王都成了商人!
王佐良指出,同样秉持人文主义理想,马洛充满了对古希腊文化“英雄时代”的神往,而莎士比亚却用“反英雄主义的精神”仿写这些诗句,从而“泄露”了1600年前后英国资产阶级的动向:在这些关心海外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海盗劫掠和殖民扩张的商人冒险家心目中,海伦不过是一颗“高价”的明珠——这体现了莎士比亚对哪怕是幽微的时代信息的敏感。[32]
1964年,中国莎士比亚批评仍继续走在阶级、社会分析的路上,但变化也明显。第一是莎士比亚的创作被进一步简化、“中心主题”化;批评家越来越不喜欢混杂、喧闹、矛盾,也不承认有神秘、不可知的东西。另一是对“局限性”的进一步强调、放大。面对文艺遗产或非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当代”批评说的“局限性”并非指作品一般的不足、缺点,而是指未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不能看清事物“本质”而导致的思想艺术的根本性质的缺陷;这一缺陷,由时代,阶级的难以摆脱的限制成为必然;不论他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不论他叫莎士比亚,还是叫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