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共识度·生长点·世界性——五年来的诗歌述评

诗歌从时间序列、精神向度上构成了一个国家的语言编年史和总体性意义上的时代启示录,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整体性的时代大势面前,“新时代”已然成为评价当前诗歌的一个重要历史装置,这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观照原则。
对于五年来的诗歌来说,繁多的诗歌现象以及处于变动之中的诗歌现场使得任何言之凿凿的定论都不可能是完备的,但一个显豁的事实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诗歌美学及其生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能、社会作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新诗、旧体诗词、散文诗、儿童诗以及少数民族诗歌、诗歌译介和国际化传播出现协同发展、相互学习、彼此促进的共生局面。诗歌不单是密室独语和精英意识的产物,诗人的写作身份越来越呈现出非专业化和大众化的特征,诗歌介入时代以及大众参与诗歌的程度不断增强。
诗人与新时代:内在与外部的彼此激发
“新时代”呼唤“新诗歌”,“大时代”需要“大诗人”“大作品”。“时代”是复杂的动态结构,而“新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每一个时代的最初发生或转型都亟须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而诗人正是以综合视野来整合时代命题和人类境遇的特殊群体。在大国重器、量子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流枢纽、快递服务、农村新变、数字经济、媒介革命、速度景观、产业转型背景下,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话题、新现象以及新素材,这都对诗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新的时代发展使得诗人的社会身份、现实经验以及创作主题、写作方向都要予以调校、更新。
新时代诗歌首先需要强化共识、加强引领。在中宣部指导下,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又适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5周年之际,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于2019年10月28日至29日在京召开。这是进入新时代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诗歌座谈会,也是新时期以来规模最大的诗歌座谈会。全国诗歌座谈会旨在回顾和梳理百年新诗,总结新中国70年来诗歌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厘清和回应相关热点问题,明确新时代诗歌发展的坐标和方向。全国诗歌座谈会聚焦“新时代诗歌”的五个议题:“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和主体性”“新时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抒写”“新时代诗歌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新时代语境下的长诗现象与总体性写作”“新时代诗歌的大众传播、对外交流与译介互动”。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意义重大的一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辐射全球而中国人民共克时艰的一年。众多诗人抒写时代之变,并通过历史、现实和未来融合的总体性视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语境下关注时代趋势、社会主潮、现实题材的诗歌大量涌现,尤其是“抗疫诗歌”“扶贫诗歌”“新工业诗歌”“新时代诗歌”成为主导性的写作潮流。《诗刊》与中国诗歌网推出“战斗在抗疫一线的诗人”“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歌咏新中国”“建党百年诗歌”“新时代诗歌”“新工业诗歌”等专辑以及“走向小康诗歌轻骑兵”创作实践活动。其中王单单结合了“抗疫”“扶贫”双重视角的主题组诗以及诗集《花鹿坪手记》受到业界广泛认可,“更为厚重、集中、强烈,更能给人一种知性的启迪与情感的冲击。毫无疑问,这部诗集不只表明王单单诗歌创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当下诗坛而言,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建设性意义”(吴思敬《花鹿坪手记·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作协推出“百年路·新征程”诗歌创作工程,《诗刊》以“庆祝建党百年专号”的形式推出其中的代表作品。在新工业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产业工人以及代表性的诗歌作品,丰富而崭新的时代经验以及精神质素亟须从评论、出版和传播的各个领域予以观照和总结,为此,中国工人出版社在2021年推出诗选《先锋:百年工人诗歌》。

2020年是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世界的一年,也同时改变了诗人和作家的世界观、写作观。吉狄马加的长诗《裂开的星球——献给人类和所有的生命》不仅对人类灾难予以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剖析与反思,而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回应了世界命题,“这首诗是一个关于我们的地球母亲和人类以及世界未知的命运的伟大而动人的故事。它仿佛一条丰沛宽阔的河流,自诗人的心脏和灵魂中喷涌而出。”([塞尔维亚]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期的诗人都必须接受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挑战,而疫情时期或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的正是具有人类总体意识的整体性、方向性写作。总体来看,“抗疫诗歌”在个人与疫情、诗学和社会学的深度对话中重新激活了及物能力以及现实精神。这是诗人和生活在现实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化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精神共时体。这最终达成的正是诗人之“真”和诗歌之“真”,也即所谓的“诗性正义”。
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对等关系和直线型地呈现,而是要更为复杂。我们要审视“新主题”“新题材”“新伦理”“新道德”的决定论倾向,历史已经证明,二元对立的思维是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复杂要求的。写作者不能为题材为主题写作,更不能唯题材、唯主题写作,而应该在社会景观的嬗变和时代的多棱镜中,回到诗歌的内部机制和个体主体性、诗歌本体性的根基上来,时代和现实必须内化于精神、思想、语言和诗性。
历史化经典与当代文本的共识度、增长点
评价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诗歌,必须放置在“历史”“当代”和“同时代人”的综合认知装置之中。关于新诗百年的总结在2017年和2018年成为增生点和讨论热点,比如《诗刊》社编选的《中国新诗百年志》(作品2卷、理论2卷),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从诗歌史叙事的角度来看,谢冕耗费十年心血撰写的《中国新诗史略》,谢冕、吴思敬主编的《中国新诗百年纪念文集》(2卷),谢冕总主编的《中国新诗总论》(6卷本)从诗歌理论与批评的角度总结和展示了百年新诗的成就,对新诗经典化焦虑症也予以了缓解。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诗刊》《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等诗歌类专业期刊推出“新时代”“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诗选”“新时代诗歌座谈会”“新时代诗歌十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歌吟新时代,抒写新安徽”“朦胧诗以来:中国现代诗精选”“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燕赵大地”等专栏,涉及新诗体制、诗歌场域、文化背景、选本文化、传统资源、整体生态以及诗歌史叙事,还涉及对一百年现代转型期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评估。2018年是穆旦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机构主持了相关的研讨和纪念活动,其中谈论最多的是现代性、中国性、译介、本土经验和原创力等诗学问题。
较之已经固化和经典化的古诗词的评价体系,现代诗的标准和评价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系统和不稳定的动态结构。目前现代诗的体式和形式非常多元和复杂,这对于读者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正是这种体式的多样、复杂和不稳定性使得评价标准一直缺乏最大化的共识。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2014—2017)的成功评选(获奖者为汤养宗、杜涯、胡弦、陈先发、张执浩)为进一步确立诗歌的标准、建构典范意义上的诗歌文本、推动优秀诗歌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奖授予冯娜、马占祥、满全、扎西才让、张远伦。“70后”和“80后”已经成为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诗歌也打破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少数民族诗歌的印象,呈现出更为开阔和独特的生命意识、存在景观以及新时代视域下族裔的新的生活状态和地方文化景深。通过阅读发表在《民族文学》《诗刊》《西部》《西藏文学》《回族文学》《满族文学》《民族文汇》《青海湖》《朔方》《滇池》《草原》《广西文学》《边疆文学》《金银滩文学》《白唇鹿》《章恰尔》《康巴文学》《香格里拉》《贡嘎山》《通天河》《玉树文艺》《格桑花》《长白山》《佛顶山》等刊物上的诗作以及《许你一世格桑花开——雪域高原21人诗选》《中国少数民族诗人诗选2018-2019卷》《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至2017年已经出版40卷)《藏族青年优秀诗人作品集》(10卷)《中国彝族当代母语诗歌大系》(收录310位彝族诗人作品)《游动的群山(诗歌卷)》等选本,很多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还是在语言方式、修辞策略、抒写特征以及想象空间上都对生存、生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体现出敬畏态度和探询姿态。这种本源性质的精神象征和相应的语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向民族、传统和母语致敬和持守的意味。综合来看,五年来的少数民族诗人的“民族之诗”“地方之诗”以及“日常之诗”“现实之诗”因为个体境遇的差异而充满了诸多可能的空间。
现代诗需要通过优秀文本来建立评价标准的共识度。“青春诗会”是中国作协《诗刊》社的知名品牌,自诞生至今发掘了一大批优秀诗人,推动了中国青年诗人的成长。2020年是“青春诗会”创办40周年,为了总结这一光荣的诗歌历史,《诗刊》社编选了《致青春:“青春诗会”40年》(8卷)和《青春回眸诗歌大系》(5卷)。每年的十几种诗歌排行榜和年度选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传播优秀诗歌的作用,但是也进一步扩大了诗歌美学的差异性。“青春诗会诗丛”、“中国好诗”、“中国桂冠诗丛”、“东大陆青年诗丛”、“无见地”青年诗人诗选、“六诗丛”、“漂移丛书”以及《天天诗历》《阳光打在地上——北大当代诗选1978—2018》《有声诗歌三百首》《中国当代诗选》《20世纪中国百名诗人作品集》《中国先锋诗歌:“北回归线”三十年》《一首诗的诞生》《新世纪诗典》《山湖集》《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2007—2017中国诗歌版图》《中国乡村诗选编》等试图从不同角度呈现和总结当下整体的诗歌创作。以“90后”“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诗人写作群体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青年诗人已然成为文坛的新的持续增长点,也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认知装置。这既与其整体性的写作面貌有关,又离不开各种平台的大力推介,比如《我听见了时间——崛起的中国90后诗人》(上下卷)《中国首部90后诗选》《中国90后诗选》《贵州90后诗选》《中国大学生诗歌年选》等相关诗选以及《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和“新时代与90后诗歌”研讨会、《星星》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以及《中国诗歌》的“新发现”诗歌夏令营等。
长诗创作与写作的总体性视野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诗歌正在走向成熟,而我们亟须有效的“时代之诗”和“总体之诗”,亟须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提下“我”和“我们”的灵魂式对话和叩访。因而,长诗创作成为五年来诗歌发展的持续增长点。
在碎片化的时代,写作越来越成为个体的行为,诗歌也越来越成为窄化的自我遣兴和自闭的修辞练习,诗人不再是大火中的淬炼者,不再是引领时代精神的灯塔和风向标。这时最需要的正是总体性诗人。长诗可以作为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综合性指标,也最能考察诗人全面的写作能力,这是对语言、智性、精神体量、思想能力、想象力、感受力、判断力甚至包括体力、耐力、心力在内的一种最彻底、最全面的考验。从一个更长时效的阅读时期来看,长诗与总体性诗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二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难度以及长久影响力上都最具代表性。
五年来的长诗创作颇为壮观,体现了诗人向总体性写作努力的丰富实践,比如《裂开的星球》《迟到的挽歌》《大河——献给黄河》(吉狄马加)、《伟大的思想实验》(张学梦)、《黄土岭》《金山岭》《上甘岭》(刘立云)、《化念山中》《松鹤图》《修灯》(雷平阳)、《埃及行星》《庚子祭》《宿墨与量子男孩》(欧阳江河)、《蝴蝶》《沉香》(胡弦)、《莫斯科札记》《大象十章》(于坚)、《窗口》(陈灿)、《卡尔·马克思》(舒洁)、《山海间》(陈人杰)、《周庄传》(谷禾)、《钓鱼城》(赵晓梦)、《关于李白》(姚辉)、《沙滩上》(蒋浩)、《大河简史》(田君)、《序曲》(陈东东)、《在飞机上俯瞰花鹿坪》(王单单)、《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刘笑伟)、《玫瑰庄园》(郑小琼)、《敦煌纪》(叶舟)、《德清散章》(沈苇)、《黄河诗篇》(曹宇翔)、《大江》(龚学敏)、《长江九章》(王自亮)等。
其中,吉狄马加的《裂开的星球》已被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俄、葡萄牙、瑞典、匈牙利、罗马尼亚等17种文字,多个国家出版了单行本或在重要的文学刊物上第一时间推出,在国内17种文字的合集也已正式出版。刘立云的“战争三部曲”《黄土岭》《金山岭》《上甘岭》是“历史之诗”,也是历史时间和生命时间以及求真意志同时降临与相遇的过程,它们激活和碰撞出来的场景以及词语本身更具有长效的生命力和活力。这是立足于个人但又最终超越了个人的对过往以及未来的彼此对视,是“英雄史诗”和“命运交响曲”。张学梦的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则凸显了诗人对新时代的深入思考,体现了诗人对时代命题和人的命题的双重回应,揭示了诗人极其敏感和准确的对时代场域的总体发现能力。欧阳江河的长诗《庚子记》让我们看到了诗人的精神能力和思想载力以及面对人类灾难的语言焦虑和阵痛体验。
为总结长诗写作,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专门举办“新时代新史诗与长诗创作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在史诗式微的时代诗人的总体感知至为重要。《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1期刊发关于当代长诗创作及文体的对谈《“当代”长诗:现象、幻觉、可能性及危机》。《汉诗》2019年第1-3卷分三期连载长诗研究专论《从“世界的血”到“私人笔记”——我的长诗阅读札记》。近年来,向杜甫致敬的中国诗人以及相应的诗歌和文论越来越多,这体现了“传统”和“现实”的双重回声。《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5、6期推出长篇对话《“我们的杜甫”:同时代人与“艺术的幽灵”》,从文学中的晚年与晚期风格、同时代人与精神共时体、史传传统与无边的现实主义、世界文学和跨文化语境中的杜甫正典以及涵括万象的终极诗人等五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杜甫的当代意义。韩作荣的《李白传》、师力斌的《杜甫与新诗》则从传统与当代对话的角度,对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和整体反思。实际上,杜甫的诗歌写作也拓展了我们当代人对诗歌、现实和时代的多元理解,“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写作,现在诗歌变成一个小玩意儿了,这是让我很悲哀的。大国写作从来不是举国体制的问题,但绝对不是小语种小国家的写作,不是小格局,大国写作是写作中的宇宙意识,千古意识,事关文明形态”(欧阳江河《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
新媒介传播矩阵、电子化生产、人工智能
五年来,诗歌的活动化、传播的日常化、公众化和电子化诗集出版的多元渠道以及体量庞大的创作人口和诗歌产量成为令人关注的增长点。五年来,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译介)的纸质诗集在4500种左右,此外还有1000多种诗歌内部刊物和交流资料。截至2019年12月23日,诗歌类微信公众号的订阅用户已超过1000万,古诗词的社团组织2000多个,从事古体诗词的写作人数高达350万人。
新媒介的参与和各种电子化的诗歌平台使得诗歌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诗歌升温”“诗歌回暖”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话题。诗歌与日常生活、公共空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诗歌文体的融合还是诗歌的跨界传播,其跨学科、跨文体的对话能力是前所未有而又有目共睹的。诗歌越来越呈现出与新媒体和技术紧密互动的发展趋势,因此诗歌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整体生态都发生了变化,诗歌越来越突出了即时性、视觉化和影音化的特征,尤其是诗歌的云直播、短视频使得大众化的参与程度进一步提升。
传播介质的改变和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使诗歌的传播形式相应发生了变革,形成了“刊+网+微信公号+诗人自媒体+短视频+云直播”的立体生态链和传播矩阵。中国诗歌网微信公众号的订阅范围已经覆盖了全球137个国家和地区。《诗刊》社与央视电影频道、“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联合主办的融媒体全网直播“青春诗会”一经播出就登上微博热搜,浏览量过亿。为推动诗歌出版与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中国诗歌网积极打造中国电子诗集数据库,丰富和拓展诗歌的数字出版和阅读。《诗刊》社与央视电影频道、学习强国等媒体合作推出“青春诗会——春天里的中国”融媒体直播,节目总观看量高达2.25亿次,7次登上微博热搜。2021年,《诗刊》社与快手短视频平台合作,推出“快来读诗,一起读《诗刊》”的诗歌朗诵活动,除了诗人之外,很多行业的诗歌爱好者参与其中,目前已推出2500多个视频,播放量超过1.5亿次。
诗歌已进入“微民写作”和“二维码时代”。在碎片化、电子化和APP移动临屏阅读语境下即时、交互性的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多媒体、自媒体平台下的诗歌在提供了写作热潮、热点话题的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其现实境遇和可能性前景。媒介即认识论,媒体即世界观。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平台、移动自媒体的沉浸式传播,使得诗人的创作心态、诗歌样态、生产方式、传播机制以及诗歌秩序、文体边界都发生变化。传播介质的改变和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以及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减弱了对好诗人、好作品遮蔽的几率,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和负面影响。比如,快餐式的浅阅读和及时性、新闻化、表层化的创作倾向,使得诗歌标准驳杂不清。大量的庸诗、伪劣诗歌泛滥,诗歌的传播、甄别以及评价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都需要各方面通过合力和有效的手段加强监管和引导,突出主流媒体、重要诗歌刊物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新媒体的引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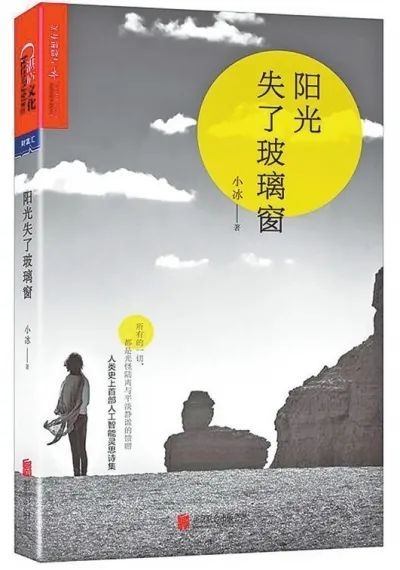
与此同时,具有惊奇效果的科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逻辑正在改变人与环境、人与人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固有关系,甚至技术革命已然成为新世界的主导精神和宏大叙事。2018年,欧阳江河的长诗《宿墨与量子男孩》处理的是近乎抽象的“科学”命题,而诗人对此完成精神对位并不断深入探问的过程体现了一个当下诗人介入现实的能力以及对未来时间和可能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人工智能跟诗歌的互动是最直接的,机器人读诗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写作成为热点,当写诗机器人“小冰”“小封”出现并先后推出各自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2017)、《万物都相爱》(2019),当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研发出小明、小南、小柯以及清华大学研制的薇薇、九歌等写作机器人批量出现的时候,甚至谷臻小简这样的评诗机器人也已登场。尽管人工智能写诗还不太让人满意,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人工智能”写作就是“次要问题”,因为它已然是人类文学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已然成为人类文化变迁的一部分。既然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那么人工智能写作就是这一特殊语言方式的必然组成部分。
国际视野、译介文化与“世界诗歌”
诗歌的开放性必然体现在诗歌的跨语际、跨区域、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出版机构和长效出版计划、译介项目对诗歌译介和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加之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参与,中国诗人较之以往已然获得了更多的世界视野和发言机会,诗歌也被提升到民族寓言、种族触角和语种文化的层面。这是以诗歌为基点而辐射到文化、政治和国家形象的“走出去”和“走进来”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多元对话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中国诗歌译介及其影响和效果史有关,还与中国对所谓的世界文学体系的想象、参与、反应和评估有关。
新诗如何能够达成个人性、本土性、汉语性和世界性的融合,显然还将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译介的现代性”或“转译的现代性”是我们谈论中国诗歌的必备话题,而诗歌译介确实对中国新诗的历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年来的诗歌译介和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诗歌经典在外国的译介,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以及少数民族诗歌在国外的翻译,新的翻译模式比如“合作自译”现象,百年视野下的诗歌对外翻译,对译介的媒介、途径、渠道和形式的讨论,海外汉学家译介中国诗歌的情况,翻译的现状、生态、新变以及出版市场,自译和“以译代作”现象,翻译的技巧、语言问题和文化问题,民族文学、文学传统、抗译性和交流性问题,译介的多层次以及重心的转移,“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背景下的诗歌翻译工程对塑造中国的海外形象以及建构本土化文学体系的作用等等。
目前来看,“从国外译入”和“向外语译出”在中国诗歌这里是不对等的,占明显优势的仍是前者。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就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以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蓝色东欧、“诗歌与人”、雅歌译丛、雅众文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磨铁诗歌译丛、俄尔甫斯诗译丛、荷马奖章桂冠诗人译丛、小众书坊、红狐丛书、镜中丛书、当代译丛、诗苑译林、浦睿文化、桂冠文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墨西哥、哥伦比亚、罗马尼亚、圣卢西亚、巴西、智利、日本、印度、韩国、葡萄牙、秘鲁、黑山共和国等更多的国家拓展。此外,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论坛、中国诗歌网的“汉诗英译”“译典”栏目、2020年海洋诗会暨第五届“一带一路”背景下当代诗歌研讨会、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第四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峰会,都聚焦于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传播和译介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题。
结 语
任何一个时代都在严格地筛选着诗人,诗人也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精神生活和想象性的世界。五年来,人们对新诗的热望、肯定与批评、不满同时存在,而诗人也应该躬身自省、砥砺前行。无论诗歌是作为一种个人的遣兴或纯诗层面的修辞练习,还是做一个时代的介入者和思想载力的承担者,一个好诗人必须具备语言能力和思想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新时代需要新的传统和个人才能。人们往往更为关注的是外部的活动、生产、传播、影响,更多是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在评价当下的诗歌,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平心而论,抗疫、扶贫、新工业、新时代等聚焦社会热点的主题性诗歌是难度更高的写作,甚至随着人们阅读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诗歌的审美期待也越来越高。其中不乏优秀的直抵现实、直击灵魂的作品,但是也存在大量的同质化的表浅文本。诗人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既是“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时代启示录、精神共时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