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范藻:超越历史后呈现的诗意——重读纪实文学《国共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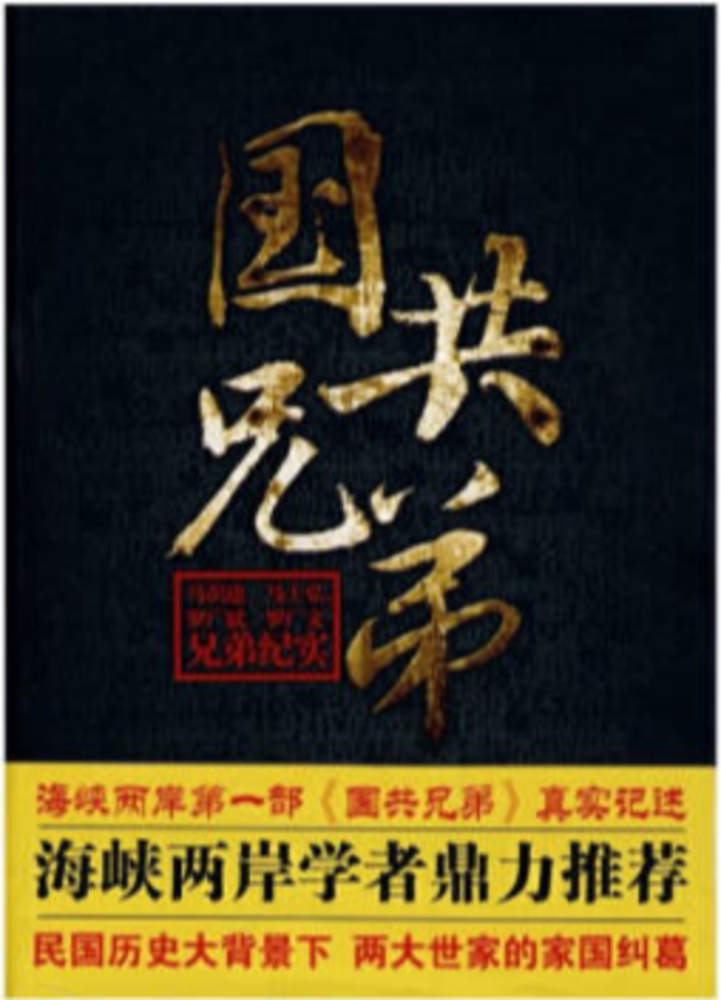
文/范藻
这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割不断中华民族的骨肉亲情;
这是一次漫漫的旅程,走不尽华夏历史的青铜时代;
这是一怀浓浓的乡愁,抹不去故国山川的桑梓痕迹。
2010年,成都作家谢天开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30万字的纪实小说《国共兄弟》。光阴荏苒,时光流连,再次捧读,感慨万千。
不必说其中蕴含的超越历史恩怨“化干戈为玉帛”的人文意识,不必说其中饱含的回归人伦亲情“血毕竟浓于水”的美学情怀,也不必说其中包含的根系乡土中国“故乡美家乡亲”的桑梓情义,仅就这部纪实小说超越历史后呈现的诗意,就是一次跨越海峡的亲情之旅、穿越时空的返乡之行和超越恩仇的审美之意。正如小说“楔子”开篇写的那样:
在对这段历史岁月的另一种访写中,深入回顾这对国共兄弟的家国情仇,细述人世间最复杂、最细腻、最柔软的情感经历,就会蓦然发现两对国共兄弟,无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硝烟中,还是在生与死的政治漩涡里,或者于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间,总有不能割舍的血缘、乡缘、学缘和业缘,让他们兄弟之间始终保持情分,明里暗中出手相援、两个家族世代交好。
那就让我们随着书页的缓缓翻动,静静地感受悄然而起的氤氲诗意。
一、在风起云涌的大视野下塑造人物
传统性的小说或虚构类小说要么围绕中心人物的命运或主要事件的变化,为了讲究情节的起承转合,或巧设悬念而悬疑不断,或异峰突起而峰回路转,或意识流动而信马由缰,表现出注重情节而淡化结构的特点。而谢天开的《国共兄弟》由于是写实性小说则刚好相反。一般而言,纪实小说是依据真实的历史事件通过艺术加工敷衍而成的,于是人物和事件互为依托,事件与人物相得益彰,因人生事,因事出人,而为了便于塑造人物,则必须选择典型性的事件。人物与事件的不可分离而又同等重要,就成了纪实性小说的重要特征。
《国共兄弟》是以老四川现为重庆市下辖忠县的马氏和罗氏两家的两个兄弟,分属国共两方,即马家的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和他的哥哥国军少将马士弘,罗家的“红岩志士”著名作家罗广斌和他的哥哥国军中将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里面的人物均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大咖,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马识途和起义将领罗广文,更不用说与此直接关联的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和蒋介石、陈诚、胡宗南等。事件则是关乎抗战陪都重庆危亡的鄂西会战、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解放战争大陆最后一战的成都战役等重要史实。
如何将这纵贯50余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遭遇构织成跌宕起伏和精彩纷呈的文学叙事文本,即从1938年武汉会战到2009年马士弘和罗广文的老上级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发表在《中国时报》上的《和平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期待》,横跨整个大陆的西南重庆到东北沈阳、西北延安到东南南京直到台湾等,几乎整个中国版图发生的国共携手抗战、后来兵戎相见到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这足以考验并检视作者的文学叙事才能,而作者却跳出了常见的“事件—人物”交织的叙事构架,采取的是以时间流程的“国共恩怨”为经线、以空间位移的“国共交锋”为纬线,既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现场,也不是单纯地表现国共交往,更不是机械地表达时代理念,而是紧紧地扣住小说艺术塑造人物的核心价值;也即是这部作品建立的“时空坐标”,不仅仅是为了“讲故事”,而是着眼于“写人物”,坐标原点或结构核心是“国共兄弟”的人生经历的生老病死、时代造成的悲欢离合和个人体验的酸甜苦辣,更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里和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建立的真善美信,并将这些转换为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和灼灼生辉的性格魅力。
小说一开场的“篇一”,就让罗广文和马识途这对“国共兄弟”偶遇在1938年3月的武汉。志满意得的国军少将罗广文慷慨宴请清贫坚韧的地下党员马识途,觥筹交错,乡情浓浓,看似热闹,实则貌合神离。正如小说写的:
“虽说是同乡,却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他们两人实际上已经分手了。人生岔道,沉浮之间:一为国民党年轻有为的高级军官,一为刚入党不久的青年大学生。”
罗广文的正直侠义跃然纸上,马识途的坚毅谨慎溢于言表。
世事沧桑,人事难料,11年后1950年1月的成都,马识途身为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委员,罗广文则是刚刚起义的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官,他们再次见面,在小说“篇三十一”写道:
“‘罗大哥,我们又见面了!’马识途的言语低沉却相当有力。罗广文目光有些迷茫,没有说话,只是有点尴尬又有所翘首地迎接住对方的手,一时无法确定相互间的恩怨情仇。”
乡情浓郁,感觉迥别,难以掩饰马识途的满腔热情和罗广文的一丝惭愧。
二、于多样手法的蒙太奇中营造效果
如前所述纪实小说主要是要突出事与人的交集和纠葛,事件则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人物则传奇非凡和形象生动,要么是围绕一个重大事件来刻画人物形象,要么是围绕一个非凡人物来展示事件经过。如果要体现必要的艺术性,往往都是在故事情节的构织上讲究悬念和突转,在外在氛围的营造上描写生动和传神,在人物心理的刻画上注重准确和细腻,在细节的挖掘上讲求个性和特色。一言以蔽之曰,就是在真实的事件记叙和人物呈现“纪实性”的基础上辅之以或加之以小说文体的“艺术性”。
而《国共兄弟》不仅体现了一般性纪实小说的“艺术性”,而且由于这个题材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特殊性和政治含义的敏感性,它既没有记录贯穿始终的核心事件,而是以20世纪后半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大背景下的,诸如宜昌的石牌保卫战、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较量、成都的解放等;也没有塑造举足轻重的一个中心人物,而是围绕忠县的马罗二家的两个兄弟、四个男人中既有共产党如马识途那样的“地下尖兵”、罗广斌那样的“红岩志士”,也有国民党如罗广文那样的“兵团司令”、马士弘那样的“起义将领”,而如何将这多样交织的事件和类型各异的人物熔铸于一个叙事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排兵布阵”的艺术。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谢天开并没有沿着这条习惯的路走下去,而是另辟蹊径地化用蒙太奇的手法,使得整部作品随时都呈现出诗情画意的美妙。所谓“蒙太奇”本是建筑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建筑构建和板块的拼接与组合,转用到影视艺术后成了镜头和画面之间的“剪接”艺术,而谢天开创意般将记叙、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的几种表达手法交替使用熔于一炉而产生出诗情画意的蒙太奇效果。
如“篇九”的“1.榜上有名”:
中州中学,一座有两扇朱红色、圆帽大钉密布的校门,颇具学宫风格的忠县县立中学。你若伫立于此,那滚滚的长江东逝水的壮观情景没遮没拦地奔来眼底,浩然长虹自胸中气贯……
罗广文、马识途和马士弘三人都是从这里跨出初中校门的。
为了还原这段岁月,2007年隆冬1月,笔者曾独自夜访忠县中州中学。
那天晚上,忽然一阵扑腾喧闹,学生们的晚自习开始散了。
同样的起点,同样的母校,共同的出发地,却分道扬镳了,尽管今天早已物是人非。
在“篇三十”“5.三个日子”一节,迎接成都解放的那一天,作者心潮澎湃,激情难抑。
走进黎明的阳光,红日照遍了东方。
心快要跳出来了,真想大喊:“我们回来了!”
真是天意!成都冬季通常是阴冷雾蒙蒙的,说来也怪,自解放大军进入川西平原后,却一直是晴朗天气,身上穿的棉军衣晒得暖烘烘的。
即景抒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写事寄理,寓理于事,事理合一。是的,马识途从1938年入党,一直战斗在白区,阴风冷雨,激流险滩,时刻处于生命的危难境地,今天终于可以正大光明,更是扬眉吐气地行进在这片昨天还虎狼成群的大地上了。作者是深谙其中的艰难与艰险,如此方能表达拨开乌云见太阳的欣喜和激动、苦尽甘来的欣慰和自豪。
三、从三峡情歌的民歌风里传递意蕴
纪实小说由于是“小说”,那么艺术性的追求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关键是如何写才有“艺术性”呢?写国内战争的纪实文学知名的有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王东兴的《建国大业》和王树增的《长征》等,和这些纪实小说比,谢天开这部《国共兄弟》令人称奇或叫绝的地方还在于,每一篇的开始都有一首巴渝地区的“三峡情歌”。表面看,这与小说无甚关联,既与故事情节无关,也与人物塑造无由,似乎画蛇添足,为文造情。那么,如此的“文艺范”究竟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的美学创意呢?也就是作者为什么要引用“三峡情歌”这种诗化的手法达到什么样的美学效果呢?
首先是揭示地域文化涵义。小说里的马罗两家是川东忠县的望族,这里临近著名的三峡。郡邑为何名之曰“忠”?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因战国时巴国将领巴曼子及东汉巴郡太守严颜并以忠烈著称而改称为忠州,这里也是古代的巴国辖地和著名的巴文化区域,民风强悍而淳朴,百姓勇武而多情,常用原始而古朴的歌谣,尤其是男女情歌来抒情言志和叙事明理,如“篇五”,讲述了马识途与刘惠馨志同道合而情投意合结成了“红色恋人”,作者吟唱出:
妹打草鞋细细搓,一心打来送情哥。一根头发搓进取,头发套住哥的脚。
1941年,刘惠馨被国民党特务关进监狱,不久英勇就义,小说“篇十三”唱道:
太阳落土四山游,情哥来到山花头。公婆面前扯个谎,日晒罗裙忘记收。
这极具地域自然风貌和文化风情的民歌,不仅表现了爱情的忠心,而且揭示了马识途、罗广斌等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甚至还隐晦地解说了罗广文和马士弘等国军将领一度的愚忠,此之谓取譬设喻,曲文深意。
其次是稀释政治理念分歧。《国共兄弟》从题目看“国共”二字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极强的政治性,很容易使人想起1927年“4·12”两党分离以后的纷争、斗争和战争带来的眼泪和伤痛、鲜血和牺牲,尽管“国共”后面是“兄弟”,但这两对兄弟只有自然性的血缘纽带,而社会性的阶级关系让他们分属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政党,那就是共产党的马识途、罗广斌和国民党的罗广文、马士弘,并且历史上同室操戈,兄弟反目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尽管1992年两岸达成“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历史造成的误解和隔阂,更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使得两岸依然处于对立状态。那么,如何实现作者的“兄弟”企图呢?即要体现“血浓于水”中华一家的理念。作者独辟蹊径,甚至可以说是脑洞大开地想到了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地域风情的民歌、乡梓风俗的情歌。
小说的每一篇开头都有一段情义缠绵、旋律优美的“三峡情歌”,在阅读效果上引导读者建立先入为主的概念:化干戈为玉帛,帮助读者获得先入为主的感觉:情感高于理智。如“篇十”记叙了1935年作为进步学生的马识途参加了著名的“12·9”从北平到南京请愿后,在扬州被特务抓进了监狱,已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的三哥马士弘立马赶到监狱将弟弟保释出来。在讲这个故事前,作者先来了一段“三峡情歌”:
农家哥哥种庄稼,手掌处处是茧巴。选郎莫看招牌好,情妹爱的是农家。
这类光鲜亮丽的“招牌”是说得闹热吃起淡白的“主义”,而勤本务实的“茧巴”才是安身立命的“庄稼”和衣食父母的“农家”,暗示政见不同无关宏旨,而血脉相连才是根本。
最后是象征国共深层关系。在小说的作者看来,国共关系可以比之于兄弟关系,《诗经》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陶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唐代李华也说“谁无兄弟,如手如足”。回溯历史,第一次国共合作赢得了北伐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和竭力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毋庸讳言,这两个政党也曾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有过“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狠毒。
小说的开篇和结尾的“三峡情歌”就委婉曲折地道出了“国共兄弟”深层而微妙的关系。
“楔子”以马识途把罗广斌引进了革命道路和罗广文将马士弘介绍到了国军十八军的历史,唱出了这对“冤家”的生死之恋:
挨姐坐来对姐言,问姐缠得好多年?葛藤上树缠到老,石板刻字万万年,阎王勾簿才不缠。
“尾声”以马士弘晚年主持主持修撰《四川忠县石宝乡坪山坝上坝马氏家史》为由头,唱出了这对“冤家”的未了情缘:
屋檐滴水点点滴滴,相爱哪怕谣风起。劝哥莫学风中灯,一时亮来一时熄。
地域的文化,演变成文化的地域——回归地域时的文化意味;
历史的诗意,呈现为诗意的历史——超越历史后的诗意盎然。
这刚好应证美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史家海登·怀特的见解:“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对它的阐释需要修辞性的阐释。”《国共兄弟》在风起云涌的大视野下塑造人物,于多样手法的蒙太奇中营造效果,从三峡情歌的民歌风里传递意蕴,充满着浓郁的乡梓情怀,弥漫着氤氲的诗意氛围,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捧读小说,再度重温“楔子”的一段话:
这对国共兄弟,纠缠着尘世上生死悲喜;交织着家国间世态炎凉快意恩仇。
是的,往事如风,恩怨已了;尘埃落定,山河依旧。正如小说的“尾声”揭示的历史规律和发出的兴亡感慨:
一切时代潮流自文化始,又回归文化。鼓之以雷霆于惨烈,润之以风雨于欣荣,历史的跌宕,历史的悲欣。
台湾海峡一水之隔,长江流水不舍昼夜。上善若水,更是水流无声。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了孔子《论语》里的一段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真可如陶渊明的感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作者简介】
范藻.知名评论家。成都锦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美学及文艺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