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学的故乡》拍摄缘起:“我不演纪录片,你只需跟我走。”


川报观察记者 肖姗姗
一声清扬的钟鸣,广袤的草原从地平线处腾起耀眼的金光,风声呼啸时,传来阿来低沉浑厚的吟诵;他在天地间漫游,走向那道金光,直到旭日东升……今晚8点,《文学的故乡》纪录片第二集《阿来》亮相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篇恢弘壮阔的长镜头,无不令人震撼。

阿来 (肖姗姗 摄)
这一集,是导演张同道心中的一道光。
那么,于阿来而言呢?7月的午后,在同样炙热的蓉城阳光下,记者独家对话阿来,揭秘这部“最美”纪录片的诞生始末。
谈出来的合作
阿来带张同道出发
阿来不是一个乐意站在镜头前的人。近年来,有无数的纪录片向他发起过邀约,但最终接拍的不过二三。2016年,当张同道第一次找到他时,他没有答应,他让张同道先来一次,见一见。“来了之后,我和张同道谈了很久,内容很深入,他这个人是真诚的,但我更希望他的镜头同样真诚。”

谈,张同道谈了对《尘埃落定》的理解,“语言纯粹,有韵味,像诗歌一样。关于土司,阿来笔下那些深入人性的故事,让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精神得到了极其壮观的体现。”张同道告诉阿来,他年轻时在四川大学求学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还以为那些文字出自一位年长的作者,后来才知道,那时的阿来,不过40岁。除了阿来的作品,他们还谈了杜甫、苏东坡。“我们去了杜甫草堂,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古典文学方面的积累还是有的,但面对阿来,我发现我的了解太有限了。”张同道如此感叹。

阿来 (肖姗姗 摄)
说起这一段儿,阿来笑了,他说:“确实,我给张同道说,杜甫写的那1400多首诗歌,我起码一大半都背得出来。”张同道反问:“那其他那些,为什么背不了呢?”阿来答:“你以为杜甫写的每首诗都很好嗦?”两人相视一笑。
阿来认为,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就一定要围绕他的作品,“首先得理解我的作品,那样,接下来进行的一切才有价值。”这一点,文学博士张同道没有让他失望。“我们最终达成的默契就是,保证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的记录都是跟文学有关的。确定了这一点,那行,拍。”
在这之前,阿来对中国的很多纪录片持保留意见,也不是说太差,但他心里有自己的标准,“我不演纪录片!”阿来直言,关于这部记录片要拍什么,怎么拍,他和张同道都从未有过讨论。没有计划,没有台本,他从头至尾给张同道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跟我走。”张同道和他的团队,扛着设备,就跟着走了。“下一站去哪里?明天去哪里?我们要不要去那里?”张同道绝口不提,提了,阿来也未必回答。
忘却镜头的存在
《阿来》就是阿来
“感觉这是个很酷的过程啊,你在主导。”面对记者这样的感叹,阿来笑了,他说:“不是拍纪录片吗?我的生活就是那样,不是说为了拍一部纪录片,我把人给带进山里,爬一爬,带回老家,跳跳舞,不是那样的。”所以,要特别强调的是,《阿来》中,所有的行程,真真切切是阿来的日常。张同道最满意的那种状态——让文学回到现场,在阿来这里,没有摆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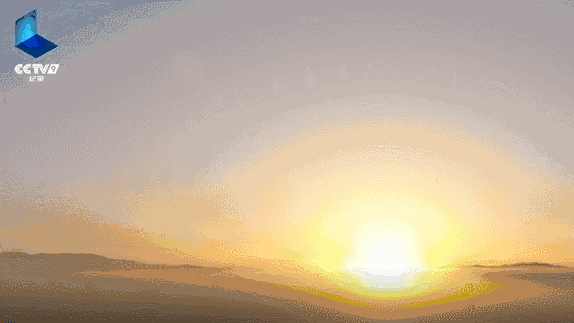
“我很多时候,都不在家里,甚至写作都是在路上,行走中的那种感触是不同的。获得启发和有写作冲动,都是在别处。回家,只是为了休整、公务,然后读书。”数十年来,阿来用双脚,更用一颗赤子之心,走过了青藏高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走过了家乡的梭磨河谷、大渡河流域、岷山深处与宽广辽远的若尔盖草原,走过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的故乡与高原圣地拉萨……“我的生活、写作,都是深入自然的。”阿来直言,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应该使自己跟这个世界有更广阔更丰富的联系,“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

阿来 (肖姗姗 摄)
纪录片中,阿来回到他少年时代极力逃离的故乡马塘,有激发最初诗歌冲动的梭磨河,改写命运的松岗水电站,青年时代调研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启迪《空山》的茂密山林,还有蕴含着文学密码的四姑娘山……一路走来,阿来根本就不把镜头放在心上,“很多时候,我都忘了张同道他们在拍,除了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拍了什么,我至今一无所知。”一路上,阿来带着自己的相机,沿途随时随地拍摄植物花卉;高兴起来,他很自然地就放声唱起了故乡的民歌,片中有几处都萦绕着他的歌声;累了,饿了,他拿出干粮席地而坐,就在路边凑合一顿;在家过年,他和母亲说着说着就落泪了……更令张同道哭笑不得的是,在四姑娘山的时候,阿来自顾自地攀爬,根本不管摄制组跟不跟得上,“我们组的年轻小伙子都累得不行,一抬头,这人不见了,赶紧把无人机飞起来,让机器拍他去。”
故乡的人真情入镜
阿来肯定这个故事讲得好
如果说,阿来的大美故乡阿坝,是自然赐予观众的礼物,那么,片中还有很多诗意的美景,则是阿来和故乡的亲人,联手制造的惊喜。阿来去到卓克基土司官寨,推开古老的寨门,院子里传来古老的锅庄舞曲,热情洋溢、身着盛装的男女老少围成圈,跳着舞。“他们并不知道有中央电视台来拍我,就是我每次回家,只要去到那里,老乡们就会组织起来欢迎我。”阿来情不自禁,与老乡们牵起手,载歌载舞。

站在一旁的张同道,被眼前的气氛感染着。他靠近阿来,说:“能不能找个藏族美女和帅哥,在二楼上去走一走?”人群中,一位高大威猛的藏族汉子立马说,“我来,我来,我是阿来老师的学生。”阿来上下打量一番,藏族汉子使劲儿介绍:“阿来老师,你当年教过我,真的。”阿来笑了笑,他其实已经想不起人家儿时的模样。之后,藏族汉子和一位藏族姑娘上楼了,又下楼了,阿来没有去过问张同道要干什么,他又自个儿上楼了,走到二楼,穿过走廊,那是他走过无数回的路,只是这次,有位藏族姑娘在凭栏远眺;他后来又下楼了,蓦然回首,发现藏族汉子站在二楼上,对他四目相对。“我很快就明白张同道是什么意思了,他就是想表达《尘埃落定》的意境嘛,比较虚幻的那种感觉。”阿来恍然大悟之后,和张同道仍然心照不宣,至今,彼此都没有就这个镜头有过交谈。

阿来 (肖姗姗 摄)
阿来始终坚持认为,文学,最重要的是讲述方式。纪录片,同理。所以,张同道的这个镜头,他虽然没看过,但内心是肯定的,“纪录片,那也是要靠镜头语言。所有的艺术,最终的目的,都是讲一个故事,我觉得,张同道应该讲出来了。”因为认同,所以开怀,在巴郎山海拔4300米的山坡上,阿来突然透露了一个秘密:一部以植物猎人为题材的小说即将开始,这次旅行他正在体验小说里的角色。那一刻,张同道的脑海徐徐展开一幅画面,于是,升华出了令观众们为之震撼的“攀登”主题——阿来不断攀越文学之山,抵达内心深处的巅峰。

阿来 (阿来供图)
《阿来》经典语录
我没有构思过《尘埃落定》,我就想起一个很好的场景,有时候就想起很好的一句话说,这样作为一个开头,我就往下写。我觉得不用刻意安排,我说我最多像一个话剧的导演都说不上,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像话剧的美工师,我搭了个舞台,这就是这个小说的空间,右边有一扇门,谁推门进来我都不知道,但是他一旦进来,就是在我给你规定好的这个空间当中,行动,说话,思想,欢乐,痛苦,一旦他们推门进来,他们就自己认识,他们就自己发生关系,他们就自己发生冲突,然后变成一台戏剧。
我对故乡,我曾经很不爱,现在有点爱。我不想美化它,我也不想丑化它,我所有的书写都想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其实故乡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投影,写故乡也是写自己。
小说就是一个探索可能性的过程,人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只能做一个选择,只有在小说里,我们可以活成各种各样的自己。
我并不认为必须回到我老家,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它才是我的故乡,当我们日渐扩大的时候,我会把故乡放大,我现在可以说,整个川西北高原,我都把它看成是我的故乡。
我觉得我对于故乡的爱,不是盲目说爱或者不爱,我按照它本来真正的面目,去认知它,书写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自己故乡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成了我的信仰。
(动图来源央视纪录)
转自腾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