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论古希腊哲学启蒙运动的现代性

本文来源:《现代哲学》 2013年第2期
转自:哲学人

由智术师在雅典民主巅峰时期开创的思想运动之所以是一场启蒙运动,就在于智术师们在此前自然哲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宗教权威,颠覆了传统礼法和道德,大力提升了人本主义的地位,以及让哲学走向市场。这场运动不仅与现代哲学极为相似,也得到了黑格尔等哲人的首肯和认同。法国当代古典学家更高度赞扬了智术师运动,认为这是一场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自我觉醒的思潮,模铸了后世哲学的方方面面。
哲学在伯里克勒斯治下的雅典民主巅峰时期经历了第一次革命性的转变(第二次转变由亚里士多德完成),这次转折改变了哲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其外在形态、表达方式、影响范围乃至根本目标。正如哲学的产生一样,哲学的这场革命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样也主要由一些“专家”——就好像泰勒斯是天文学和数学上的专业人士一样——推动,而这两场根本性的变革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在于这些“革命家”都是外邦人——后来再次推动哲学革命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外邦人!
这场革命的推动者被古希腊的同时代人称作sophist(智术师)——而这些智术师们甚至在该词已经变得臭名昭著时,亦不惮于如此自称(见柏拉图,《普罗塔戈拉》,317b4)。正如格罗特在为他们平反时愤愤不平的态度所示,这是一个极难处理的词汇,[1] 原因在于我们目前似乎还无法公正地评价这场运动,个中难处不仅仅在于古人(包括他们的同时代人)对智术师运动的评价与现代人的评价正好相反,还在于我们自己本身还处在这场运动所开启的哲学样式中,无法窥得庐山真面目。但如果我们能够对古今针锋相对的态度进行超然的观察,虽然还远远不能得出什么定论,但对于整体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尤其是“鉴古知今”的目的来说,却必定有所发明。
1、这场运动何以叫做哲学的启蒙?
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而智术师就是这场启蒙的承担者。德国哲学家往往把希腊这场理智上的革命比附为十八世纪的Aufklaerung(启蒙运动),有学者不断分辨说,这两场运动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相似性和共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差异。由智术师们开启的这场全民思想普及运动和哲学教育运动之所以被称作“哲学的启蒙”,理由有很多,[2] 撮其要者如次。
(一)智术师们在此前自然哲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宗教权威。所谓“关于神,我既不知道其存在,也不知道其不存在,更不知道他具有什么样的长相(idea)。有许多东西阻碍着我们的认识,如问题的晦涩及人生的短促”,[3] 这种说法本质上就是无神论,显然把人们从蒙昧或盲目崇拜(fetishism)中启迪了出来,让理性光辉火辣辣地照进人们的心田,它与近代的理智革命一样,当然能够被合理地称为“启蒙”(En-lighten-ment)。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罗塔戈拉据说正是因为上述大逆不道的无神论说法而被逐出雅典,他的著作也被逐一收缴,然后在广场加以焚毁。[4] 现代的启蒙运动者相比而言就幸运多了,在现代民主政体中绝无焚书驱儒之虞(可见伯里克勒斯时代所谓绝对民主其实“民主”得还很有限,远不如当今的民主)。
(二)颠覆了传统礼法和道德。智术师运动中轰轰烈烈的nomos与physis的争论,其实质就是一场旨在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刚崛起的知识分子试图以新的道德规范来取代旧的礼法秩序,尽管这个过程是智术师们独立完成的,传统宗教和礼法的进一步崩溃与智术师运动互为表里(详下)。具体地说,智术师诉诸所谓的physis(天性或自然)来反对传统的nomos(习俗或礼法),在他们看来,“法律和习惯强加于人的道德是与天性相反的,而天性的方式才是好的。”[5] 这在智术师看来,这才是进步,他们以“进化论”取代了传统的“退化论”和“循环论”。在推翻传统的努力中,相对主义也就在physis和nomos的论争中得以孕育成型。后来,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这个physis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自此“自然”成了哲学的根基。
(三)人本主义的提升。颠覆宗教权威和传统礼法道德观念,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拔高属人的一切,正如近代“上帝死了”背后的真正原因一样:杀死上帝是为了取而代之,是为了人类自身的“成长”。智术师运动时期,人们企图从国家和宗教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我”或“主体性”。这一时期的哲学可以大略地归结为经验主义、实证主义(positivism)、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人文主义(humanism)。[6] 哲学不再讨论外在宇宙的生灭变化,转而关注个体内在的幸福,而为了更好地探究自身的地位,“批判的推理的思想就兴起了,使集体的意见受到一种考察,而代之以个人偶然的学说,或代之以一种自命为有必然性及普遍性的概念的组合。因此,人就代替了自然而变成思辨的中心。在各方面,一种‘人本主义’(就这一名词所能包含的最广意义而言)就继承了早期哲学的‘自然主义’。”[7]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与人相关的学科由此产生,如社会学、心理学,尤其是人类学——西人把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阶段称作“人类学时期”。
(四)哲学的市场化。希波战争让希腊人的能量释放到了极致,希腊民族精神生活得以统一,希腊文化随之高度繁荣,“哲学从研究团体走向了市场”,[8] 在这场哲学市场化、通俗化和庸俗化的运动中,智术师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没有能创造独立而新颖的理论,他们只能将原有哲学通俗化和市场化。据说,普罗塔戈拉这位最重要的智术师出身于“搬运工”(拉尔修9.53),这本身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场运动的本质。在此之前,哲学具有秘教的性质,只在小范围内秘密传播。但智术师们为了糊口,便把这些隐秘的高深学问出卖了:“一切本来属于个人的能力以及学派中秘传的方法,现在都已经公之于世,而变成可以分科传授的学问了。”[9] 智术师为了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一席之地而把哲学这种“隐微的交流”(esoteric associations)公诸于众,[10] 这就是典型的“启蒙”,但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其是祸是福,誉之者或曰“哲学普及”,毁之者以为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瓶。
(五)哲学走向“纯粹”。这个时期的哲学开始出现形式化的趋势,内容已不再重要,形式变得更为要紧,或者用拉尔修的话说,智术师“将思想本身抛在了一边,看重的只是言辞上的取胜。”[11] 换言之,智术师看重的只是形式上完美,逻辑上的无懈可击以及语词指称上的圆满周密——不难理解,二十世纪引以为傲的语言哲学、逻辑哲学和美学正是在“启蒙”对形式上的“纯粹性”追求中得以奠基,其最初的源头就在于智术师运动的纯粹化和形式化,“这种专门技术的发展,就把方法和知识的形式方面的问题提到了第一位。”[12] 哲学就从目标的王国转型为方法或手段的王国,[13] 关注方法的合理胜过内容的美善,不问内在的“说什么”,而追求外在的“怎么说”。无论我们把这种纯粹化进程美化到什么程度,它越来越纯粹因而也就离本真的源头越来越远,越来越与生活无关,逐渐变成一种“空疏的形式主义”(empty formalism),[14] 却是逐渐为天才哲学家自身所醒悟到的问题:“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我们的生存问题也还根本没有触及。”[15] 自此至今,哲学越来越纯粹,却越来越空疏,也越来越异化。
2、智术师运动的现代性
古希腊这场大规模开启民智的运动之所以可以被恰当地称作“启蒙”,还在于它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甚至可以大略地说,今天的思想样式就是古希腊这场启蒙运动造就的。它离我们虽然遥远,却规定着哲学思想后来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方法。其实,我们只需要考察现代人对智术师运动的评价,然后再来比照古人的评判,就可以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就会知道我们与那些智术师究竟有着怎样的亲缘关系,也才能更准确地评价被我们拔得太高的现代思想,尤其是“启蒙运动”——尽管这种评价是以后的事情,但智术师运动会向我们展示“启蒙”的一般本质。
智术师运动在古希腊一直称得上臭名昭著,但黑格尔和格罗特却开始为智术师运动平反,到了最近几十年,甚至有学者把智术师捧上了天,的确可以让人充分感觉到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尤其会发现,我们今天其实还生活在智术师运动的余荫中,或者说,我们今天的思想形态究其实质来说,仍然是“智术师式的”。近现代学者纷纷为古希腊智术师运动平反昭雪,其深刻的缘由大概还在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吧。
黑格尔第一个从积极的方面或严格地说“科学的方面”来探讨智术师在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在他看来,智术师把一般性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对象上去,深入到一切人事关系中去,从而唤起了人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是绝对和唯一的实体”,从而发掘出“主体性”或“主观性”,而“由于正是这个概念现在出现了,所以它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并且不仅成为哲学,而且成为一切有思想的民族中任何一个人所参与和必须参与的一般教养。”[16] 正如柯费尔德清楚地看到的,黑格尔用自己的“正反合”方式把智术师运动看做是自我决定着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17] 无非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哲学观念,同时为自己的哲学百科全书奠定基础。但黑格尔没有全面肯定智术师运动,而是认识到“就形式的文化来说,智者们是属于哲学的,就他们的反思来说,他们又不属于哲学”,[18] 用柯费尔德的话说,黑格尔及其后学反而含含糊糊地肯定了古人对智术师运动的批评,即智术师至少助长了人的情欲和私人利益等等。不过,黑格尔虽然没有全面肯定智术师运动,却让人惊讶地看到智术师运动的“当代性”,他说:
我们现在的教化、启蒙运动,不但在形式方面和智者采取完全相同的立场,就是从内容方面来说,也是如此。[19]
我们该如何评价德国启蒙运动,由此便不难找到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尽管黑格尔绝对不会同意我们这样简单地比附这两场相隔两千多年的运动,并把古希腊哲人对智术师运动的批评用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一启蒙运动的结晶之上,但黑格尔自己上述评判就已经让我们有所感悟了,黑格尔毕竟是思想大家,目光如炬。的确,“黑格尔的思想对于我们接受智术师所产生影响仍然为很多学者严重地低估了”,[20] 不过,我的结论与柯费尔德恰恰相反。
英国人格罗特的翻案文章进一步印证了黑格尔的判断,尽管他是抱怨德国哲学史家用Sophistik把它打扮成一个恶魔样子,认为智术师用败坏的学说来毒害了雅典的道德品质并使之堕落,但格罗特与德国哲学史家在为智术师鸣冤叫屈甚至歌功颂德方面其实并无二致,比如泽勒尔就说,正如没有启蒙时代德国就几乎不可能有康德一样,没有智者们,希腊几乎就不可能有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哲学。[21] 在格罗特看来,柏拉图等人对智术师的批评是不真实不公平的,是恶意嫉妒的结果,而主要的智术师其实都可以算作好人和值得尊敬的人。据说,从全盘否定智术师运动到承认其历史功绩,乃是历史的进步,而且自从格罗特之后,几乎不再有人彻底否定智术师运动了。[22]
但格罗特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极力为智术师“洗冤”?同样为智术师翻案的柯费尔德指出,格罗特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派和自由思想家,“作为一个改革者和功利主义者,他十分重视对旧传统的攻击,他致力于对智者的再评价不是偶然的。”[23] 难怪格罗特的观点遭到了Stallbaum、乔伊特(Jowett)、格兰特(Grant)和格思里(Guthrie)等人的猛烈批判。这里只需要引用尼采颇为持平之论即可,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揶揄地肯定了智者们的功绩,顺便批评了格罗特:“智者们乃是希腊人: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袒护德性和正义时,他们就是犹太人了,或者,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东西了——格罗特为智者们辩护的手法是错误的:他想把智者们抬高到正直之人和道德旗帜的高度——而智者们的荣耀则在于,并没有用大话和德性招摇撞骗……”。[24] 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或“大江湖骗子”,而智术师的功绩在于他们是实在论者,也就是“真小人”:他们拥有一切强壮心灵所具有的勇气,知道自己的非德性,甚至公开承认自己对传统nomos的敌视,承认自己对青年人非道德的教导。
还有些学者换着花样为智术师运动辩护,把它视为年轻人对父母和家庭权威的反叛,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毛病”(eine Entwicklungskrankheit der Jugend),这种逆反心理或青春期的躁动来自于“年轻人的过度兴奋”(Rausch der Jugend),实际上并不是很糟糕或危险,不应该太认真对待之甚至苛责。[25] 更有甚者,有人正面评价了智术师运动的反叛和革命:他们埋葬传统社会秩序不过是为了提升更好的社会政治安排。这种美誉到了德罗米莉(J. de Romilly,1913-2010)这里,则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智术师运动与当今世界外在的关联与内在的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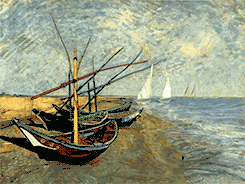
推荐关注几个公众号
哲学艺术类的
据说
可以提升一个人的
眼界和品味
哲学王 ID:zhexueking
设计与哲学 ID:PhilosophyDesign
慧田哲学 ID:zhexue-ht
哲学人 ID:philosophs
第一哲学家 ID:firstphilosopher
长按或扫码 依次关注
感受永远冷峻幽深与澄明(Lichtung)的
生命的刚强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不必等候炬火
朝向 朝向那
沉醉之路 不安之路
法国当代最伟大的古典学家德罗米莉虽然认识到智术师的弊端,比如败坏青年就是一种不可否定的“道德上的冒险”,而且也指出,城邦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智术师所带来的危险,[26] 但她却把智术师所带来的危险理解为城邦中本地学者对他们的嫉妒。但尽管柏拉图对他们横加批判,他们在柏拉图哲学的发展中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在后来的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中重新崛起,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柏拉图主义!他们的“原创性”在于第一次以人类的名义(in terms of human being)来思考这个世界,或者以人为尺度(human scale)来重新创造世界,并按照人的需要来建立世界。他们开发出了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并把两者都推到了极致,他们鼓励人们更仔细地位自己的信仰辩护,更仔细地思考那些信仰的内涵,因此,智术师的努力乃是不可估量的。[27]
在德罗米莉看来,智术师应运而生,满足了时代的需要,甚至以理性主义拯救了当时的民主!他们在很多领域开发出了新的学科,他们在教育、修辞、逻辑、语言(语法)、人性、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从自己发明的这些领域转向了政治哲学,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注入了燃料。虽然他们也有一些缺点,那就是太过卖弄、自信和夸耀,但他们是伟大的,因为“由这些思想家引入的每一种新的技艺、每一种新的学说、每一个新鲜词汇都缓慢地、有时不可察觉地改变着所有一切的感觉。”[28] 在德罗米莉眼中,智术师可谓“功超柏氏,冠盖学园,模铸至今,影响深远。”但正是他们的原创性和超愈前辈而遭人妒恨、敌视进而嘲讽,被人歪曲或边缘化(marginalized),不过他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尽管有时具有不可预料和不受欢迎的形式,但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却不可否认,因而我们“有足够的原因解释为什么这些默默无闻的人能够让二十世纪的思想如此着迷”,就因为他们的伟大贡献,试想,“如果没有他们,那些带着不倦热情、带着悲怆感、悲剧感和历史感来追随他们的人,就绝不会像那个样子。的确,我们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29] 真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我们的看法与德罗米莉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在于她是满怀赞赏和崇敬之情谈起智术师运动的当代性,而我们却遗憾地看到智术师运动的另一面,而且似乎只看到了另一面:如果现代性或当代性不是那么的令人欢欣鼓舞,那么,智术师运动就不是我们的恩人,而是相反——这是哲学思想第一次灾难性的转渡。看看这样的评价:“智术师的辩护者(以及他们的敌人)之间如果有任何共识(consensus)的话,那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异的观点‘智术师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无论把智术师说成启蒙理性主义者、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士、十九世纪末愤世嫉俗的视角主义者(cynical fin de siecle perspectivists)、分析的道德哲学家,或最新近的后现代主义者。”[30]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后现代主义不是未来发展的正路(否则后现代主义不会很快就烟消云散),那么,古希腊的智术师运动就应该为后世的思想危机承担责任,因为当今思想的智术师特质不仅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它本身就是一种已及膏肓的疾病。
古希腊的这场转渡离我们虽然遥远,并且也是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但它的必然出现以及后世不断的复活和至今愈来愈大的影响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确“去古未远”,“智术师运动”就在身边,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败坏的思想里。正如尼采所指出的:
智者派的希腊文化是从所有希腊本能中成长起来的:它属于伯里克利时代的文化,同样必然地,柏拉图并不属于伯里克利时代的文化:智者派希腊文化的先行者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古代哲学中科学家类型;它在诸如修昔底德的高度发展的文化中得到了自己的表达。
——而且,智者派希腊文化最后获得了合法性:认识理论和道德认识的每一个进步都为他们恢复了名誉……
我们今天的思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普罗塔戈拉式的……或许我们只消指出,我们今天的思想方式是普罗塔戈拉式的,因为普罗塔戈拉乃集赫拉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之大成。[31]
智术师运动当然具有“希腊性”(greekness),但由于我们的“现代性”正是智术师运动所开创或改造过的那种“希腊性”所决定的(借用时髦的学术语言来说,我们需要甄别“哪个希腊”和“谁的希腊”),因而智术师运动也就具有了“现代性”。“现代性”的方方面面都旨在为智术师运动的合法性辩护并为之恢复名誉,无非是为现代性自身的合法性和名誉摇旗呐喊,但我们从古希腊不同流派的高人那里知道,这种辩护甚至贴金其实都是徒劳——时代精神既是如此,恐怕连这种徒劳无功都不能有丝毫的感悟。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与当今何其相似,仅此一点,亦不难判别当今的精神实质。
注释:
[1]通常译作“智者”,严群先生译为“智术师”,非常贴切,“智”、“术”、“师”正是这帮人最根本的特质。
[2]参John Burnet. Greek Philosophy,Part I:Thales to Plato. 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 1928,p. 109,伯奈特举了两点:宗教和道德的颠覆者,自由思想的捍卫者。
[3]残篇4.5。见苗力田编:《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页186,译文略有改动。另参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9.51,那里的希腊文与DK本稍异。
[4]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917。
[5]安提丰语,见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刘开会、徐名驹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页131。
[6] 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该书是作者所写的六卷本希腊哲学史第三卷的第一部分。该书大量地以humanism和anthropology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思想实质。
[7]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段德智修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35。
[8]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页99。
[9]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前揭,页135。
[10]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Truth and Relativism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Lanham: Lexington Books, 1999,p. 88.
[11]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前揭,页917。
[12]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前揭,页135。
[13]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p. 90.
[14]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p. 92.
[15]维特根斯坦:《名理论》,张申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页88。
[1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卷二,页8。
[17]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8。
[1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前揭,页24。
[19]同上,页19-20。
[20] G. B. Kerfer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ophistic Studies. In his edition.The Sophists and Their Legacy. 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1981,p. 2.
[21]泽勒尔语,见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10。
[22] G. B. Kerferd (ed.). The Sophistsand Their Legacy,p. 2.
[23]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9。
[24]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1065。
[25] G. B. Kerferd (ed.). The Sophistsand Their Legacy,p. 2.
[26] J. de Romilly. The Great Sophistsin Periclean Athens. Tr. By J. Lloyd.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pp. 27,10.
[27] Ibid, p. 238.
[28] Ibid, p. 239.
[29] Ibid, p. 242.
[30] R. Barney. The Sophistic Movement. In M. L. Gill and P. Pellegrin (eds.).A Companion to Ancient Philosophy.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 78。作者在脚注中例举了Barnes、Fish和Jarratt的观点。所谓视角主义,即认为真理取决于视角。
[31]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1022-1023。着重号为原有。引文未加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