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胡学文|他们用八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都说了啥

今年1月,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掀开了牛年纯文学出版的大幕,图书出版一个多月,便横扫“年度最佳小说”月度“中国好书”等多项重要文学评选和好书榜单,很多重要的作家、评论家都对其作出点评与赞誉,并且两次加印。
3月,余华又推出最新长篇小说《文城》,小说出版旋即受到了各界的瞩目,评论报道纷至沓来,有人视其为名作《活着》之后的又一巅峰之作。
作为开年以来两部最重要的长篇纯文学作品,有非常多的巧合之处,作者创作都用了八年时间,两部作品的故事线索都是清末那几年开始,讲的又都是发生在乡村的传奇故事……
今天,让我们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细细品味他们同样精彩,但又各具巧妙之处吧。
乱世,跋涉与错过
——《文城》《有生》对读
文/张德强
对《文城》有一种评价的声音,即,它可能是好故事,但未必是好小说,我们姑且接受这说法的前一半,且将之也用在对《有生》的判断上。《文城》和《有生》都是有趣的故事,是那种可以坐在火炉边娓娓道来,让围坐者听得进去——岂止听进去,是听得入迷的故事。也许从写《活着》开始,余华醉心于认真讲故事,他在《活着》日文版后记中说,是时间创造了故事。他道出了有关故事的一半真相。还有一半,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在人们的想象中,讲故事的人就是从远方归来的人”,那么,还有远方,或曰距离,深度地参与了故事的生产,使之富于魅力。《文城》和《有生》都是在时空中延伸成长的故事。《文城》的世界,是从林祥福从北至南的远行开始的。他自黄河北岸一个小村出发,用双脚风尘仆仆地丈量土地,渡过淮河和长江,一心去江南的文城寻找出走的妻子小美,最后落脚在溪镇。《有生》的祖奶乔大梅则从南到北,自河南的虞城,跟随手艺人父亲一路向北流浪,抵达河北坝上的小村宋庄。哦,还有时间,算起来,林祥福活了四十多岁,祖奶活了一百多岁,到小说结束时还活着。两部小说的时间线索均是从清末那几年开始,远方的京城是牢固而缥缈的地理坐标,《文城》中阿强要投奔北京恭王府的亲戚,《有生》里祖奶的父亲最初北上的动机便是将大梅送到北京做宫廷鋦匠。《文城》故事大约终止在匪患横行的北伐战争结束前后,《有生》就要漫长得多,故事差不多讲到我们眼前才截止。
两部小说的作者对故事的态度均十分谦虚,绝无为形式探索而牺牲叙事流畅性之意。据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不掺杂心理分析的简洁细密的叙述风格,能更有效地使故事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本雅明语),《文城》的开头朴素而庄重,就像一则民间故事的第一句:“在溪镇有一个人,他的财产在万亩荡”。余华和胡学文更在意故事有序的推进与耿直地成长,他们描述、介绍、呈现对话,却都不在意为人物的心理活动停留太久。这是两个饱满茁壮的世界,各自分出或粗或细的枝枝叉叉,有的枝杈在叙述中为作者所回收,比如林祥福一生牵挂的小美和阿强的故事,余华要特别分出四分之一还要多的篇幅交待(这一章为评论家所深爱)。《有生》中诸多处在各章叙事核心的人物,也就是故事的讲述者们,他们的故事则到小说结束时都没有结束——继续生长无妨,也可以就此打住。两部小说在这里都显示出叙事的从容,也是其不同作者风格的体现。
《文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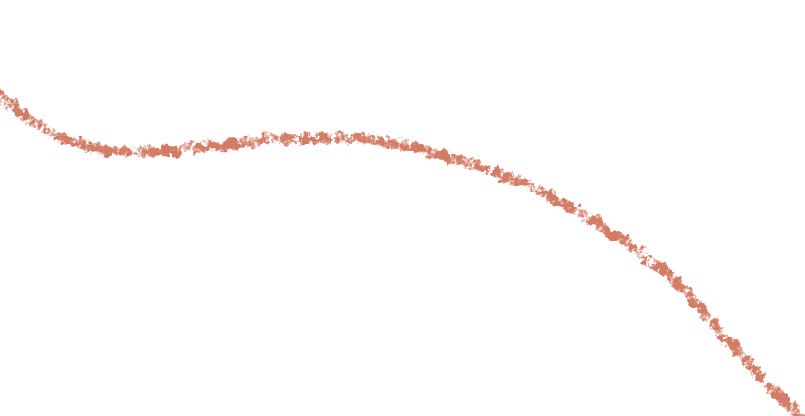
余华


《有生》
胡学文
《文城》是一个完整且封闭的世界,它在林祥福死去时已经开始收拢。既然有现代史为背景,用时间打底,《文城》的世界自然也能跟着其他尚未回收的人物走得更远,像丁帆教授的猜测,可能继续衍生出完整的三部曲。毕竟,和《活着》不一样,《文城》有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并非以林祥福为讲述者,故事的叙述也常偏离他;溪镇在地理上勾连着远方的上海乃至更远的海外。不过,既然故事从林祥福的寻觅正式说起,“文城”这个小美随口编出的地名落实于水乡溪镇,便有粗心的读者质疑,林祥福在溪镇生活了十七年,为何始终未得到关于生于斯逝于斯的小美夫妇任何蛛丝马迹?因为林祥福自己没有讲啊(除了对陈永良),少壮的他,其寻觅之旅自黄河北岸出发,开始时抱着客死他乡的觉悟。他最终在溪镇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文城”。随着岁月逝去,他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对女性真正的兴趣,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友情、财富和声望,以及责任。他算是迷失了初心吗?小美死后葬在西山的角落,“林祥福很多次来到西山,他与陈永良爬上西山俯瞰溪镇……可是他从未到过这僻静之处”。当林祥福和小美的埋葬地擦肩而过时,让人想起苏童的《园艺》,一个封闭的中产家庭,儿女为了寻找失踪的家长孔先生,一个个走到外面的世界,发生诸多故事。而孔先生,王安忆分析这则小说时说,人们不知道他一直长眠在庭院的花圃中。如果“寻找”这件事是《文城》的叙事起点的话,应该说,小说点出“错过”这一事实时,林祥福的故事就已经结束了。“文城”是个生造的地方,“找小美”这场毕生的远行便是肇始于谎言;《有生》的百年跋涉又何尝不是部分地开始于大梅父亲一个荒诞的念头,送心灵手巧的女儿去做宫廷鋦匠——宫里的碗打破了,还会鋦它吗?


余华(左)、胡学文(右)
《有生》和《文城》比起来,实在太长了。这么长的故事,这么久的历史,这么多的细节,如果全交给一个人讲,读者会疲劳,叙述者也会捉襟见肘。作者胡学文索性采用了他自称的“伞状结构”,二十章的小说以祖奶的十章故事为基座与“伞柄”,其间间杂着如花、毛根、罗包、杨一凡、喜鹊五个视点人物的故事,这种写法倒叫人想起《权力的游戏》POV的写法。和《有生》比较本分的全知叙事不同,《有生》是以十章祖奶的第一人称叙事和十章五个视点人物的POV结合起来完成的。POV,Point of View,所谓视点人物,似乎并非什么新的长篇小说写法,无非是甲一章,全讲甲的故事,乙一章,全讲乙的故事,能否用得好,则全看作者组织统筹的功夫。于是,我们看到,在祖奶的讲述中,时间在进行时中缓慢前进;而其他视点人物的故事则相互丰富着细节与全景,并串联起下一段故事。作者在努力贯彻着“多声部”的写作追求,但不得不说,这些声音因为次第到来,倒真没产生多少类似和声的效果。有些人物也活生生地在不同人物讲述中不时闪现,如乔石头的故事就是在各章节的闪回中逐渐丰满的,视点人物只是在对事情的认知上各有盲区,却绝无多少冲突。
假如我们把这两部作品放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乡土小说”或“长河小说”序列里,会发现某种现当代史观念在小说呈现上的嬗变。从张炜《古船》对乡村文化冷峻的审视,到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的黑色幽默,再到余华《活着》模糊又凿凿的时代背景,人们都不难读出某种反思历史的雄心。《文城》和《有生》似乎并无此意。前者发生在溪镇,后者发生在宋庄,故事都是在小村落四周发生,却辐射和映射着中国文明的南北;正直与善良处在故事的核心,也许未必每次都能胜利,却始终不会迷失。乱世是大背景,对秩序最切身的威胁,都是土匪。溪镇险些毁于匪患,最终却在和土匪的战争或涅槃或重生。祖奶失身于土匪,她第一个丈夫也死于土匪之手,她最后一个丈夫却是个隐藏的土匪——在新中国被发现并正法。翻翻二三十年代的《大公报》或《申报》,土匪抢掠乃至屠村的报道不算鲜见。从洗白成为枭雄的张作霖到死在抱犊崮下的孙美瑶,土匪也算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动荡的重要风景。《文城》和《有生》两部在故事时空上相映成趣的作品,除了讲述人自身的内心纠葛与人与人间的爱恨外,土匪成了表现故事矛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这当然是作家各自的选择,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选择。
图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