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随笔】“书”与“法”

邓石如、包世臣以降,碑帖之争不辍,影响至今。果真有碑帖之分吗?在印刷术的初级阶段,优秀法帖不得付梓刊印,仅靠响拓摹写传世,使得书法精神大坏,后人无法得其精髓,全赖摹刻上石,原作精神得存大略,故有碑学兴起。而其风蚀败坏之迹,亦成为后世书家追逐效法之兴味,致使古法变乱,贻害于今。今天大量的考古发现,借助媒体广为传播,简牍的出土、魏晋残纸的发现、秦汉墨迹的现世等等,似乎为我们揭开谜底。我以为“碑书”并不存在,书法就是书法,并无二置,更无所谓“碑”“帖”之分了。

一
金石味的遗风
碑碣的风化剥蚀,使得碑刻字迹,表面效果丰富多变,披上了一层历史沧桑感的外衣,为近代审美所推崇,似乎以此作为评判书法的第一要素。在批判明清馆阁体的同时,这种追逐金石斑驳的书风,在近世已形成书法的主流,康有为将其弘扬推广到极致。当今书法努力模仿石碑刀刻痕迹,线条粗俗刻板,字型乖张造作,加之日本少字派、墨象派对国人的影响,使书法已沦落为空洞的、自我表现的形式主义的产物。书法原本的人本意识、心灵脉动荡然无存。窖藏青铜器的出土,使我们看到数千年前光灿如新的器物,与我们印象中锈迹斑斑的青铜器大相径庭。器物铭文,字口清晰流畅,这才是庐山真面目。故齐白石云:“深入古人骨体,却无古人皮毛”。此乃真正的大师见地。舍本求末在皮毛上下的功夫太多,追求铜器石刻的物理性损害效果,真正的书法精神能够存在吗?金石味的追求并非书法的本质,好友萨本介兄诗云:“鼎彝堂而皇,道咸遇乖张,误从斑斑锈,学作刻舟郎”。

二
执笔法的遗失
日本人对书法重视超越了国人,上升到一种精神追求、道德理念的高度,故称书法为:“书道”。而国人从末将它推崇到如此高的境界。他们知注重的是心性的修为及人格的完善。书法仅为小道,故定意义为“法”,从字面直解就是,“书写方法”。“法”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自由其“法理”。它无外呼执笔方法、用笔、用墨、以及落笔在纸上的角度、压力、速度等问题。最紧要的仍然是执笔问题。

魏晋以前的书法理论典籍中,很少谈论技术问题。大多是论述书写状态及字面效果,因其技术层面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如同我们今天使用筷箸一般,因而未见缀述。随着后世对书法的热爱及重视,书法逐渐成为仕途进阶的手段,书法技术亦就束之高阁了。从技术角度讲仅存卫夫人“去笔头二寸”及王羲之“夺笔不脱”而已。而后来苏东坡“执笔无定法”,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均处于一种迷茫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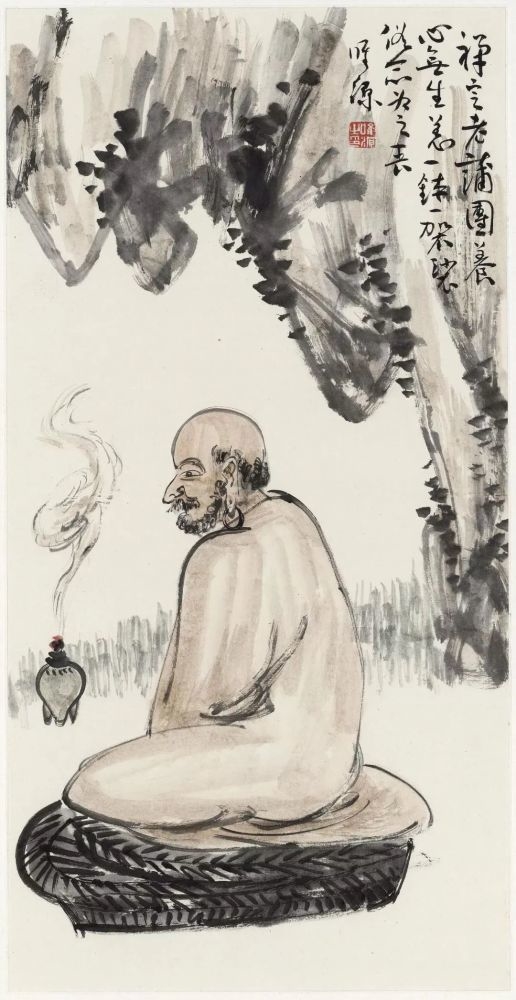
智永的“五字执笔法”是我们今天的执笔津梁,然我们以此并不能洞达魏晋古风。结论只是是执笔法误传,或注释偏差。(当然有些人会指摘“人心不古”如何以达?我个人以为这是不求上进的一种逃避推辞罢了)。执笔法如此重要吗?否则钟繇不必掘韦诞墓,寻蔡邕笔法了。逸少寿仅五十有九,大令行年四十,其书法数千年无人逾越。何故于此?非后人才情顽劣,亦非用力不勤,实笔法不传矣。今观魏晋残纸,书家多为下里巴人,然其书迹天真浪漫,不让右军,全在其时书法技术开明,点划自入法理,天趣昂然,书者心无牵挂,心性流露。推想去,我们倘亲见右军执笔,不出百日,人人自可逾乎“兰亭”。

三
功用性的遗变
书法的立轴形式出现,便成为要展示给别人看的东西,其潜台词是要给别人欣赏夸赞的东西,因之与上古书家心态从此分道扬镳。心灵上的离经叛道,也就使我们的书法艺术形成了重要的分野,即“功用书法”和“艺术书法”。

书法的蒙生,原本是一种记录功用,“石鼓猎碣”“泰山刻石”“兰亭序”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书写者以记述为目的,心系于所表述的内容。书写过程中的情绪波动,像心电图般的透过书法如实地传递出来,而形成我们看到的优秀作品。在记述的形为过程中,所产生的形式美感,逐步发展形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势。近世,书法的功用性逐步走向衰亡,而它的纯粹艺术表现得以申张,这种从功用向艺术的转形,也是使书法日薄西山的成因。

艺术强调自我,注重形式感。有意区别于人,使书法在其功用阶段时的自然抒发,沦落为做作和虚伪。追求章法的怪诞、笔法的霸悍、墨法的绘画性,使书法作品狂躁而不真实。这与功用书法中流露出的自然天成艺术美,心灵与形式相契和的包蕴着作者心灵脉冲的作品,早已南辕北辙大相近庭了。

以上这些近乎于“悲观”的阐述,并非昭示和判定书法的死亡,只是想通过客观的分析来判定我们所处的坐标,认清我们的发展方向。现阶段书法艺术的状态自有其美感及成就,同时也有着它们存在的必然成因。而我所要说明的是中国书法正脉式微,薪火不传,这亦或许是我个人的狭隘偏见所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