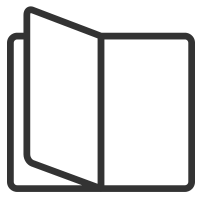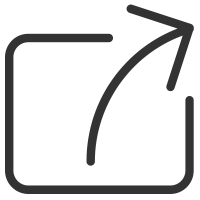写朦胧诗的海子、顾城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2021-06-22
2021-06-22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写朦胧诗的群体,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北岛、顾城、舒婷、海子、西川、江河等人。

中国朦胧诗开拓者是食指(郭路生),1968年,他写下《相信未来》。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据说,当时,全国只要有知青的地方,都有郭路生的诗歌传诵。不知道郭路生是否影响了北岛、顾城等人,可说他是开辟了一代诗风的先驱者,应该不过分。后有人评论说,其诗歌成就比北岛、顾城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北岛是将朦胧诗从地下走上地面的代表人物。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是朦胧诗公开亮相的标志。
著名的格言式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出现在这首诗里。同食指相信未来不同,北岛则是什么都不相信。“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但是我想,既然他一切不相信,“一切都是烟云”,那他在一段时间内,为什么会积极投入与社会大流格格不入的行动中?可见,当初的北岛处于找不到出路似的迷惘痛苦和激愤之中。后来,他可能想明白了: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祖国是一种乡音”,“ 是的,你不顾一切/总要踏上归程”。
他说:“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情感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

舒婷也写朦胧诗,而且写得非常成功。1977年发表的《致橡树》,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男性与女性应当是平等的”是这首诗的主题。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舒婷的胸怀比北岛、顾城他们宽阔得多。她写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深沉而热烈的爱。

接下来说顾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这句诗感动了多少文学青年。遗憾的是顾城本人却没有孜孜不倦地寻求下去,而是陷入了无法自解的苦闷空虚之中。
他写过好诗,“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很具朦胧感,意味深长。
可是他的多数诗作,依我这个外行人看来,是灰暗的。
“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一片死灰中(《感觉》”。以致他对妻子和情人的感觉,也是“使我们相恋的/是共同的痛苦/而不是狂欢。”
他说:“如果你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那就该死了。”纵然他隐居在南太平洋,那个遥远的激流岛上,想逃避这个喧嚣的世界,最后还是选择了死。令人震惊的是,1993年10月8日自杀前,他的妻子也不能幸免。

该说说海子了。
海子是后来的朦胧诗人,但他的名气丝毫不亚于上述几位。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知让多少人为他流泪。
有人说,“倾心死亡”是海子对艺术和生命的一种终极式的哲学理解,是使他的作品焕发出神性与不朽力量的原因之一。
我不以为然。海子无视“物极必反”这个哲学道理。他始终对于面前的纷呈的世界,抱着拒绝接受的态度,促使在他的诗里,表现出一股疲倦、忧伤甚至阴凉和死亡的气息。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土地-王》)。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日记》)。
“亡灵游荡的河,在过去我们有多少恐惧,只对你诉说”(《汉绯,河水》)。
他的诗自有其特点,我不敢狂评,只凭感觉,读他的诗,心里也会阴凉起来。他死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年仅25岁。有专家评说,海子之死是诗歌转折点的标志,海子死后,中国诗歌的先锋性不复存在,诗歌神性的年代结束,泛娱乐和诗歌娱乐化时代到来。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他真的以自己全部的青春生命和意志力为诗歌而牺牲吗?是真正完成中国近代诗歌改革的第一人吗?从海子最后的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也许可以找到线索:
“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海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热爱的乡村是“空虚”和“寒冷”的,他的状态何尝不是寒冷的空虚的呢!
同样有成就的朦胧诗人,同样与顾城、海子同辈或者交谊的诗人,如北岛、舒婷、西川、江河,他们经历了一段迷惘后,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顾城、海子们为什么却选择死亡呢?据说其中重要的因素是他俩都跟“情”有关。
依我看,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们的死,跟固执、幼稚、自私有关。性格上的自私,政治上的幼稚,行为上的固执,使他们看不见也不愿看见面前的祖国是什么样子的,他们陷入在空想或幻想当中,他们“想涂去一切不幸”,谁知不幸偏偏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要看看太阳”,却没去了解太阳,更不会去了解“人间”,他们只了解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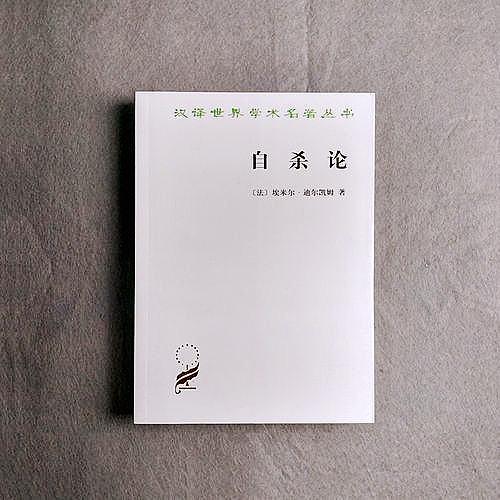
有一本外国人著的书,叫《自杀论》,作者将自杀分为四类: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 。其中关于利己型自杀的论述似乎可以回答诗人之死的主要原因。
作者說,个人主义的兴起增强了个人的独立性和利己心态,削弱了群体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降低了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松弛了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个人的自我在社会的自我面前过分的显示自己并牺牲后者的情況称之为利己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产生于过分个人主义的特殊类型自杀称之为利己主义自杀。利己主义可理解为个人主义對社会一体化的对抗。
利己主义者更多的进行思考和怀疑,他們强烈的反抗着对給定目标的遵守,他們思考价值、怀疑价值(价值是社会赋予的),并且渴望自身建立价值。这便意味着其与社会联系的松弛。利己主义者们渴望亲自建立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但他們的力量过於渺小,他們无能为力。作者說,利己主义的状态和人的本性必然矛盾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很容易陷入沮丧、绝望而难以自拔,进而采取自杀以求解脱。他們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松弛了,于是,他們与生命在一起的纽带便也松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