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遥远的视野重新走近鲁迅

作者:薛羽
1931年3月,鲁迅主动邀请一位日本青年来到家里,为其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及《呐喊》《彷徨》,每天从两点左右学习到四五点钟,一直持续了三个月。青年归国后,两人保持书信往来,师弟情谊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佳话。这位青年就是后来第一套鲁迅全集——日本改造社《大鲁迅全集》的编译者之一、著名学者增田涉。他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培养了众多后学,内中翘楚便有在大阪市立大学跟随其攻读硕士、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教授的丸尾常喜。关于鲁迅和中国,丸尾亲承乃师教诲,深受两代人的精神影响。他写有《鲁迅:“人”与“鬼”的纠葛》等专著,参与翻译日文版《鲁迅全集》,同时向大众描绘了真切可感的鲁迅肖像,也就是这本最近译介到中文世界的《明暗之间:鲁迅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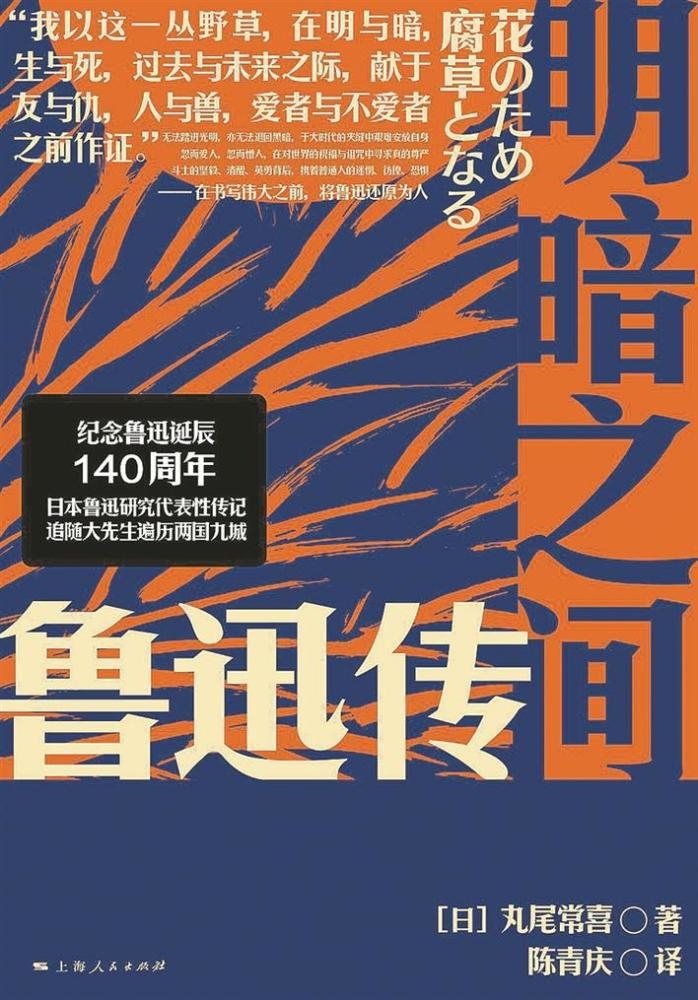
《明暗之间:鲁迅传》 [日]丸尾常喜 著 陈青庆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2021年9月版
传记的日文版收录于集英社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中国的人与思想”丛书,该系列集结了沟口雄三等中国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为孔子等12人立传,鲁迅则是当中唯一的现代中国人。其传记原副题“为了鲜花甘为腐草”,腰封称作“黑暗中寻求光明,终而不屈的灵魂记录”,均传递出写作者丸尾常喜对传主形象的基本认识。他在“序章”中更表达了自己把握鲁迅上述生存方式的立足点:“作为一个将过渡性中间物视为自身命运并加以承担的人,他是如何在仅此一回的生命中活下去的。”这句话稍嫌拗口,却提示了传记的写作关怀及线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鲁迅,如何不断面对挫败和失望,继续挣扎和反抗,呈现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学面貌和精神结构。
《明暗之间:鲁迅传》以鲁迅平生所涉地理空间为章节,勾勒出他遍历中日两国九城的生命轨迹。故乡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转而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虽说也有着接触新事物的欣喜,但更多则是现实生活的不断碾压:日本留学的苦闷屈辱,提倡新文艺的无人响应,北京公务员生涯的寂寞厌倦,大学职场的幻灭失落,再加上旧式婚姻的不幸,兄弟怡怡的破灭,重获真爱的犹疑,同侪后辈的攻击……这些百年前“小镇青年”的郁闷,“人到中年”的危机,似乎离今天的每一个普通人也不那么遥远。按照传记对鲁迅的描述,传统社会、传统文化所给予他的旧教养与感觉,现实生活使他背负的精神创伤和罪与耻的意识,进而还有他自身称为“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起伏消长”的生存方式所内含的激烈矛盾,这一切形成了他的思想,影响着他的行动,并将历史与现实把握为他独特的文学世界。他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绝望的反抗”。这是丸尾常喜从动荡大时代的背景之中,洗练裁出的鲁迅剪影。
丸尾常喜认为,他的鲁迅研究至少要超越时间与民族这两重障壁,因而依据“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方式予以接近,研究对象既是鲁迅及其文学,也是文学内外的中国。具体而言,“尽可能地将鲁迅作品所展现的事象返回到鲁迅生活的时空,加深对鲁迅作品作为前提的那些事象的历史、社会、民俗等意义的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文学与中国相”。身为外来研究者,既要了解异国的状况,又要把握文字的内涵,不得不采取上述看似笨拙的办法,从而也构成了丸尾的写作特色。此外,传记颇为注意鲁迅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以大量戏曲、科举、民俗材料为基础,读入鲁迅小说、散文中的绍兴与中国,从中读出民间“小传统”或土俗世界之于鲁迅的重要意义。丸尾略费笔墨爬梳鲁迅的房族世系、科考的制度、目连戏的因缘,深入触达传统在鲁迅心灵投下的长影。
人物传记的主体固然是个人的生活,不过丸尾充分意识到,鲁迅及其叙事已然成为中国近代经验和看待经验的方式,比如“《朝花夕拾》是一本回忆文集,是步入中年的鲁迅对自己从幼年至青年的体验所做的回顾,但该书通过一个人从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体验,生动地呈现出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变化。我们能够在个体的历史中清晰地品读出民族历史的缩影”。他还指出,“书中所描绘的往事是鲁迅在写作时整理和读取的体验,所以我们或许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鲁迅的说法”,提醒注意叙述者的姿态,也提示了不仅要以“历史的”方式,而且应以“文学的”方式来阅读和把握鲁迅。
与此同时,丸尾常喜努力对“私事”进行思想性的理解,即从中把握“看似完全个人的私事是如何与鲁迅思想上的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他重视以“耻辱”意识来勾连、凸显鲁迅早年经历、留学体验、“国民性”思考、《新青年》写作等当中对于民族陋习的批判,对于“真的人”的呼唤,对于自我“中间物”存在的把握,并由此串联起对“幻灯片事件”作为鲁迅“文学根源的原初场景”的认识,对“民族的自我批评”作为鲁迅文学特色的理解,对《狂人日记》等经典作品的解读,以及对“婚姻”“爱情”作为鲁迅生存方式和精神过程的最集中呈现。正是经由早年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各种“公事”及“私事”,鲁迅不断挣扎调整着自我,从“将生命完全寄托在自己的过渡性之上”,经历“与其内心难以抑制的‘生命的一次性’剧烈摩擦”的“彷徨”,继而“从过去的魔咒中解脱”,终于踏入一个新的战场,可以“同时实现生命的一次性与过渡性”。于是,按照丸尾的理解,“鲁迅的思想到广州时期已经基本成型”,他从“封闭的青春”走出,心情和精神逻辑已经化解了以往的矛盾与困惑,走向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与战斗。
钱理群先生在这本传记中文版的推荐语里,对中日鲁迅研究作了比较性的观察:“鲁迅是需要隔开一定的距离去看他的”,这也提示了丸尾版鲁迅传的特点和意义。当然,没有“包袱”,并不意味着没有研究立场或问题意识,毋宁说,好的研究自有其向着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提问。丸尾常喜“一直想通过鲁迅的文学来思索、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且由此在对于人的观点与对于社会、历史的理解方式诸方面也多承教泽”。这种朴素的学习姿态,能为今天重新走近鲁迅、读懂我们自身的历史提供一些启发。(薛羽)
来源:深圳特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