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的“小说课”(下)|如果没有男女关系,人类小说没必要存在了


11月13日,在浙江女作家杨怡芬的新书《离觞》的钱报读书会上,作为现场嘉宾的著名评论家、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教授,在现场娓娓道来,给杭州的读者们,上了一堂生动又深入的“小说课”。
从中国有小说伊始,就有人在读小说。当下阅读市场,长篇小说依然是阅读者喜欢的体裁。洪治纲作为小说的专家,每年都要读大量的小说作品。
杨怡芬的《离觞》,是他今年读的其中一部长篇小说。
在分享会现场,洪治纲教授的一些观点吸引住了很多喜欢小说的读者。不管是写小说的还是读小说的,都为此而沉浸其中。
小说,写的是生命,是人性,是时代,是日常生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洪治纲说,两性是永恒的一场战争,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点关系,人类小说也没必要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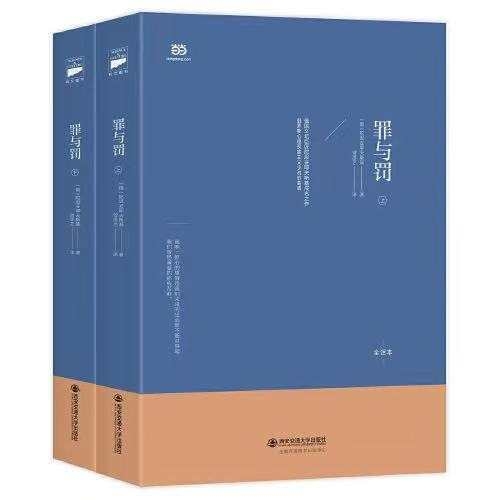
【好的小说其实好在细节】
从《离觞》的整个故事发展来说,确实是以三四个女人在时代面前面临命运裂变遇到的种种情况以及反应来展开,主角肯定是李丽云了吧?还有宋以文的妻子秦怡莲,还有一个受到新思想影响的老师叫宋安华。我注意到她们在那个时代对时尚的把控,是对标上海的。浙江海边的人,他的遥望窗口不是杭州,是上海。宁波人说我要到外面去买东西,他一定是到上海。温州人要买东西,一定也是去上海。温州有个作家叫王手,他小说写得也挺不错的,他写小说主人公出外买东西,从来不写去杭州,都是去上海。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能听懂上海话,就能听懂宁波话,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就是从近代以来,上海的商业基本上是宁波的商人在把控一样,所以才有“宁波帮”这样的说法。这里,我不去多说它了,我要说的是,如果有的人不熟悉历史,他会觉得那个时代舟山小岛上还这么时尚,扯吧?其实还真不扯。那个时代舟山就是跟上海有紧密的联系。这个小说的开头不错,杨怡芬看似没花多少力气,但能够一下把上海勾连起来,把所有的人物在第一章就放出场,这个也挺不容易的。一般作家第一次写长篇没那么好的经验。
小说展开之后,你会看到小城镇的那些时尚的东西,特别是她写的潘绮珍家里面,父母做的是一个布庄,当然小说里也有米店,有饭店,但那些我感觉都是顺带过的,布店却是从头写到尾的,这个是女性生活中最至关重要的场所。女人衣服再多也还是要嫌少了几件,就是这么一个生存状态。所以杨怡芬的日常书写选择还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讲小说的三要素里面,第二个问题是情节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小说已经不太去过度讲情节了。如果我们过度追求情节,它是会造成一种传奇性。什么是情节的传奇性?就是说一个一个事件通过外力构成传奇。比如两个人谈恋爱,然后突然第三者出现了,那么这是外力,是外在发展。或者是你们两个人恋爱了,马上要结婚了啥的,突然有一方得绝症了,这个也是外在的事件。这些事件,就像琼瑶剧的那种,它就是由种种外力构成,串起来就是情节。小说写情节相对容易,我们小时候看的《故事会》里都是情节,靠外在力量改变故事的发展走向,然后不断的用这个东西去推动。
现代小说它最注重的是细节,不太关心情节的离散。如果大家愿意去细细读读《离觞》,其实情节进展非常慢。其中李丽云和郑景润的一个情感故事,几乎看不出两人好到什么程度,不是像琼瑶式的那种感情,但是,两个人好的时候心很相通,剧烈的东西都在人物内心当中,都在细节当中。比如说,她写到那个时代的恋爱特征,包括带点心,什么样的点心,怎么样坐车,这些细节,都能够非常好的体现两个人的爱情到了哪一步。
现在,我们读小说,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读细节。对细节的要求,首先是一个真实和准确,还有,细节要有力度。对细节的把握,跟一个作家的世俗经验和写作能力有关系。因为“细节”的要求非常的多,它不是你把它写得很鲜活,想象力很丰富,或者说写得很真实、很准确就很好了。卡尔维诺说到过,“在古埃及,精确是由一种羽毛来衡量的”,也就是说,好的作家细节处理出来,要像古埃及人称人的灵魂的天平,那个天平砝码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羽毛。那么轻就都能够发现,就是说,要进入到一个文字玩味的地步了。这在我们当代就比较少了,在汪曾祺有些作品是可以看得到的。
“细节”里面,它的爆发力和想象力也很重要。《离觞》细节的处理跟杨怡芬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因为很多关键性的细节应该是可以拓展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她绕过去了。比如说,李丽云已经知道了刘仲瑞的飞机被打落了,王天锡来接她到部队去。在这里,我觉得这个细节处理得过于匆忙。好像来人就跟她说了这么一件事,然后她就去了就回来了。像这么重要的细节,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力度感的东西。包括她最后准备去台湾,后来没去,回来的时候就发现王天锡给她的箱子是刘仲瑞的箱子,结果她也把它打开了等等,总觉得这里面的心理应该都呈现为一种非常饱满的状态。人在复杂的心理状态下,他有很多下意识的动作,我为什么这样说?余华谈过这个东西,他谈到《罪与罚》里写到一个杀人犯把房东老太太杀死之后,花了两页写他各种各样的动作,动作就是反映他内心矛盾冲突。各种剧烈的矛盾冲突捏在一起,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叙述的力度。我也想到了茨威格《一个女人的24小时》,C太太曾经疯狂地迷上一个素昧平生的赌徒,为了把赌徒从生死的边缘拉回来,她不惜付出金钱、感情和身体来挽救赌徒,最后换来的却是赌徒对她的侮辱和欺骗。二十四小时后,她终于觉醒了,并迅速离开了赌徒,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他就写了很多细微处,就那种时候,你会感觉到叙述的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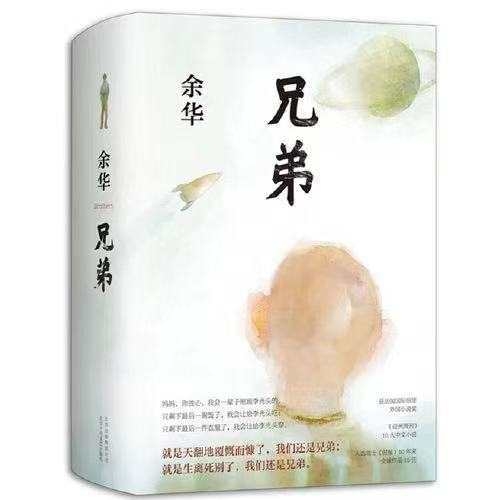
包括余华写《兄弟》,成熟的作家会在细节处爆发出来。我印象很清楚的,有一节,许兰到上海去治病还没回来,她丈夫宋凡平文被打死了,两个孩像孤儿一样,天天等着他老娘回来,天天在长途汽车站等。那个时候就一天一班班车,他们也很好等。长途班车终于等来了,他妈妈拎着礼品包很兴奋站起来,看到她两个儿子正高兴的时候,李光德嘴巴大,说,爸爸没了。她手上那个包就掉下去了,之后,整个一段,余华就是写她的这种状态,眼前一片漆黑然后怎么样,然后过了多少时间以后,然后又怎么样。当她跟两个人说没事了,我们回家的时候,她拎起包,那个包就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的,把她压垮了。她拎这个包的时候,啪地就顺着往下一跪。你会觉得他那个细节有力度。我觉得一般作家来写的话,估计让她两眼一翻白还往地上一躺,或者在地上大哭。要多维地想想人物面对的情况,第一,她治好了病回来,满心期盼一家人过幸福的日子;第二,她丈夫被打死了。第三,当时是一段什么样特殊历史时期,她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什么反应,包括她自己的身体状况、性格特点,这些情况加总在一起,处理起来就非常有力度感。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细节处理可能跟作家的风格有关系,比如说像杨怡芬的小说,我读了那么多,她从来就没有一种剧烈的东西在里面,即使再剧烈的东西,她都可以用平静来对待,这也是一种方式。
一个作家有没有想象能力,有没有对现实日常生活的一个还原能力,就关系到对“细节”的把控程度。你看了很多资料以后,怎样把它的信息还原,是一个挺难的过程。有一个学者就说了,优秀的作家应该是福尔摩斯,发现蛛丝马迹,把它放大成饶有意味的细节,甚至是决定情节发展的东西,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东西。好的细节,它就像尖锐的玻璃划过皮肤,一点声音都没有,但那一定是一针见血,一下子有很深的血痕,忘都忘不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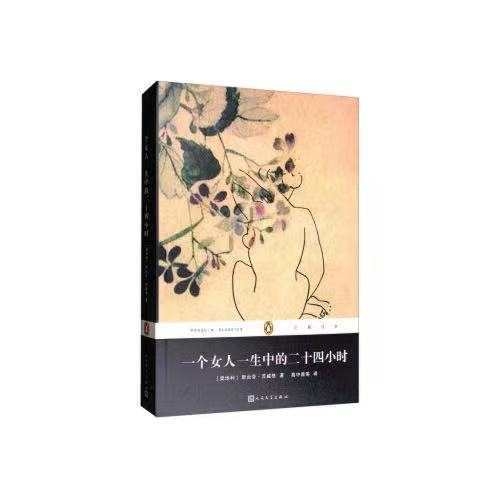
【两性是永恒的一场战争】
现在我们就谈一下人物。《离觞》这个小说肯定是一个群像表达。群像表达的小说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金宇澄的《繁花》。小说肯定少不了写人物,就算写动物,这个动物它一定是带着人物的观念去活动的,因为人不可能知道一条狗一只猫在想什么,动物带着人的心理去行动的,所以还是“人”物。小说里面写人物,必须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来,就是两个字,关系。为什么?因为,人一定是活在关系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肩负很多角色,角色对应关系定位。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儿子,当我身上肩负着我的角色,我对应着一个个很明确的关系。小说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除了要承担着自己的角色之外,还要面对关系。小说的情节无论怎么发展,细节怎么呈现,其实都是在关系当中的。凡关系即伦理,这个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关系的背后是有道德准则,道德准则背后有伦理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很多小说的时候,我们对小说人物关系评判依据是小说背后的伦理。第二个问题,小说的关系里面一定是涉及到人性的微妙,当然了,我们读传奇性小说,会看到它把那种人性的东西搞得很外在,就像早期的历史题材小说里坏人出来脸都是歪的,是吧?仅是一种是和非的冲突,好和坏的冲突,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不是这样的,是复杂的。这个复杂就包含着很多种关系。刚才我觉得杨怡芬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读出这种关系当中的那种复杂性,这是小说要把控的一个度。比如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爱和憎都非常分明,大快人心,那也是一种方法;但现在好的小说一定不再是这么简单地去处理了,他会把很多东西蕴含在里面,让你去品味这些关系。
回到《离觞》上来,这些人物关系其实是一个网络状态,那些关系既不是特别纠结,也不是特别松散。比如说,李丽云早期跟郑景润谈恋爱,感情控制得还是非常好的,后面跟刘仲瑞电光火石那种感情,确实就有点倾城之恋的感觉,蛮惊心动魄的。在秦怡莲和丈夫宋以文、宋安华之间那段关系里,秦怡莲发现了丈夫和宋安华之间的关系,但一点也不说破,其中,我觉得有个细节写得也还是很有力度的。她已经发现了丈夫跟宋安华之间的关系之后,她一点都不说,有天晚上宋以文回家,她又隐约地让他意识到她发现了,所以,宋以文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说了,“有些事情我有点对不起你”,但是她也不理会,而且马上打起小呼噜睡了。在半夜的时候,他梦醒迷糊中伸手一摸,结果摸到了秦怡莲满脸都是泪水。这细节写到这样,那就行了。所有的关系里面的复杂度就在这,不需要说得太过。《离觞》可能缺乏一点力度感的细节,但并不是说没有细节营造,可能这个小说需要安静的阅读,想想人物表面和内部的一些复杂性。
现在我们回到女性层面上来。我是这样看的,人类在两性之间的差异永远在。我比较相信一句话,两性之间是永恒的一场战争,没有办法的。两性之间各个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人类在磕磕绊绊当中去前行的。在微观权力学里面,像福柯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微观层面上有很多关系,比如说一个老板娘,她跟她的男性工人之间一定是不平等的。是不是?假如我是女老师,我跟男同学之间是师生关系,但我是权力的一方。在很多家庭也是这样,尤其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很多家庭里面也是女的说了算。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总体来说,作家面对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男男女女爱恨情仇,怎么去体会人生的况味,怎么去体现对这种人性的复杂性,让读者能够从乱世当中,从离恨别绪当中,甚至连人物自己都把握不住的状况当中,从双方的考角度来考虑对方,思考关系;作家和读者一起体会,很多人性的东西都会打得开。
《离觞》的人物中,我还挺喜欢宋以文的。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那就是中国式的男人,他永远把责任和孩子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对军舰上上下下的责任,对家里的责任,这部下的哪怕他的勤卫兵的责任,当然也对宋安华的责任,他的责任很多。一个人的能力越强,他承担的责任就越多,他的复杂性也会越强。宋以文这个人物我觉得他内心的丰富性已经引出来了,但还不足够丰富,为什么?他要承担的非常复杂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小说我已经把它打得很开了,但相对来说,也还是不够。还有李丽云,如果作为女一号,她也还处在一种简单关系当中,跟父亲的关系,跟闺蜜的关系,两个男人的关系,自己的命运也是这么一个简单状态,她的关系决定了她的人性的丰富度不够,撕不了多少开。倒是秦怡莲这个角色,她毕竟是做了母亲的人,又会经营饭店和米店,她会处理各种社会投资,在她身上,反而能够看得出来中国传统女性的深沉、智慧和韧性,她的丰富性就展开得好。李丽云在《离觞》中也评论过,宋安华的美是在于任性,秦怡莲的美是在坚韧。想想也确实是这样。女性的坚韧和男性的责任,这两个东西如果把它写透,也是符合我们东方的或者中国人的一个审美精神的重要的东西。
在这么一个关系里面,怎么样呈现这个时代,把难以言说的人物生存状态打开,让我们从中能够体会到那种人生、人性、生命的况味和生活的况味,是很重要的。

讲女性独立,比如钱钟书的《围城》,一群留洋女博士,回来了干什么?无非是忙着找有钱人当老公。这都白启蒙了是吧?所以鲁迅说的很正确,娜拉出走以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回来,要么死掉,所以他写了一个《伤逝》,让子君不但回来了,而且死掉了。因为在两性关系当中,在中国的伦理关系当中,女性怎么去独立,我觉得挺难的。有的时候你想得远一点,独立或者自由,会不会是一个蛮空的概念?
刚才讲到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我观察到一个社会学现象,现在县城里面的剩女,比城市的还多。据社会学报告,县城那些男的好一点的老早结婚了,差一点的她也看不上,所以,剩女就剩下了。这怕是闹独立闹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她这样独立很幸福,但是这个东西我也说不清楚。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女性独立问题确实是一个漫长的问题,有的时候,女性主义其实是蛮简单的一个口号,关键问题还是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很多情况都变了,但是变了以后,两性之间还是一样有新的问题。所以,是不是不要去过分强调女性独立的发展?两性之间永远在变动不居的。不是简单的强弱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文明的发展。两性之间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它既是伴随人类发展始终的问题,也是小说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国外有个评论家说,整个19世纪的欧洲小说就是两个字,通奸。他这样说的太过分了,其实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点关系,小说也没必要存在了。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