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三面五地”的大师


李斯特是我好奇的音乐家,我一直觉得他人格层面复杂,内外和深浅交错,并有着大起大落的变化,令人难以把握;这些复杂、交错、变化是人格心理学很好的案例,这些状况可能来自童年、青年期、中年期的心理创伤,以及对这些心理创伤的修复和补偿。
李斯特的人格是甘泪卿、靡菲斯特、浮士德的糅合,是单纯的心灵、黑暗的诱惑、光明的渴望的糅合。甘泪卿是美的象征、单纯的孩子般的心灵、成熟的女性身体,是人健康茂盛的本能;靡菲斯特是诱惑的象征——金钱、权力、虚荣、嫉妒,是人的本性和社会性;浮士德是一位生性怀疑的天才、追寻永恒的艺术家、需要爱的思考者、宽厚的慈善家,是人的精神性。李斯特把这三个角色糅合到一起。
李斯特的人格丰富、分裂、不和谐、不稳定,直到将近60岁才慢慢水落石出。他天真简单,温柔多情,渴望不断有充满才华和热情的美女赞美他、围绕他,给他注入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力和灵感,他和玛丽·达古、卡洛琳·冯·赛因—维特根斯坦的故事是他艺术和生命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是同时代的柏辽兹、19世纪音乐界的毕加索;他自命不凡、傲慢夸张,躁动不安、精力无限,甚至矫揉造作,用超技的演奏获取国王般的荣耀,沉醉于世俗声誉的争夺、荣耀和愉悦当中,挖掘了钢琴音响的所有潜力和交响乐团匹敌,创造了钢琴演奏的不朽传奇,他是同时代钢琴界的帕格尼尼,但他最终也成了听众的奴隶,他们不拜倒他就纠结;他又渴望与世隔绝,远离尘嚣,平息婚姻的挫折、子女的早逝、爱女的婚变、众人诽谤的世俗困苦,他充满了皈依上帝的宗教热情,甚至把这种热情奉献给众多的年轻人和瓦格纳。这三面混杂在一起,浓淡不均地伴随了他的一生。
我们至今不太清楚这三面哪些是他的内在人格或面具人格;哪些是来自他的无意识或意识。他的人格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但一条螺旋线似乎分明,那就是对世俗荣耀的不舍不弃和对独立自由、孤独沉思的执著,它们都发自其内在人格和无意识,纠缠其一生。他的演奏和创作总是在炫技和内心精神世界表达中摇摆、争斗。相对他大量的演奏和作品而言,两者的平衡是稀有的事情。只有在他演奏贝多芬的后期奏鸣曲的时候,只有在他写作自己最严肃的交响乐作品和钢琴作品的时候,如浮士德交响曲、但丁交响曲、交响诗、旅游岁月、b小调钢琴奏鸣曲、匈牙利狂想曲,他才彻底达到了这种平衡。
李斯特五个生活空间也反映出他精神世界复杂性。1823—1835年的巴黎岁月是他和浪漫主义文学和美术结缘,并融入其中的时代,是他浪漫主义革命精神塑造和艺术解构、建构的时代。他大部分的音乐素养,基本全部的文学、哲学修养都来自巴黎。没有这个时代,我们是无法理解他音乐对文学、绘画的偏爱。他从那时就一直认为音乐家在真正开始从事艺术之前,首先要提高文化修养。演奏技术固然重要,但最终要在艺术中被文化所吸纳和融化,否则再好的技术也是生硬的。
1835—1848年是他遨游四方的时代,其中的1839—1847年是他钢琴炫技的辉煌时期;1848年他37岁时常住魏玛,担任公国的宫廷乐长和乐队指挥;1861年他50岁时来到了天主教的中心地意大利罗马,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宗教的倾向日益强烈;1869年他58岁时以神父的身份和宽容一切的心态再度回到魏玛,人格的分裂和不和谐开始化解,他的宽厚仁慈和艺术才华给自己和魏玛再度带来了活力;1875年他64岁时接受了布达佩斯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他把他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身到了教育工作中,且不收学费。从此,他不断地奔波于魏玛、罗马、布达佩斯三地。魏玛是他创作艺术多样性展开的地方,继柏辽兹之往,开瓦格纳之来,提倡既有戏剧性和交响性的标题音乐。罗马是他灵魂安居、皈依神性的地方。布达佩斯是解决他民族归属的地方。
不过,这位一生光艳四射的人最后却在瓦格纳的光芒下,黯然失色。一位极其自负只能容下自己的人,最后见证了另一位更自大的人的梦想实现。瓦格纳巨大的阴影彻底吞没了他。他在孤立和遗忘中,1886年他75岁时在拜罗伊特的朝圣和看望孀居的女儿柯西玛时离世,死前低语着“特里斯坦”的名字。这时刻,他人格中的对立完全化解,只剩下对上帝,也许那时就是对瓦格纳的皈依。
李斯特是一位彻底改变古典主义形式的浪漫主义大师,是市民习气、学院传统的坚决敌对者。他把音乐作为无所不包的艺术,和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相贯通。他是钢琴形式、音响、风格的独创者,他认为肖邦的独创风格过于个性、亲昵,不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风格。
他把钢琴的音响潜能全部挖掘出来,使其成为了“万能乐器”来匹配浪漫主义作曲技巧的发展。他带来了交响乐气场的钢琴曲,十九首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是巅峰之作。
他的演奏生涯充满传奇故事,但在1848年戛然而止,从此专心创作;1875年之后,他只免费培养天才琴手,传承其技法和神韵。他相信技术是必须跨越的,这样才能在艺术中被文化化为无形。
他创立了标题音乐,相应的产品是14首交响诗和两首交响乐,气势宏大,通常用一个主题的复杂变化,表现爱情、紧张和斗争、田园景色、凯旋的赞歌四部曲。他是这种新音乐的坚定支持者,尤其是瓦格纳的音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耀和生命。不过必须指出,在19世纪所有的标题音乐家中,他是唯一能体会到贝多芬在其第六交响曲前写的“情绪的表现多于描绘”这句话意思的人。李斯特明确地规定了标题音乐的标准:文学、绘画的题材必须融化到音乐之中。
他还是一位好写作的评论家,不过今天读来觉得情感过于泛滥、语言过于夸张,言肥意瘦,难以卒读。
李斯特的演奏、作曲、教学无一不是以宏大的规模进行,他和瓦格纳、马勒一道创造了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的传奇和音乐作品的奇迹。(佘江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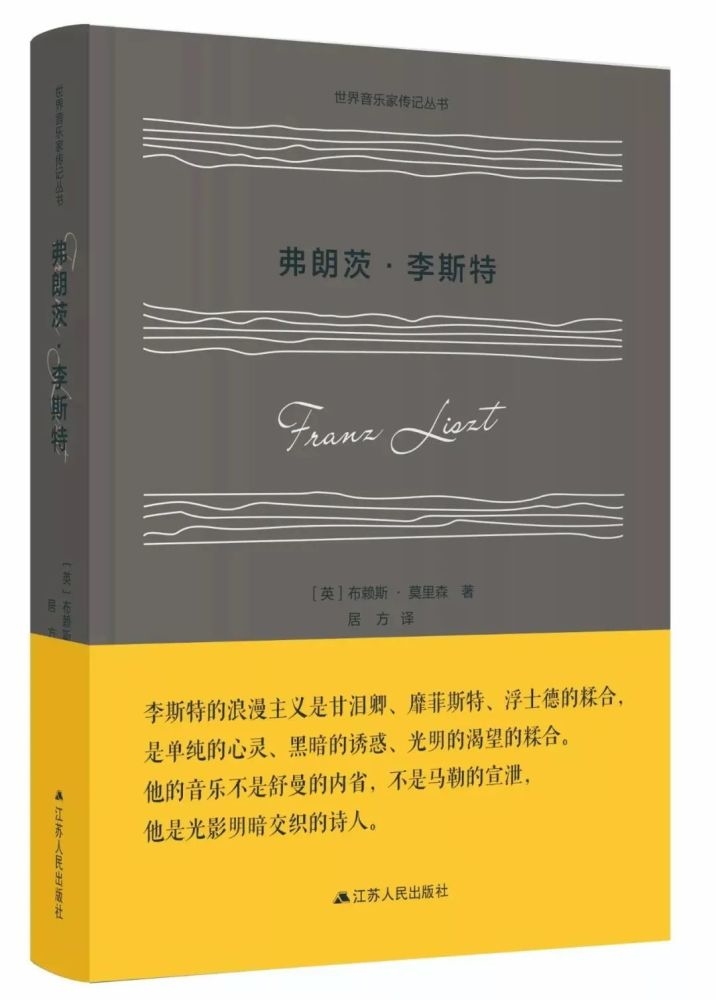
转自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