憧憬着诗与远方的我们,为何越来越难读懂古老的《诗经》?

本期话题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曾经也是许多中国人启学发蒙的必读之书。可是到了当下,这部古老的诗集似乎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为什么天天向往着诗与远方的我们却读不懂《诗经》呢?
上期链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第一篇究竟写的是一种什么鸟

在旧时的中国,《诗经》不但是读书人案头的必备典籍,也是小孩子发蒙的必修课本。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说:
我读《国风》时,虽是减少了历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轻妙,态度的温柔,这种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
——《古史辨自序》

顾先生第一次领略到《诗经》的美,那年他才9岁。时间过去了一个世纪,到今天,别说一个9岁的孩子,就算是专业的《诗经》研究学者都不见得能有这份珍贵的体验。这部曾经家喻户晓的诗集好像和我们的生活有了越来越深的隔阂。为什么我们不再愿意读《诗经》?
我想,《关雎》的第一句其实已经揭示了横亘在我们和《诗经》之间的那堵墙究竟是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今天要提取《关雎》描写的若干细节,然后利用鸟类学的知识去考证雎鸠到底是一种什么鸟,这并非全不可能。
可是这样的研究工作不但因为较高的知识门槛而把普通读者挡在了外面,更糟糕的是,就算待在里面的人,也多半只是运用工具理性去破译一个写作“雎鸠”的文字符号而已,这恰恰远离了《诗经》创作之初最珍贵、最美好的本质。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美就美在淳朴,美在能原汁原味地反映生活。
《关雎》这首诗最初成形的时候,很可能只是某个人看到了一对水鸟,这生活中的寻常事物碰巧勾起了他的浮想联翩。这就好比今天,一个女孩子看见别人窗前的玫瑰花而心生恋爱的渴望一样。于是乎“关关雎鸠”便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了。
可是这种质朴的情感喷涌我们却很难感同身受,因为时过境迁,在作者是寻常口语的“雎鸠”,在我们却不知所谓何物。
清代学者戴震曾说,今天的人读古书,其实跟中国人读外文的感受是相似的——许多人都看得懂一个简单的英语笑话,但真能会心一笑的却寥寥无几。
因为作者是用心在写作,我们是用脑在分析;他写的是带着体温的生活,我们分析的是冷冰冰的文字;他的感性和我们的理性行走在两条互不交集的并行线上。

这样说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无奈地目送《诗经》的背影远去,而再也没办法亲近它了呢?倒也不尽然。《关雎》接下来写道: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关雎》
荇菜是一种长在浅水的野菜,会开出鲜艳的小黄花。诗人说,他追求佳偶的那颗心哪,就像趟着水去摘野菜那样,虽然辛苦,却百计设法,孜孜不倦。
如果我们相信《关雎》是在忠实地描写诗人的生活,那么雎鸠、荇菜的元素拼接在一起,这不就是一幅水乡生活的图景吗?你甚至可以像旧剧《似水年华》那样,想象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枕水而居的乌镇。


《似水年华》写了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文和英,最终一个留在乌镇,另一个回到了台北,虽然他们之间仍有隔山隔水的思念。那《关雎》呢?诗人寤寐以求的那个女孩子,他追到了吗?孔子说: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许多人相信,孔子的意思是说当诗人还没有追到这个女孩儿的时候,他相思难耐,形神憔悴;直至如愿以偿,“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快乐之情又油然而生了。只不过孔子强调,无论是相思的神伤还是耦合的喜悦,都是发乎性情,止乎礼义的。
我对孔子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水平始终怀有最大的敬意,但仅就这首诗而言,我私意以为,其实是可以做第二种理解的。我们不妨把《关雎》中的这三段文字拼接起来看看: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中略)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
这首诗从“参差荇菜”开始,连续出现了三个重章迭唱的段落。单看第一章,“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是一个比喻,比喻诗人追寻佳偶的执着与艰辛,所以下文才能引出“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的诗句。
而在接下来的两个乐章中,这种比喻的结构仍然同第一章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虽然“左右采之”和“左右芼之”做了动词的更换,但“采(即采)”、“芼(即择取)”二字同“流(即“求”的假借字)”的意义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这个局部微调更有可能是为了调剂表达的单调重复而不是改变诗句的中心意思。
可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第一章的“参差荇菜”云云既然是比喻对佳偶的求而不获,第二、第三章还沿用同样的比喻,怎么可能话锋突然一转,就变成比喻两情相悦、琴瑟和鸣了呢?从文本的结构上,我们很难找到这种急剧转变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第二章的“琴瑟友之”和第三章的“钟鼓乐之”很可能不是在描写一个圆满的爱情的结局,而只是对首章求而不获的重唱。
时代无论古今,总有那么一些不幸的人会在不经意间陷入情欲的漩涡,难以自拔,正如《关雎》的作者所感叹的那样,绵长的思念就像一条蛇,在漫漫的夜里折磨得他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而面对这样的困境,侵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君子们和我们今天排遣感情的方式是很不相同的。晚清名士彭玉麟有诗云:
生平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
安得玉人心似铁,始终不负岁寒盟。
——《彭玉麟集》
雪帅一生戎马倥偬,叱咤风云,但感情生活却极不如意。他这辈子终始不渝地深爱着自己的初恋梅姑,纵使阴阳相隔,仍然念兹在兹。可人死毕竟不能复生,梅姑已经零落成泥,雪帅只得移情别恋——不过不是移情在另一个女人,而是移情在梅花的身上,“梅(花)”就是“梅(姑)”。雪帅的咏梅诗,只要多读上几首,我总会产生一种恍惚:他究竟是在咏花呢,还是说人呢?
这是抱道君子表达感情的委婉方式:限于严肃的礼法,他们不愿对情欲作露骨的坦承,而是悄悄地将它寄托在别的雅物上以作消解。
彭玉麟寄情于梅花,《关雎》的作者恐怕是寄情于琴瑟了,当然,琴瑟钟鼓奏响的时候,可能还伴有他歌诗的吟唱。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
(琴瑟)友之,犹乐之也,故《传》连言“友乐之”。《广雅》:“友,亲也。”友为相亲有之称。
——《毛诗传笺通释》
照马瑞辰的解释,友是亲近之意。“琴瑟友之”译作今天的话说,就是“只有在琴声里,我才能亲近你。”当然,诗人笔下的“你”,可能是有确指的,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如果他的所谓佳人之思纯粹是被雎鸠勾起的无的放矢的遐想,那么还原这首诗的创作图景,也不过就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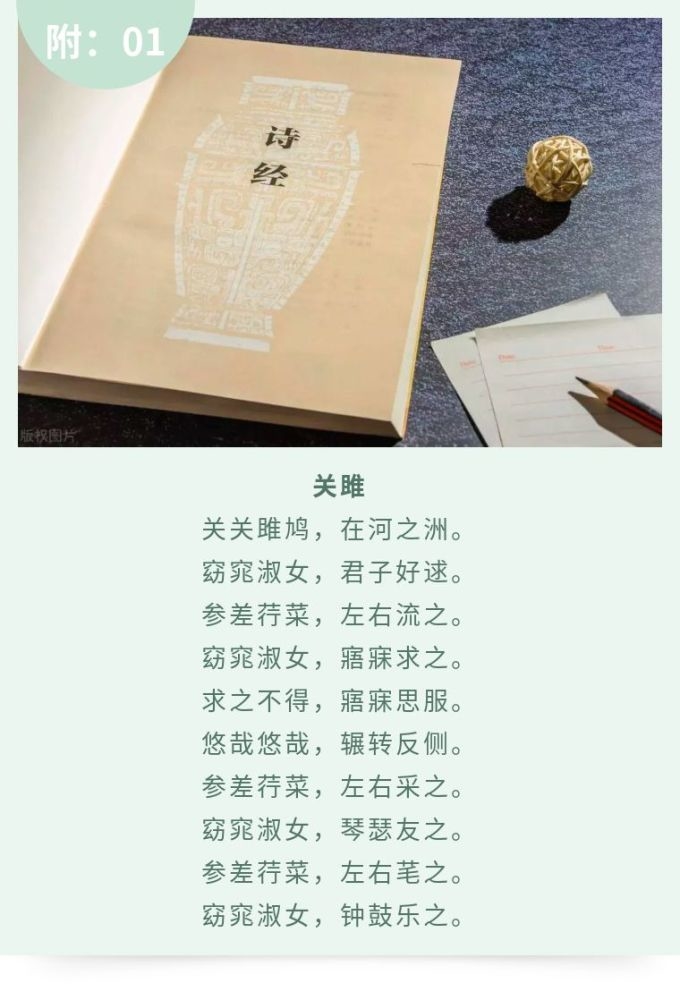
参考文献:
孔颖达《毛诗正义》;
朱熹《诗集传》;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时培建《雎鸠可能是一种什么鸟》。
本文系晋公子原创。已签约维权骑士,对原创版权进行保护,侵权必究!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欢迎分享转发,您的分享转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