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瓦尔泽:精神病患者,或自我流亡的天才作家

撰文|张不退
罗伯特·瓦尔泽本应成为难以计数的被遗忘的庞大作家群中的一个,在嚣嚷中悄悄消失在绝对静默里。如果结果是这样,也许更符合他个人的设想,一种永恒的隐身或匿名状态,远离且彻底远离人群,像一只独自迷失在没有光线的深海里的鱼。

罗伯特·瓦尔泽(1878―1956)瑞士作家,20世纪德语文学的大师,在欧洲同卡夫卡、乔伊斯、穆齐尔等齐名。在世时读者稀少,被《洛杉矶时报》认为是20世纪最被低估的作家。受到卡夫卡、本雅明、黑塞等诸多作家推崇。
1936年起,瓦尔泽的仰慕者卡尔·塞利希(Carl Seelig)定期去黑里绍精神病院看望他,陪他在森林或山间小路中长时间地散步,聊天,累了就坐在小饭馆里喝啤酒。从卡尔的记述中我们知道,瓦尔泽的反应偶尔会有些暴躁,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沉稳、礼貌,对文学有鲜明的个人喜恶和观点,对自然风光有几乎过度的迷恋。后来,卡尔将这些拜访经历写成了《与瓦尔泽一起散步》,促成瓦尔泽作品选集的出版,甚至在德国文学界到处募捐,这让瓦尔泽“避免因交不起饭钱而被驱到贫民救济院去的命运”,也让沉默二十多年的瓦尔泽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尽管那时的“公众”少得可怜——进而扩大其影响力,受到卡内蒂、库切、塞巴尔德、苏珊·桑塔格、彼得·汉德克等人的推崇,与卡夫卡、穆齐尔、乔伊斯一起被视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象征。这个结局,我想,一定会使瓦尔泽感到惊讶,他会睁大他天真、空洞的眼睛,木讷地站在那里,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接着他会沉思一小会儿,不给出任何表示,表情依旧木讷地走开。
1929年初,瓦尔泽在长期经受幻觉和焦虑的困扰后,在姐姐丽莎的劝说下进入伯尔尼的瓦尔道精神病院,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一年是他从柏林回到瑞士家乡后的第十六年,在伯尔尼生活的第八年。此前,也就是刚从柏林回到瑞士时,他住在比尔一家名为“蓝十字”的简陋旅馆里,靠写以瑞士自然风光为素材的小品文为生。那是一段贫苦交加的时期,甚至冬天没钱买煤取暖,但我想瓦尔泽对此不会太在意。不是说瓦尔泽为了献身写作而顾不上现实环境的艰苦,这种说法未免太理想化,而是他早已习惯了贫困。
1878年4月月15日,瓦尔泽生于瑞士比尔一个多子女家庭,是八个孩子中的第七个。他的父亲是个文具店商人,生意不景气,因家里无法承担学费,瓦尔泽只得辍学,十四岁去银行当了学徒。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一直让瓦尔泽感到担心。经过一系列短暂的工作和失败的戏剧演员梦之后,1905年,瓦尔泽前往德国中心柏林,为的也是试图通过写作来摆脱自身的糟糕处境,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罗伯特·瓦尔泽
去柏林之前,他已在苏黎世的报纸上发了不少诗,出版了第一本书《弗利茨·考赫散文集》,这也许给他了一些信心,让他产生幻想,以为自己可以在更大的城市里得到一席之地。在卡尔1936年1月3日记录的谈话中,瓦尔泽说,“一个人永远都不应该拒绝社会。一个人应该生活在社会之中,要么为之奋斗,要么与之斗争。”我们无法知道,离开柏林二十多年后,在先后两个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七年时间后,瓦尔泽说这些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他也许是认真的,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进行自我反思,可事实上,瓦尔泽的柏林时期和其他时期一样,总被远离人群的某种内在力量所牵引,对具有权威性的文学沙龙和所谓“上流文化圈”感到不适,行为有时怪诞可笑,有时放肆乖张。就像塞巴尔德说的,“从一开始,他就与世界以最短暂的方式联系着……就像他完全把物质财产和他的生命分离开来,他和他人保持着遥远的关系。”他从未真正生活在社会中,更没有为之奋斗。而他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他与社会斗争的方式,只是对于生性如此敏感脆弱的瓦尔泽来说,其结果是毁灭性的。在柏林,他的作品得到一些反响,穆齐尔和卡夫卡都喜欢瓦尔泽作品中独特的声调、反讽性和幽默感,但这并不足以阻止他在读者中的失败。在卡尔1936年7月26日的记述中,瓦尔泽告诉卡尔,脱离了文学圈子最终对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影响,而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权威和崇拜让他反感。在另一处他则说:我宁愿不去读我同龄人的作品,只要我仍然被看成一个病人。这样可以保持最适当的距离。
作品不被主流文学圈和读者接受,对瓦尔泽是个巨大的打击,他也因此受伤。据说,当时有一位女演员,买了本瓦尔泽的书寄给他,在上面写了“要写书先学学德语”之类的话。现在,在瓦尔泽已经成为德语文学经典以后,这句话读来带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既让人心酸又让人失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瓦尔泽也在追求——如果他真的追求过的话——被认可的同时,感受到逃离的迫切意愿。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目的就是出现在读者面前,并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至少是不可忽视,可瓦尔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即便在作品中,他也总是偏向于隐藏自己,让自己消弭在性格略显夸张怪异的众多人物之中,留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影子。他在作品中从不彰显自己,更不确立自己,而是出于某种天性中的羞涩而躲藏起来。他也许希望会有人去找到他,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进入让人费解的文字中去寻找一位无名小卒。

罗伯特·瓦尔泽
如果说,认为瓦尔泽的作品只有穆齐尔和卡夫卡这样的伟大作家才可以即刻辨识出来多少有些矫情,那么瓦尔泽作品的独特性已超出当时大部分读者可接受的范围则是无疑的。他的那些带有“逸散”特质的作品也确实难以理解。本雅明评价瓦尔泽的作品时说:“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每句话的唯一目的就是让读者忘记前一句话。”这一概括所依据的文本不多,但极为精准。到目前为止,瓦尔泽的中译本作品少得可怜,2002年出版的一本合集《散步》收录了瓦尔泽的一些散文,以及他最重要的小说《雅考伯·冯·贡腾》,由一个在仆人学校就读的调皮的年轻人的日记组成。随手翻开,看到书中这样一段:
今天小姐哭了,她为什么要哭?在课堂上,她突然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动极了。无论怎么说,我对观察、对仔细听清声音微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必须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这事能美化生活,因为如果不需要观察,也就没有生活了。显而易见,班雅曼塔小姐心里有烦恼,平时,我们的女老师很会控制自己。我必须得有点钱,另外,我把履历写好了,履历内容如下……
从班雅曼塔小姐的哭到对观察的简单论述,再回到小姐的哭,又突然转向钱和履历……句子的逸散性,或者说下一句对上一句的逃逸,让这部作品读起来很怪,像用手去捉全身湿滑的鱼群。这种写作方式也奇异地应对着瓦尔泽的存在状态。在他孤僻、贫困的一生中,瓦尔泽像他的句子一样从人群中离散,包括他的哥哥卡尔和姐姐丽莎。他有一种变得疏离和渺小的本能愿望,如《雅考伯·冯·贡腾》中的主人公的座右铭:变得微不足道,并保持渺小。事实上,瓦尔泽比他笔下的主人公做得更极端,他不仅让自己变得微不足道,而且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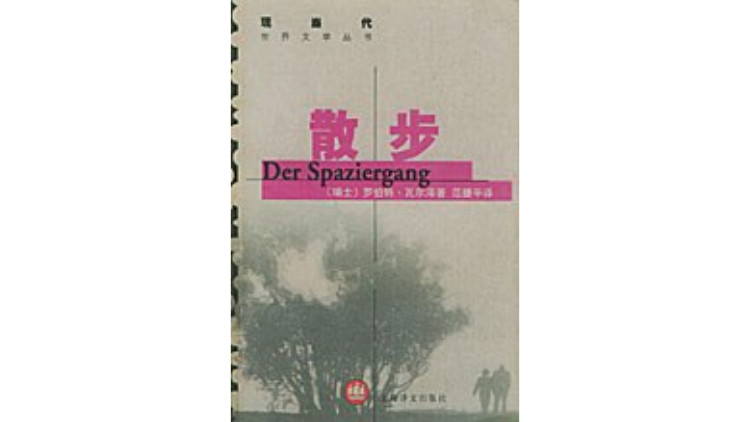
《散步》,作者:(瑞士)罗伯特·瓦尔泽,译者:范捷平,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12月
1933年之后,瓦尔泽彻底放弃了写作。他对卡尔说的一句话经常被引用:“我来这里(精神病院)不是为了写作,而是来发疯的。”这句话可能是真实的,是他让自己变得更加渺小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其中听到一个受伤者玻璃破碎般的声音。在这之前,在瓦尔道精神病院,瓦尔泽曾为了克服对写作的抑制改为用铅笔写作。他俯身在一张张废纸,如车票、日历、卷烟壳上,痴迷地、不知疲倦地滑动铅笔。铅笔写出的文字极微小,后来的研究者只得用放大镜来整理他的“铅笔手稿”,而据“铅笔手稿”整理出的文本成为瓦尔泽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二十世纪德语文学最重要的发现。但1933年以后,随着二战爆发,瓦尔泽似乎觉得在文字中留下一个模糊背影的必要也没有了,于是他停止了写作。他把自己驱逐出文字,抵达了对整个世界的几乎彻底的内心流亡。现在,他能做的,就只有散步了。此时距离他去世还有漫长的二十三年。他是如何度过——尤其在心灵上——这望不到尽头的干枯的时间的?我们不得而知。也许瓦尔泽几十年来一直迷恋的散步真的可以作为一个生命的主要生活方式,而避免陷入真正的疯狂。至于外部的世界,则像火柴的灰烬——据塞巴尔德说,瓦尔泽曾用“灰烬”这一意象形容自己的状态,说“灰烬是一种顺从的、毫无价值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灰烬本身就弥漫着一种认为它不配做任何事的信念”——被一阵微风从他身边吹走了。

罗伯特·瓦尔泽
1956年圣诞节那天,瓦尔泽独自一人去散步,途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几个孩子发现了他的尸体。后来有人叫来警察,给他拍了照。照片上,瓦尔泽躺在厚厚的积雪上,右手搭在身上,左手伸展在另一侧,头也微微歪向左侧,帽子滚落出去,像他故意扔掉的。
作者|张不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