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往事:实存驾到,带着第二性
 2021-03-30
2021-03-30

战后日本文学中,有这样一类小说:如果不看故事中的人名、地名和构成故事背景的特定历史事件,你会以为简直就是西方小说。那种叙述方式、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心理描写,都相当“脱日本”。典型者如村上春树的小说,连情节构成的“佐料”,都是一水儿的鸡尾酒、爵士乐和好莱坞电影,以至于读英文版甚至比读日文版更自然,更舒服——反正都带着黄油味。可若是追根溯源的话,村上其实是后来者。在村上踏上创作道路之前,这种洋范儿的类型小说,便已然确立,并广泛存在了。
文学艺术有时像极了生殖活动,有受体,必有授体。日本现代文学备受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从波德莱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加缪,积蕴深厚。从战前到战后,不止两代作家,写出了一大波存在主义味道十足的文本,从埴谷雄高、野间宏、武田泰淳、堀田善卫,到椎名麟三、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开高健,不一而足。这种影响,在六十年代中期,达到顶点,其标志就是萨特访日。

1966年9月20日,萨特与波伏娃到达庆应义塾三田校区时,学生们举着“反对越南战争”的标语牌迎接(作者提供)
受庆应义塾大学和京都人文书院的联合邀请,1966年9月18日,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与他的终生伴侣、文学和思想的同志西蒙娜·德·波伏娃一道,抵达东京羽田国际机场,开始了为期近一个月的东洋学术访问。日本小报川柳道:“实存驾到,带着第二性”(実存が第二の性を連れてくれる。日文中,存在主义写成“实存主义”,《第二性》是波伏娃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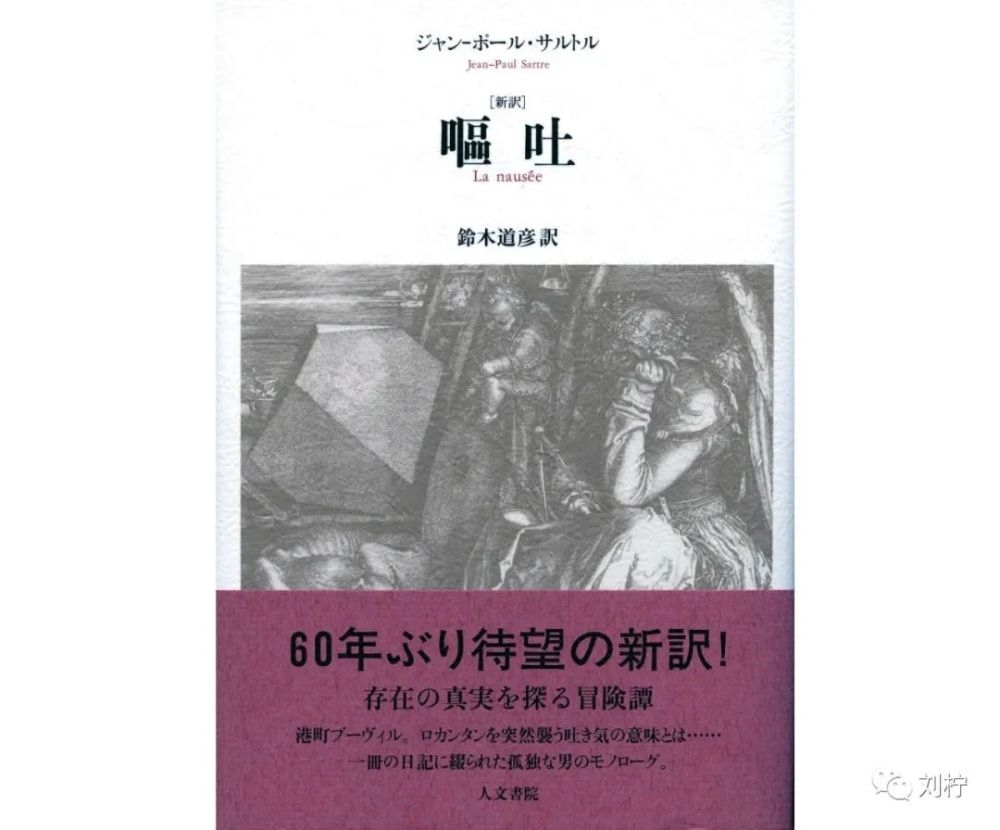
萨特代表作《呕吐》的日译新版
很少有西方思想家像萨特那样,受到日本知识界如此持续的关注与阅读,也许有一比者,只有中国的鲁迅。早在战时的1940年,诗人堀口大学就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译介过萨特的短篇小说《墙》(Le Mur),但反响寥寥。或许正是战争,使日人重新发现了这位法兰西思想家,诸如“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由的”和“选择即代价”“他人即地狱”等思想,在战后初期,“保(守)革(新)”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张力下,引发了强烈共鸣,日本成了世界上阅读萨特的书和萨特研究本最多的国家,知识左翼们甚至觉得自个与巴黎拉丁区的知识人一样,是在实时阅读萨特和存在主义。作家开高健如此回忆,在“终战”不久,最初遭遇萨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呕吐》时的情景:
那本书由一家叫青磁社的出版社付梓,红色的封面。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大脑皮层上还未形成尼古丁和酒精的斑点,每日浸泡在种种书中,在形形色色的语词间穿梭,也是醉了。初读《呕吐》时,我甚至眼瞅着那些活字一个个从白纸上跃起……就这样,《呕吐》成了我不离手的一册,每年都会重温一两遍。

访日中的萨特与波伏娃(作者提供)
只消对日本战后出版史稍加盘点,也难怪知识人会有这种“实时阅读”的“错觉”:1950年,位于京都的自由主义出版重镇人文书院,以预付65万日元的高昂价格,从巴黎的伽利玛出版社引进版权,开始刊行日文版《萨特全集》,译者清一色为一流的法文学者和左翼知识人。煌煌39卷,历时近二十年。先于萨特的祖国法国,日本成为第一个出版萨特全集的国度。据统计,至1966年秋,萨特访日的时点,《萨特全集》共发行了170万部,如加上全集之外,由其它社零散刊行的萨著,总发行量当不下于200万部,堪称战后日本知识界空前绝后的景观。在这种由出版和媒体联手酿造的时代氛围中,萨特伉俪踏上了访日之旅,空气之炙热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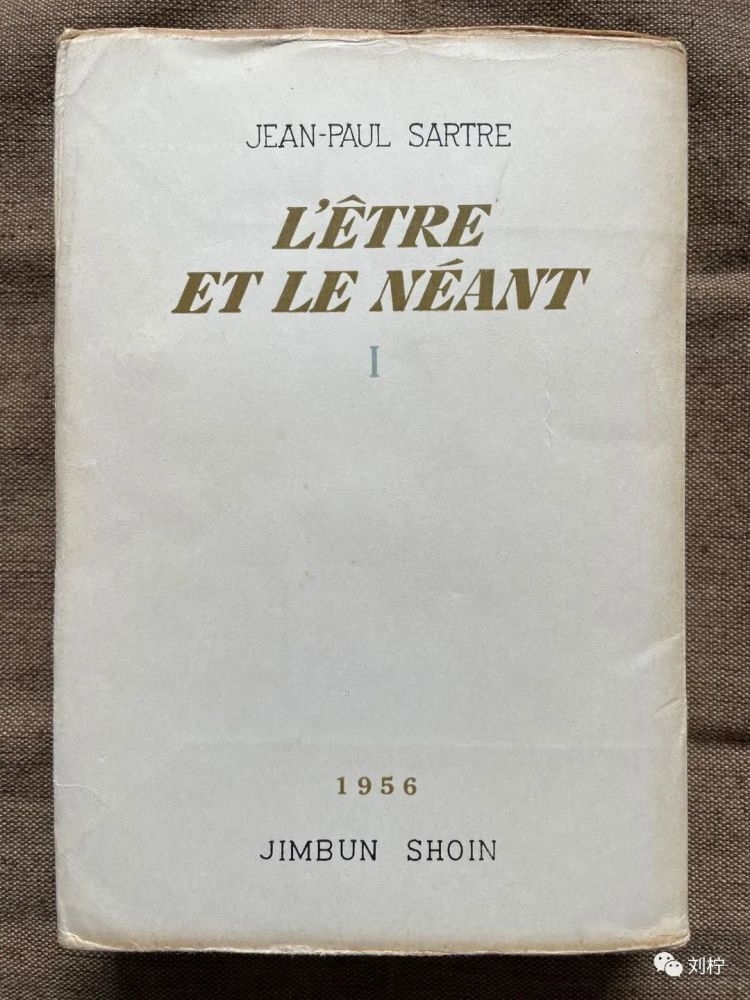
日译版萨特《存在与虚无》(人文书院,1956年版)
二人在东京和京都做了三场公开演讲,与日本思想家、文学家和知识界领袖举办了多场对谈(一对一)、鼎谈(三人谈)和座谈(多人谈),其内容均刊发于1966年10至12月号的主要论坛志上,如《世界》《文艺》和《三田评论》等。萨特与波伏娃多数场合在一起,但也有被“拆散”的时候,波伏娃作为女权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单独受到一些女性团体的邀请,或被安排与女作家对话。可以说,这对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伉俪,在访日期间所有公式、非公式行程,包括种种花絮,统统变成了日本报纸和周刊志的报道,《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自由主义大报和NHK更是不惜派遣名记者,实时追踪报道。

萨特与加藤周一、《呕吐》日译者白井浩司的鼎谈会“西欧与日本”
如10月14日,萨特与曾经留法的思想家加藤周一和法文学者、《呕吐》日译者白井浩司的一场鼎谈,便由NHK做了实况直播。鼎谈开场,白井问萨特对日本的第一印象。萨特直言,自己“几乎感觉不到异国情绪”:“就是说,一般旅行者会与外国形成的那种关系——在并不理解那个国家的情况下回国,然后开始大谈特谈那个国家的神秘性,如此关系,在我的身上,并不成立”;连“最初感到有些不可思,那些用汉字书写的看板” “后来也都消失了似的,我现在觉不出丁点违和感”。接着,他强调了不同国度知识分子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与重要性:
实际上,从访问日本之前,我便有这种预感。因为在接受人文书院和庆应大学的邀请之时,我读了大量日本知识人写的和关于日本知识人的杂志论文,了解到这些知识人所抱有的众多问题与我们法国知识人的问题具有同一性。来到日本之后,立马就清晰化的一点,是我们之间只存在可理解的共通事象。还有那种说日本人的精神与法兰西精神(法esprit)相近,喜欢诙谐什么的,其实都是虚像。与法国一样,日本人生活艰辛,这仍然是一个严峻的国家。可另一方面,我又意识到自己身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与法国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且堆积如山。但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知识人,终归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而且是唯一的世界。在这种认识所生发的相互理解的氛围中,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谈论,可以交流的。

参观广岛核爆遗址的萨特与波伏娃
除了两京(东京和京都),萨特伉俪还访问了箱根、大阪、神户、奈良、志摩、高野山、福冈、别府、长崎和广岛。当时尚未剃度、还是世俗女流作家的濑户内晴美,在她的随笔中写道:“波伏娃真的好美呀。”应该说,濑户内的女性直觉,并非个别。在很多场合,波伏娃风头甚健,举手投足都带着一种女权主义者的落拓不羁,仿佛要颠覆“第二性”似的。而萨特,有时候则显得有些落寞,蔫蔫儿的,透出“存在主义”式的不合群。
日人不承想,萨特居然喜欢活火山。一行乘船在别府上陆后,他说想看阿苏山。到了阿苏山的喷火口,哲学家再次被记者问及“日本印象”。萨特说:“我们遭遇了台风,也见识了歌舞伎和能乐,还有地震。甚至经历了交通事故,没见过的只有共产党和富士山。而富士山早晚会喷火……”所谓“交通事故”,是指10月4日,从大阪道顿堀向神户移动途中,伉俪所乘的出租车与其它车辆发生刮蹭,幸好人车均无碍,有惊无险。彼时,萨特的视力还算好,他还注意到事故发生的瞬间,出租车计价表的指数是“2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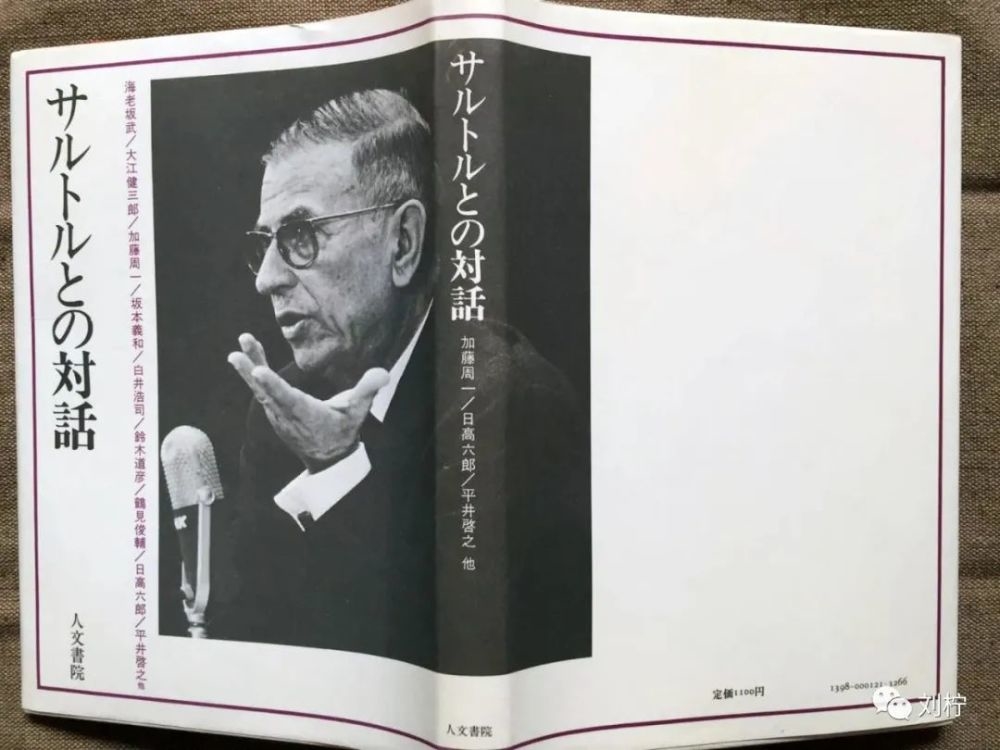
笔者所藏日文版《与萨特的对话》(人文书院,1967年6月初版)
存在主义大师毫不掩饰对谷崎润一郎的偏爱,特别是谷崎的感官系作品。惜乎谷崎已在前一年离世,萨特与松子夫人做了一次对谈。他也拜谒了谷崎墓,但他似乎讨厌墓碑上镌刻的“寂”字。
在法国哲学家中,萨特是出名的美食家。但他不喜欢生鱼刺身,爱吃烤牛肥肠和炸猪排,酷爱日产“老三”(Suntory Old)威士忌,但酒量似乎有限,在京都著名的和式旅馆“俵屋”喝醉过一次。往往结束一天浓密的活动,晚间回到酒店后,还白嘴与“第二性”对酌。“老三”的酒瓶是达摩造型,大肚能容,“实存”哪里晓得厉害?结果,每每夜阑更深,在酒店套房里上演“呕吐”的活剧。

朝吹登水子《与萨特、波伏娃在一起的二十八天·日本》(同朋社,1995年6月初版)
值得一提的是,萨特伉俪访日期间,全程陪同者是以翻译法兰索瓦·萨冈作品而名世的女翻译家朝吹登水子。1995年,她出版了《与萨特、波伏娃在一起的二十八天·日本》一书,风靡一时,早已绝版,书中没少抖“实存”和“第二性”的八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