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书评丨波澜的翻涌和星光的照耀:读马平长篇小说《塞影记》

编者按:四川作家马平的长篇新作《塞影记》,日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小说横跨沧桑巨变一百年,历史和现实交错行进,其浩瀚岁月和苍茫众生,其生命无常和情义无价,无不让人慨叹。

内容简介:《塞影记》中的鸿祯塞,以四川省武胜县的宝箴塞为原型。小说主人公雷高汉八岁逃荒来到那里,被无儿无女的贫贱夫妻收养,半年以后,才仰望到了盘踞山丘之上的鸿祯塞。养父养母相继去世,雷高汉小小年纪典身还债,进入鸿祯塞时已经十九岁。鸿祯塞是一座集防御和居住为一体的庞大建筑,正在扩建,雷高汉和另外两人一起在地下修出了一条暗道。那条暗道未有一次为其主人所用,也没能在危急时刻救出雷高汉心爱的女人,却划开一条血路让他救出一个女婴,为他跌宕出千绪万端的人生。他在一百岁高龄之后,先是住进了和鸿祯塞遥遥相望的一幢乡间别墅,继而身边多出来一个谜一样的漂亮女子,接下来,一个年轻作家闯入他最后的时光。他凭着记忆,也凭着他七十岁才正式自学而陆续写下的文字,和作家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对话,风云再起,波澜重生,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马平一直活跃于文坛,继长篇小说《草房山》《香车》《山谷芬芳》和散文集《我的语文》之后,近年来不断推出《我在夜里说话》《高腔》《我看日出的地方》等中篇小说。《塞影记》已在《作家》杂志今年1期刊出,备受关注。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塞影记》里雷高汉这个弃儿出身的人物,在人生关键时刻都表现出了他的担当精神和仁义情怀,卑微也由此显现出了正大。显而易见,写作这部作品,塑造这个人物,马平在文学观念与小说写法上有突破,有出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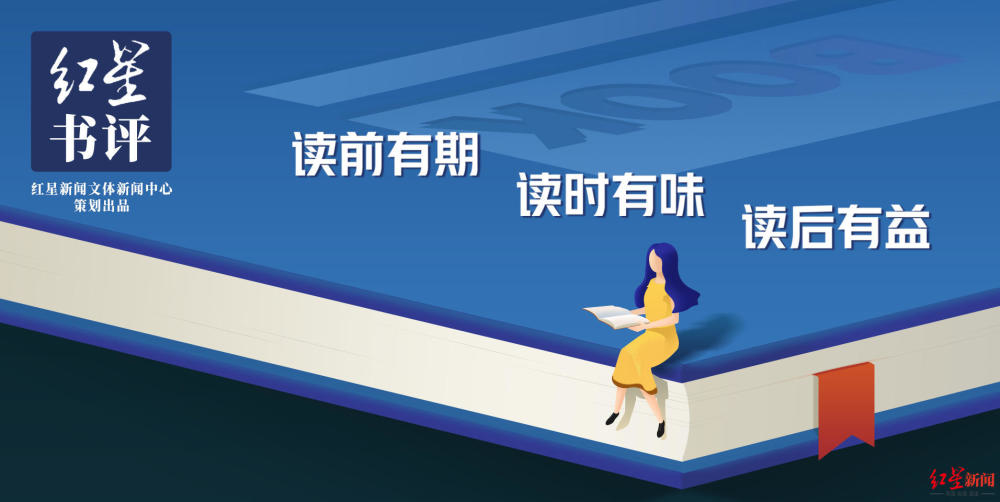
波澜的翻涌和星光的照耀
——读马平长篇小说新作《塞影记》
马平的长篇新作《塞影记》的写作和出版,被作者寄予厚望,植入了他对小说人物、故事情节、语言、结构等传统技巧表达的思考和理想追求,更植入了他对小说“思想化”架构的成熟主张。毫无疑问,《塞影记》在马平的小说大系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是一个高度融合了个人旨趣和读者期待以及艺术主张的长篇力作。
和《草房山》相比,《塞影记》固执地奔着一个“好故事”的目标而去。这个讲述了一位108岁的老人在一百年间的饥饱冷暖、恩怨情仇的故事,读来确乎壮阔波澜,立体丰满,引人入胜,余韵绵长。
人物:雷高汉文学形象的成立
《塞影记》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成功塑造了一个立体丰满的人物:长寿者雷高汉。
在当代文学谱系里,这样一个饱经风霜的苦命幸存者形象,并不稀少。但他的非典型性恰好在于,他并不以“祥林嫂”这样的自怨自艾者存在,也不以“隋不召”(张炜《古船》中的人物)的偏执而苟活,更不以“福贵”这样的被凌辱者而挣扎求存,他虽然卑微,但是勇敢;虽然低贱,但是坚韧;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深明大义;虽然频频遭遇磨难,但是天性乐观积极;他虽然并不睿智,但是懂得大是大非;他有很多残缺,却也呈现出了很多天性的完美;他是被命运捉弄的人,却也常常得到善意的眷顾。
就是这么一个人物,顽强地活了一个世纪。他在他的玻璃房子里,冷静地观察并且安然接受鸿祯塞周边的世界。时间的召唤,在他这里失去了力量。他是山中大木,不才得以终其年。所以,他的长寿,是累积了那些早早离开他的亲人们的福报。一台人生大戏上演,他连戏子都不能算,顶多只能是一个吼班,唱念独白,都轮不到他,掌声都是献给梅云娥这样的主角的,但是,他在鸿祯塞里演出的恩深义重,却比哪一个主角都精彩动人。
雷高汉的身上,有浓厚的旧时代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新社会完成对自我及其观念的改造甚至进步追求。出于一种解密动机的学习认字,是小说里塑造人物形象需要而架设的一个动人的部分,这个拼图式的学习过程,既帮助雷高汉完成了与自身命运关联的秘密探索,也完成了一个进步追求者的人物形象塑造。到县城寻女,则是小说架设的第二个动人的部分,他看着女儿渐行渐远,直到完全退出自己的世界,他没有不甘,也没有抱怨,而是选择沉默接受。
雷高汉命运的传奇性,人物气质的独立性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排他性,使他作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文学形象,得以在当代小说人物形象中脱颖而出,也让他有了跻身当代小说主流人物大系的可能。
情节:展现传奇命运的动人过程
《塞影记》的故事情节在小说中的作用,异常明确,就是要展现雷高汉传奇命运的动人过程。在一百年的生命历程里,他怎样进入鸿祯塞做长工,怎样拯救梅云娥,怎样认字解密,怎样寻找女儿,怎样交代毕生经历。这样的情节展示过程,并不烧脑,也并不复杂萦回,但实在可以称得上是精妙和精彩,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人物天性里缺少离经叛道的部分,所以,所有的情节都在可控的范围内。
但即便是如此,这些情节的一一展开,依然有足够的阅读吸附力,对于阅读体验而言,结果似乎早已经不重要,终点布置的,是雷高汉平淡地离开,连他的外孙女都没能见上一面。在他而言,不曾得到,也就意味着并未失去,这是“最好的告别”。到了此时,读者才会赫然发现,这传奇命运竟然终了,多少有些不舍。情节的使命到此完成,小说家功成身退。
《塞影记》里的情节,并非一水顺流的,也有马平匠心设置的曲折波澜。他需要制造新的条件,使情节得以推动。翠香的死亡和虞婉芬的死亡,都可以视为马平在情节架构上的绝处逢生。因着这两个死亡的特殊性,雷高汉的传奇命运才有了逐渐堆垛起来的高度,并且可以屹立不倒。
但这还在情节的三分之二阶段,雷高汉要如何面对失去爱人、失去女儿的后半生,这似乎也在情节设置的要害之处,但是呢,这尽可以在读者的想象里完成。相较于前半段的传奇,这样的后半生,可以说得上平淡。不是篇幅不允许,而是马平有自己的取舍,或者说小说情节自己帮助自己完成了取舍。所以要插进来“我”对雷高汉的采访,用以缓冲那三分之二情节的急鼓繁弦,同时,也完成剩下三分之一的情节交代。
这是《塞影记》情节设置上的高明之处。雷高汉的命运交代,作为启笔,帮助情节开展,但绝不干涉情节自己的发展方向,纪实与虚构的命运,“我”自有判别。作家听别人讲故事的经历多了,也因此有了丰富的锻炼,一条主线下来,荡气回肠,就这四个字,便知道情节圆满而完美了。

语言:磨心与炼字的双重作用
《塞影记》的语言,主要脱胎于川北乡村,但又融进了时代的主流语境。所以,我们分明能看出作品语言明显的地域属性,但是,似乎又不止于此。“藏头诗”这样的语言设计,多少有些传统意味,这传统里的语言,却是有时代的共通之处。虞婉芬在临死前擦掉包志卓写在岩石上的语言,也是有时代的代表性的,尽管,它从藏头诗变成了标语和口号。
这种语言,经过马平的锤炼,饱含了一种隐喻色彩。擦掉意味着保全,而存在,反昭示着危机。这样看起来,虔心学认字的雷高汉,反不如目不识丁好。正如鸿祯塞并不意味着大大的吉祥一样,“认得几个字”并不代表着可以被保全,这两组反讽,都和语言相关。
为每一个人物匹配合适的语言系统,这是马平在《塞影记》里的又一硬功夫。除了雷高汉这一条主线外,我还特别看重柳鸣凤这样一个人物,她的语言系统里,有村妇的直截了当和俚俗,却也有个性里的智慧和机巧。“她是一家,我是一户。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埋了多少婉致的情绪,也只有雷高汉才懂得,却是柳鸣凤该有的表达。彼一处,罗红玉津津于雷高汉欠她的三个馒头,不是提醒债务的存在,其实更像是提醒她予他的良善,所以“你这辈子,欠我三个馒头了”这样的语言,活化了罗红玉的感情。
语言磨练到这个程度,小说也就充满了活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年雷高汉的语言,结合了长者和智者的双重内涵,马平在一个人物上的多重语言设计,看起来并非是多余,而是随形换势的必以其然。在听到女儿金海棠去世的消息后,雷高汉参禅一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一再被冷落,又一再被关照。”多少生命体会在其中啊。
结构:戏剧意象的精妙串连
熟悉马平作品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他对戏剧尤其是川剧的运用,时常是信手拈来,大增阅读的妙趣。典型的作品如《高腔》,直接用川剧知识来命名。如果把鸿祯塞的百年历史以及人物命运的起伏流变比喻成一台大戏的话,那么,戏剧理论和戏剧知识就无疑是小说中具有桥梁作用的小说结构要件。
《塞影记》里,川剧唱词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实际承担了情节推动和感情展开的关键作用。一部小说在情节上的起承转合,必然因应着结构上的辗转腾挪。川剧的唱白里,隐含着人物命运,而吼班呢,正是小说里堆垛主要人物上到高处的人物基础,或者是时代背景,缺一不可,可又是相互成全。
戏剧承担的结构之外,还承担着思想的隐喻功能。如果说《高腔》的戏剧桥梁作用,是明白晓畅的,那么,在《塞影记》里,戏剧在结构上的桥梁作用,则是暗藏着的。“戏台”在小说的第四章,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而尾章的“暗红皮箱”,不正是小旦角色的梅云娥人生如戏的余音?此外,“玻璃屋”“暗道”“喜鹊窝”和后面诸章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在表现形态之间,无一不在和戏剧发生关系。
最后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问题,《塞影记》的思想深刻性究竟在何处?马平突出了情节的重要性,而摆脱了思想主题的束缚。他把思想主题深藏于心,用一个长寿者的传奇一生,探求人的价值、人活着的意义和灵魂的气息,这正是他迂回主题与呈现思想的高妙之处。至于读者能否寻索得到,这当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传奇大幕落下,鸿祯塞的重重迷影里,的确需要共鸣者,才能懂得舞台上人的无奈、悲凉与孤独。(文/庞惊涛)
编辑 乔雪阳
红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