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芝谈斯皮瓦克:什么是“庶民研究”?
 2021-07-13
2021-07-13

2021年7月13日(今天),“南南论坛”邀请了《庶民能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著名文本的作者、印度思想家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参会,“南南论坛”发起人、岭南大学教授刘健芝应《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之邀撰写本文,梳理斯皮瓦克的思想脉络。读本请参看Global U 微信。

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跟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第一次见面,是在2002年6月香港大学的会议室。当时,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办“公共批判与视觉文化”暑期研讨会,邀请斯皮瓦克主讲。我的本科、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香港大学修读的,硕士、博士论文导师是全球布莱希特学会的会长安冬尼.泰特娄教授(Anthony Tatlow),也在学校里听了很多老师谈后结构主义、新左理论的课,其中包括阿克巴·亚巴斯(Ackbar Abbas)等,都是我非常敬佩的有深厚人文关怀的君子。2002年,我已在岭南大学任教15年,作为亚洲学者交流中心(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 – ARENA)的主席也有9年了。亚巴斯老师跟我说,斯皮瓦克指定要跟我来一场对话,谈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这次对话,开启了我和斯皮瓦克的友谊。对话后,斯皮瓦克建议,我们俩应更深入交流,合写一本书,中、英文同时出版。于是,接下来的半年,我们多次见面讨论、聊天。不幸的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打断了她来香港的安排,也中断了我们的面对面交流,当年没有像现在那么便捷的互联网沟通方式,不知不觉中,出对谈集的计划延宕了。

斯皮瓦克是性情中人,豪爽风趣。我说,来个合影吧;她说,好,向健芝致敬!(从左到右:薛翠、斯皮瓦克、刘健芝,摄于2002年)

亚巴斯(左)主持斯皮瓦克(右)的演讲

斯皮瓦克(左)与刘健芝(右)在研讨会上对话
从1996年开始,我们岭南大学翻译系(后来转去文化研究系)的几位同事,分工编译自己最感兴趣的题目,集结成“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译丛”,繁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出版三集后,我们和汪晖、戴锦华、孙歌等内地学者合作编纂,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简体版。汪晖和许宝强合编《发展的幻象》、戴锦华和陈顺馨合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等,我对另类历史观感兴趣,把相关的书籍找来看,雄心壮志想编几本书,介绍Allen Ginsberg、Michel de Certeau、Walter Benjamin等大师的理论。要编一本选集,必须读大量文章再从中挑选,于我而言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自1996年开始,连续多年,我每年几趟去印度的喀拉拉邦,探索民众科学运动和邦政府推出的人民计划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对印度历史产生很大兴趣,搬回来一大摞书,其中有“庶民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Group)领头人古哈(Ranajit Guha)、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等历史学家编辑的系列,丛书从1982年到2005年,总共出版了12本。因此,我在“文化/社会研究译丛”的第一本(后来没继续出版,所以是唯一一本),就是与许兆麟合作编译的《庶民研究》。我们毫不吝啬时间的投入,有一次,在岭南的课室里,我们几位编辑用了三小时讨论一个名词如何翻译,最后决定,加脚注也没法传达名词的复杂内涵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所以要在每一本书的后面加上关键词解说。在当时的学术界,出版中文书籍不被重视,对评职称完全没好处,但是,对我们来说,那种不计较名利、只为知性研习推介新思潮的日子,是那么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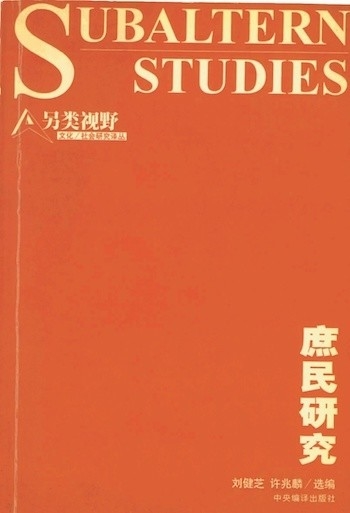
编纂《庶民研究》时,我们收入斯皮瓦克一篇题为“庶民研究——解构历史编纂”的文章。严格来说,斯皮瓦克不属于“庶民研究小组”这个集体。据她说,1981年构思、其后发表题为“庶民能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文章时,没听说“庶民研究小组”;后来接触了,跟古哈合编了《庶民研究精选集》。斯皮瓦克的论述补充了妇女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不是边缘的问题——“庶民研究小组”成员大多数是男性,谈工人、农民,谈封建关系、殖民霸权,却忽略了性别在维持权力结构中的关键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合作后,因为“庶民研究小组”只谈印度、不接受斯皮瓦克对南非问题的讨论,因此停止了合作。
我编译《庶民研究》时,还没认识斯皮瓦克;在香港大学相识后,一见如故,聊理论,也聊身边事,特别是身为女人的处境。斯皮瓦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被聘为“大学教授”(即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仅授予少数十来位杰出教授的名衔)的有色女性教授,至今只有两人,有色人种女性在精英白人父权社会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我们认识时,我与江西贫困山区农村妇女们的交往已有8年,斯皮瓦克在印度偏远农村为贱民妇女办学比我更早8年,我们有共同话题、共同感受。斯皮瓦克说,她在两种极端之间的讲学,是那么惹人热议——她的学生,一边是美国精英学府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另一边是印度山区小学的贱民妇女。她让自己泡在两个极端的环境里。她最讨厌人们恭维她在农村办学,她说,“要恭维就恭维我做得棒的理论工作”,然后会补充上一句,“没几个人这样恭维我!”
“庶民能发声吗?”
斯皮瓦克自1968年开始翻译、最终于1976年出版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的英译本,写了洋洋数万字的译者导言,崭露头角。德里达是阿尔及利亚法裔犹太人,出生在二战前,从内部遭遇西方哲学,批判西方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斯皮瓦克的导言,阐释发扬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斯皮瓦克读本》编者如此概括斯皮瓦克的知识轨迹:“在过去十五年,她的学术生涯循着一条复杂的知识轨迹发展,有对解构理论的深刻的女性主义视角考察,有对资本和国际劳动分工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对帝国主义和殖民话语的批判,有对与民族性、族裔性、移民工身份相关的种族问题的批判,也有对新殖民世界之下的后殖民国家和文化的批判。这样的知识轨迹为斯皮瓦克赢得了纷纭多样的国际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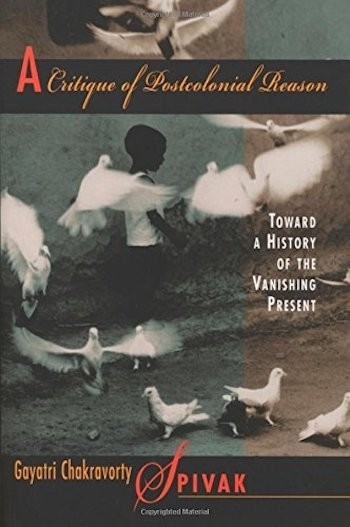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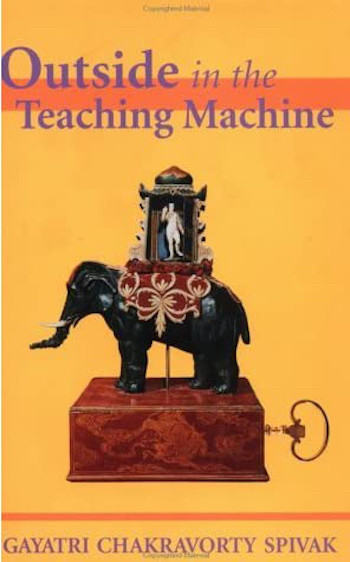
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论、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教育理论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树。可是与她的名字不可分的,是她的文章“庶民能发声吗?” 两个关键词有多个中文翻译版本,subaltern有如下翻译:庶民、底层人、被殖民者、次元、属下、属下阶层、从属者,至于speak,则有发声、言说、说话、发言… 由于这篇文章在后殖民理论中占据经典地位,后来者纷纷以此为题发挥,写了诸如Can the subaltern vote? (庶民能投票吗?) Can the subaltern be felt?(庶民能被感知吗?) Can the subaltern securitize?(庶民能自卫安全吗?)…
我选择翻译为“庶民”。其实,重要的不是名字的选取,而是概念的缘起、使用、语境、文化社会背景,特别是能带来怎么样的批判思考。Subaltern一词,出于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关于社会霸权问题的讨论。“庶民”原来是军队用语,下级、从属者的意思,通过纪律训练必须接受上级指令、服从上级制定的规则标准。葛兰西被囚禁在监狱,所有书信被当局审查,没法直接用上“无产阶级”等政治用语,因此,他笔下的“庶民”,有时候被视为“无产阶级”的代名词,也可被视为标示没有权势的社群。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葛兰西提出霸权的说法,是要探讨霸权关系在文化领域的作用,即数量上是少数的统治集团如何使为其一己谋取利益的价值、标准、世界观,成为多数人认同接受的东西。要理解这个状况便要探讨庶民的历史。
斯皮瓦克和“庶民研究小组”笔下的“庶民”,不简单是 “无产阶级”的扩大或引伸。斯皮瓦克经常强调,没有人可以说“我是庶民”。听起来比较抽象,但是,在她的理论发展轨迹中,“庶民”的界定不在于身份认同的层面,而是指涉排除在任何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之外的状况。“状况”不是人,不是阶级,但处于这种状况的群体,一般是社会边缘群体,因此这些群体可用来标示“庶民性”,犹如风帆之于帆船。在书写庶民历史方面,借助斯皮瓦克的理解,我们可以说“庶民”指的是关系,“庶民”一词总是相对于“精英”(elite)而言的,即“庶民”不是指“现实”中的“实体”,“庶民”没有内在的本质。“庶民”标示的是主导社会的不平等关系,是弱势相对于强势的位置。“庶民”更多是一种视角,从弱势的位置来看支配关系,借此拆解支配关系所依靠的霸权论述。
作为一种视角,借助尼采的诠释,是批判西方哲学传统沿用的关于知识的过于简单的概念,拆解所谓不偏不倚的纯知识的神话,突出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互动关系和张力中形成的,就是说,知识有其历史,求知者在其所置身的世界有欲求、有恐惧,承载着种种印记的身体存活在特定的时空,在我们的“世界”中,因我们有所求、有所拒、有所取向,知识才成为可能。视角是我们认知能力的起点,让我们了解身处的世界所形成的强势的习俗和典章制度,如何在我们身上烙刻痛楚和折磨,如何塑造我们的感情和取向,如何塑造我们的混乱和矛盾,也如何赋与我们和这一切角力的能力。知识生产与其说不偏不倚,不如说是建基在推动知识建构的取向、欲望和与权力的勾结。
如何研究庶民历史?
如果说“庶民”是处在历史边缘的群体,研究庶民历史就不在于增加、丰富“人类”的知识库,不在于补充主流学术权威所认许的历史的遗漏,而在于在过去看似不可能活动的处境中看到可能活动的空间。主流的历史叙述,把一切明确和不明确的东西在因果分明的逻辑关系中赋予位置并组织起来,追求严谨科学性理路清晰的叙述。主流历史叙述的权威,依赖的是“理性—非理性”的二元框架,让人们接受其重“理性”、轻“非理性”的倾向。在这种二元框架中,事实和虚构的分辨不但是“真”和“假”的分辨,同时还是“客观知识”和“主观想象”的分辨,意味着“知识”必须绝对客观,不受任何个人的情感左右。于是,“知识”不可能是一般的经验,因为一般的经验不可能没有情感的作用。于是,守卫和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是一般的人,因为他们必须能够超越一般经验。换句话说,知识分子要通过接受学术、科学的训练,才能有超越“一般人”的成就,即成为“精英”。简言之,科学关于真实与幻象的分辨,跟“精英”和“一般人”在社会上的划分是同构的。和事实与虚构(真/假)紧扣一起的划分,有理性/非理性、正确/不正确、科学/迷信、现代/传统、客观/主观等的划分,这是学科的权威依赖的好/坏标准,“好”的能成为权威的一部份,进而巩固维系权威的机制,“坏”的只能被排斥到边缘位置。
主流历史以其权威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历史,我们研究庶民历史,就是要寻找被忽视和屏蔽的,在我们自身的经历中,看到总是说不清楚、暧昧、不能确定、偶发的感情,如何左右我们的思想行径,进而质疑现代社会的等级关系被合理化的运作逻辑。现代社会科学各门知识不但和种种社会控制的技术关系紧密,其建立更有赖于维系、生产、繁衍权力关系的机制的运作,即社会科学在社会制度、生活组织、以至每个人的“自我”的打造,都有关键的规范作用。福柯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论述,我们编纂的第一本“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译丛”,正是福柯的《学科、知识、权力》。
我们提出了精英—庶民的相对关系,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个相对关系呢?是否通过否定“他者”来确立自己,以“庶民历史”取代“精英历史”?在精英历史书写中,被置于边缘、不被重视的角色,甚或只能在暗处窥见其影子的角色,或只能在落后、非理性、叛乱等指责中占一席位的角色,是否现在反过来成为叙述的中心、成为历史书写的“英雄”,而在精英历史书写中的“英雄”现在则成了“丑角”?
我们要看到,精英和庶民的相对关系是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关系,但不是两个独立实体的对立关系。所谓“精英”或“庶民”是对相对关系中的不同位置的命名,而这些位置又是由多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交错折叠而构造的。不平等的支配关系可概称为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性别关系等。“精英”和“庶民”的相对关系是对相对固定的不平等关系的一种说法。可以说,这样的关系是不同作用(本身也是交错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交错下形成的“果”。因此,“精英”和“庶民”指的是在权力关系中相对固定下来的不同位置,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才是其存在的条件,而不是什么出于自身的本质,也不是假设了本质上对立的二分法。
如帕拉卡殊(Prakash)在 “后殖民评论和印度史学”一文中所说,“庶民”在维持支配关系的论述中被置于边缘隐形的位置,“庶民”被看成没有什么价值和重要性的,能从支配者/精英的位置上说话的论述中留下痕迹也是很勉强的事情。因此,要从刻满了一层又一层支配者/精英的言辞说法的哈哈镜零散的碎片里,重整“庶民”完整的面貌是不可能的。造成庶民历史不可能的哈哈镜碎片,不仅仅是殖民统治精英的问题,也是为独立事业奔走的民族主义精英的问题,殖民统治训练出来的民族主义精英也让造就帝国扩张和殖民统治的现代理性和人文主义铭刻他们的灵魂。
因此,探究庶民历史,与其说是窥探哈哈镜里零散的碎片,不如说,是从哈哈镜的反照中,质问“知识分子”的作用。洛特(David Lloyd)指出,为现代化论述收编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传统等二分法的规范下,只能陷于国家主义贫乏的形式主义中,没有能力认识人民的“同时代性”的创造力,只昧于寻求把人民改进为有现代精神的现代国民。知识分子这种置身于领导者之位置发言的理所当然的想象,正是现代“中心”对“他者”的控制, 而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同一化”。
“现代理性”的权威,其实是通过制度确立的封闭的“自我中心”,把“他者”看待为“中心”不能容纳的颠覆的威胁,是封闭的果,亦是制造、巩固封闭的实践。因此,庶民历史研究不是为了补充权威史学确认的历史——精英历史——的不足,更不是要取代精英历史,而是跟踪精英历史施行删改、压抑、排挤“他者”的痕迹,从中动摇其封闭的二分法确立的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表意和叙述的封闭。要根本动摇主导的逻辑,便不能走重复这样的逻辑的路,所以庶民历史研究不是要寻找、还原庶民的“声音”,让其“声音”在主流历史中占一席位。古哈称众多的“他者”为众多的微弱杂音。即是说,庶民不是一种声音、一种说法;庶民历史研究是要聆听众多微弱的杂音、残留历史的回音。聆听纷杳余音、细察零碎残影,是要让“微弱的”、“纷乱的”释放出动摇支配逻辑的偶合力量,让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关系得以繁衍。
“新庶民”
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斯皮瓦克回顾了她的庶民理论的轨迹,明确地说,庶民所指的,不是特定的人,而是指“subalternity”,可翻译为庶民性、庶民处境、庶民环境,即断绝了边缘群体有社会上升流动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问题不在于庶民能不能发声,而在于庶民不被听到、不被认可,因为由精英主导的主流社会根本不会注意他们、聆听他们,或者视他们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提出庶民性的思考,是她作为教育者,省思自己的角色,一方面努力进行漫长持久的教育,着眼学生的主体性构造,期望他们在非强迫性的条件下有欲望的转移,打开视野。同时针对庶民在全球主导文化的孤立状况,她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工作,打开庶民的想象,突破孤立经验的樊笼,思考庶民作为国家的一部分,面对主流精英的边缘化压制时,能从其现实中抽离,思考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思考参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实践。
如果说“旧庶民”谈的是边缘群体被撂到边上、抛弃在现代“公民/人民”社会的整体之外的话,斯皮瓦克提出,庶民现在面对新的状况,即全球化主导文化的渗透,这反映在庶民(例如原住民)的语言结合了主导文化片言只语,但反过来原住民的文化却不能无条件地与殖民者文化交流,因为在科学的名义下,本地知识/原住民知识,被夺取剽窃,被转化为数据,成为强权的私有财产,成为知识专利产权(例如,跨国药业去亚马逊丛林搜集草药然后申请专利),这是当今不可忽视的状况。主体性塑造的教育,一方面要让全球北方的学生突破科学的逻辑和世界观,看到原住民知识体系的本身价值,同时协助原住民在融入数据洪流之时,能坚持传统知识和经验的完整性。指称“新庶民”,是为了突显边缘群体被自上而下、从中心到边缘的力量所渗透,但渗透力量的流动是单向的。斯皮瓦克强调,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这几十年的演变,进入数码年代,庶民身处的社会关系,只是以不同形式延续精英社会的自我繁衍。
说到底,斯皮瓦克让自己泡在两种极端环境的教学工作里,更好地体会社会的不公、排斥、分化如何延续,而教育者不断要自我警醒的,是颠覆封闭性,转化为开放性。知识分子的“认知失误”(cognitive failure),既是认知的不可能,也是认知的可能性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