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温厚的人格形象长留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史铁生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似乎越来越具有感召力。对于很多读者来说,阅读史铁生就是在亲近人文精神、探寻文学真谛、接受精神洗礼。为何有那么多人一直倾心于阅读史铁生?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一贯坚持自由、真诚、纯粹的心魂写作。

史铁生
“为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把生存这件事想深想透
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自小聪慧。中学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这所优秀学生云集的学校,他依然是佼佼者,不仅文理兼修,还有不少特长。1967年中学毕业,两年后自愿到陕北农村插队。艰苦的插队生活使他少年时曾有过的脊髓病症再度发作。插队期间,两度回京治病,但病情严重,最终瘫痪。此时史铁生刚满21岁。
残疾让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在一家街道工厂做点小工谋生。劳作之余,他开始尝试写作。史铁生多次写道:“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假若不是因为残疾,他大概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尽管写作是无奈的选择,但自1978年初登文坛,史铁生就显露出不俗的创作才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连续两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则是其创作才华的证明。

史铁生早期的创作主要还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也体现出对当时文学潮流的追随。比如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多篇小说,就有当时“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两股文学潮流的深刻烙印。不过,随着写作实践和思考的深入,史铁生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摆脱了一个文学“追逐者”的姿态,慢慢成长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个性、具备自由精神的创造者。在《答自己问》等作品中,史铁生写到,写作对于他,先是为了谋生,接着是为了价值实现,后才看见了生命的荒诞,这时他逐渐领悟到写作的真正意义所在,“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他意识到,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活着,写作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说到底是对生命意义的询问,对生命困境的思索,是要“以寻找以创造去实现人生”。他感叹写作之于他,最终成为一种信仰,也是命运。
史铁生将文学分为三种类型: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严肃文学侧重于社会、政治、阶级层面,通俗文学主要为人的娱乐需要而产生,纯文学则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史铁生认为三种文学各有价值,各有存在的必要。但显然他更看重的是纯文学,而他所坚持的也正是纯文学之路。他将人本的困境看作写作的起点,也是维系写作激情的源泉。在他看来,写作就在于看出了生活的荒诞、生命的困境,而力图“为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只有将生存这件事想深想透了,才能更好地活着,也才能更好地写作。
“心魂”“务虚”“真诚”:思想型写作的关键词
史铁生的写作由对传统的靠近、对生活的探寻,而逐渐走向对自我心魂的追问。他指出:“缺乏对心魂的关注,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艺术,也限制着中国人心魂的伸展。”文学应该超越所谓的“真实”,即表面的现实,或常规的生活,向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思想和精神领域进发。“所有的实际之真,以及所谓的普遍的情感,都不是写作应该止步的地方。”写作不只是对外在世界的观察和描摹,而是“鲜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问路”,是在“写作之夜”“向着心灵的探险”。写作者所要做的是回归心魂的“聆听和跟随”。只有这样,写作才能获得一片无穷无尽的自由天地。
对写作自由的追求,让史铁生不喜欢“文学”这个词,也不接受“文学家”的称谓,而只认为自己是一个写作者。他说:“文学这个词并不美妙,并不恰切,不如是写作,不如是倾诉和倾听……是天地间最自由的一片思绪。”他还说:“说到底,文学(和艺术)是一种自由,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灵魂。”他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一样,应该是自由而真诚的,但在现实中,“文学”二字喻示着规则和标准,因此埋藏下一种危险,即取消个人的自由,限定探索的形式与范围。自由不在,真诚也就难求。史铁生认为,只有给予写作充分的自由,写作才能承担起心魂深处有关生命那么多本源性的主题。

20世纪80年代,史铁生回到陕北探访
“心魂”“务虚”“真诚”,是史铁生文学观念的核心,也是他中后期思想型写作的关键词。他的写作日渐脱离了一般意义上文学创作的陈规陋习。对他来说,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任何方式、文体和语言,都是自然而然,是在回归心魂的“聆听和跟随”中自然流淌而出的。史铁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文体的创新。他认同“形式即内容”“有意味的形式”之说,反对“形式即容器”观念。他认为,文学或艺术的形式,来自人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形式,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就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当感到人与世界融为一体、天人合一,存在乃是主客体的共同参与时,也就看到了“形式即内容”。从1987年的中篇小说《礼拜日》开始,史铁生的绝大部分作品就以超越文体的创作,真正践行了“形式即内容”的理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最为鲜明地体现出了形式上的巨大突破。
史铁生在文体上的超越曾经造成评论的困难,也带来阅读就像猜谜的感受。不过20世纪90年代初,有评论者就由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复调”理论找到了进入史铁生作品的门径。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使命是对存在的探询,叙事只是探询的方式之一,它还可以发动其他的方式。昆德拉的大多数作品都打破了文体的界限,但不管文体多么复杂,都是为了完成同一个主题,即对存在的揭示。史铁生确实同昆德拉很像,既是先锋的,又是传统的。先锋表现在形式的创新,传统则在于他们对形式的共同认知: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创新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存在的主题。同昆德拉一样,史铁生的形式创新并非单纯的形式革命,其意义更是精神层面的。
“爱的弘扬是唯一的拯救之路”:爱成就永恒、消除隔阂、抵抗孤独
21岁突然残疾,恋爱、求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让史铁生饱受歧视之苦。随后几年,疼爱他的奶奶和母亲又相继离世。巨大的不幸,让他坠入深渊。早期的史铁生内心极为痛苦、孤独。以《没有太阳的角落》为代表的早期作品是他这一时期生命的写照。这些作品多以残疾人为主人公,格调低沉。但生命中的亲情、友情与爱情给予他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慰藉,使他不至于在苦难中沉沦。而随着写作、思考的深入,他对生命有了深刻认识。他意识到,他的苦难不是外在社会的或人的原因造成的。他开始跳出个人的苦难看到了普遍的生命困境,由个人的残缺看到了普遍的人性的残缺。史铁生认为,命运的无常、死亡的必然和本质的孤独,是人的三大困境,或者说是生而为人的宿命。早期作品中,史铁生充满了对生命意义的迷惘,生命“好像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存在”。
但在《命若琴弦》《好运设计》等中后期作品中,他则力图在虚无中重建生命的意义。他引导我们将目光从目的、结果转向过程,指出生命的意义不在目的,而在过程,或者说过程就是目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能够创造过程的美好与精彩。他进一步指出,在有限或永恒的生命历程中,唯有爱才是最终的超越之路,唯有爱才能赋予生命以真正的意义。爱成就永恒、消除隔阂、抵抗孤独。在《病隙碎笔》等作品有关信仰的诸多探讨中,史铁生也尤为强调爱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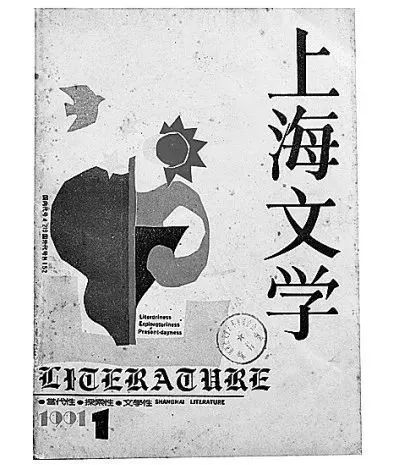
散文《我与地坛》首发于《上海文学》1991年1月号
人们之所以热爱史铁生,除了其深邃的思想,或许更在于其作品中流淌着的温情与爱。《秋天的怀念》《合欢树》里的妈妈、《奶奶的星星》里的奶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贫瘠山沟里白老汉等朴实善良的人们,唤起了读者内心深刻而长久的感动;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对苦难命运的书写中所流露出的平和、温情和透彻,有着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而在以《病隙碎笔》、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为代表的思想型写作中,“爱”也是最重要的主题。
“爱的弘扬是唯一的拯救之路”,写作就是“要在不解的疑难中开出一条善美之路”,这是史铁生最为重要的领悟,也是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八十年代后期,史铁生在家中
“爱”不仅是史铁生贯穿始终的写作主题,而且是其人格的真实底色。他对爱的敏于感受、乐于付出,他的慈悲、超脱的人格形象,让人内心温暖并得到莫大鼓舞。而在生命的终点,深度昏迷的他以超强的毅力维持有力的心跳,只为顺利完成遗体捐赠,则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爱的表达。
史铁生宽厚、温暖的人格形象长留在人们心中,其自由真诚、回归心魂的写作则持续提醒着我们文学精神的标高所在。他的深刻和超越,使得他的写作具有了世界性,也使得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个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存在。写作就是“要在不解的疑难中开出一条善美之路”,如指路明灯,将长久闪耀在文学的上空。
(作者:顾林,系中国社科院文艺学博士,供职于鲁东大学,著有《救赎的可能——走近史铁生》)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1月3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