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秦来来:40年前,路遥来上海看话剧《人生》

2015年,《平凡的世界》的电视剧,由上海的影视公司参与拍摄。2021年11月13、14日,西安话剧院大型原创话剧《路遥》,在上音歌剧院歌剧厅上演。本文是“路遥与上海”的前传——40年以前,上海青年话剧团改编演出了根据路遥小说《人生》创作的同名话剧,而路遥来到上海,亲自观看演出、接受记者采访……

《人生》演出结束后,路遥(前排右4)和编剧程浦林(左4)余伟芳(左1),主演徐幸(右3)李建华(右2)庞敏(左3)等合影
程浦林慧眼识《人生》
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上海的《收获》第三期发表,旋即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上海青年话剧团的编剧程浦林看了《人生》以后,很喜欢。“这部小说提供的基础好,人物新,高加林是当前作品的奇迹,写好了它对青年有很大的作用”,程浦林对我说,“小说的成功在于:作者以真实的笔触展示了一幅当代农村现实主义的生动画面,深刻地刻画了高加林这一个带着悲剧色彩的农村知识青年的性格和命运。开阔了人们对当代青年认识的视野,而且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在广大农村起步是多么艰难,不仅是物质的,更是观念的。”可是当时剧团也为经济效益所累,剧团想演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
“所以我就想个人承担责任。用我个人向剧团贷款的方式排戏,然后走向市场,通过演出向市场要钱。”程浦林说。程浦林向剧团领导立下了“军令状”,贷款人民币三千元,开始了话剧《人生》的起航。
大幕开启了,剧本展现的是浓郁的生活气息,舞美呈现的是醉人的诗情画意,演员塑造的是深刻复杂的角色,结尾是悲怆的耐人寻味的思考……程浦林用上海的方式改编演出的话剧《人生》,深深吸引了来到剧场的观众、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观众。

路遥(前排中)接受媒体采访,后站立者为编导程浦林
演出取得了成功,演出长达四个月,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有不小的积累。“这个戏又感人、又抓人。抓人:引人入胜;感人:发人深省。”著名剧作家杜宣先生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誉,“如果这个戏不卖钱的话,那就值得开会研究,说明话剧成大问题了。”
演出结束后,特地来到上海观剧的路遥也深受感染,他感慨地说:“首先感谢程浦林、余伟芳两位编剧,把小说改成话剧。”我请他谈谈看了戏以后的感受,他说:“这个戏基本上准确反映了原作,最重要的方面都抓住了。北方的生活能在上海青话的戏里反映,我觉得很成功、很感动。因为北方人的生活,南方人很难体现。原小说的人物活现在舞台上,我流了七八次眼泪。”他特别对上海观众的观剧水平之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上海是一座文化很高的城市,观众水平高,反映北方农村的生活能被接受,我感到惊讶!”
主创者精心演《人生》
扮演男主角高加林的是李建华,他说,“我有过类似高加林的生活,我在农村劳动了六年,高中毕业后回家劳动,经历有某些类似。”因此他也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为什么进戏剧学院、进青话呢?我也有追求。我同情高加林对人生的企望、对现代化的企望。他是现代城乡交接地段的一个新人。他的身上有利己主义的东西,但不绝对是个利己主义者。他的新,就新在有高中文化水平,外界文化对他的影响、他有朦朦胧胧的现代化的幻觉。”
李建华的农村生活的经历,为他塑造高加林加分了。路遥给他的评价是,“关于高加林的塑造,因为是上海的演出,观众是南方的,作品做些改动是应该允许的;作为北方人也很感兴趣,没有‘隔’的感觉。演高加林的演员能演到这个程度,我看很不容易了。因为这个人物很复杂。”
巧珍这个人物,不仅是路遥偏爱的,也是演员徐幸精心打造的一个角色。那时的徐幸很年轻,没有演过太多的主角,“有些人担心,不相信我能演好这个戏。”徐幸很实在,并不忌讳这个话题。和李建华一样,她曾经的农村生活的经历,为她塑造巧珍这个人物,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我1971年去南翔插队,接触过很多农村姑娘,她们身上具有中国农村妇女的美德。我看了小说以后就喜欢上了。所以,导演一找我,我就答应了。”
于是,在排练时徐幸穿上布鞋,在道具方面用一块毛巾作为贯穿,帮助她体现人物;在人物造型上,梳一根光光的大辫子,体现角色的单纯、干净、内秀,有时还能用辫子来做戏。

李建华扮演的高加林(右)与徐幸扮演的巧珍
对于巧珍的定位,徐幸认为,如果说黄亚萍是一个小号,明亮;而巧珍则是一把大提琴,深沉。青年人当然喜欢明亮。但是巧珍是一块金子,只是未经雕琢,所以要演得恰如其分,不能太理想化。
路遥的说法是,“我有些伤心,巧珍的命运很不幸,这同她的出身、同土地的联系有关系;她有她自己的不幸,是某种历史、某种客观条件造成。徐幸的表演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的思想。”
被徐幸称作为“明亮小号”的黄亚萍这个角色,是由庞敏扮演的。相较于李建华、徐幸,当时的庞敏可以算是著名演员了。本是上海歌剧院的庞敏,曾经先后参加电影《小字辈》《雾都茫茫》《诱捕》《何处不风流》等影片的拍摄,在观众中颇有人气。对于出演黄亚萍一角,她还是有点担心,因为在银幕上,导演可以‘剪’出气氛,而舞台上要来真格的。”黄亚萍开朗,但不邪,就是在爱情上摔了个跟头,所以语言、动作、形体都不能邪。庞敏较好地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连一向挑剔的路遥,也给庞敏的表演点了赞:“黄亚萍主要怪罪于小说没写好,戏我觉得比小说成功。黄亚萍性格上活泼、淘气、有生气,坚定的个性是她的优点,她对高加林的感情是很真诚的。这人身上有很多缺点,但也有很多优点,她一般的行为和表现,同在关键时刻表现不一样,要区分开来。我觉得她身上的弱点比高加林要好得多了,它只是性格上的东西。演黄亚萍的演员,基本完成了角色的塑造。”
路遥上海谈《人生》
路遥是1983年4月8日晚上在贵州剧场看的话剧《人生》,演出结束后,面对一些记者的采访,他做了回答。后来他又约我4月10日来到青年话剧团,以展开充分的采访。在青话的草坪上,我们做了交谈。

演出结束后,路遥(右)对本文作者谈观后感
路遥说:“当时接到程浦林寄来的剧本稿子,上海演戏能否演出北方的生活,没抱多大的希望。而且更为好笑的是,一直到来上海之前,我还以为这个戏是用上海话来演的。直到前天看了戏以后觉得惊讶。成功当然在于剧本对小说的改造,整个表演是满意的,对徐幸的表演是满意的。”
小说通过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张克南四个青年形象,集中表现了八十年代青年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尽管舞台上出现的只是一个北方的县城、乡村,但它的意义却概括了整整一个时代,揭示了八十年代斑斓缤纷万花筒般的青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和人生思考。
最初,高加林被别人走后门受到侵害,自己民办教师的名额被夺走,他很气愤;后来,他却利用亲戚关系,也走起了后门,还变本加厉起来。他从一个想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变成一个为达目的出卖灵魂不择手段的势利小人,被不良风气裹挟,完全丧失了自我。
路遥感慨地说:“作为艺术作品首先要反映真实的生活,才能达到教育生活;光主题正确、细节虚假,观众不一定接受。要准确地观察生活,反映生活。作者应有思想倾向,但要通过作品自然流露出来。”“我并不回避高加林的缺点,但我是抱着兄长般的感情写他的。青年不可能十全十美,有可能走弯路,但最终会成为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先进青年。这取决于社会的帮助,自己的努力,能克服自己的弱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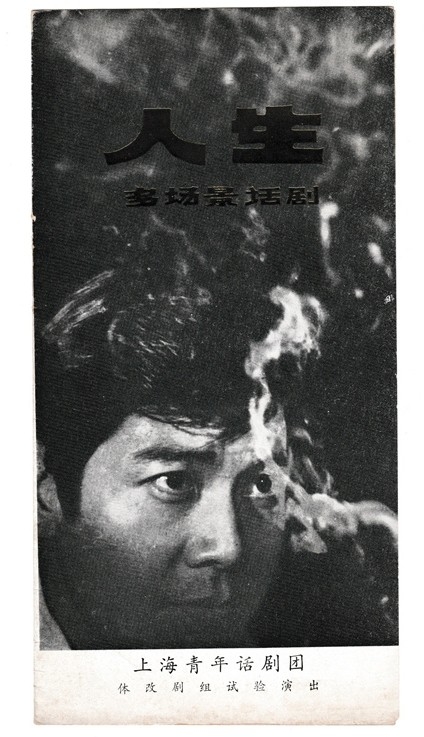
谈到程浦林编导的这个戏,路遥说:“小说中人物内心活动多些,话剧则用对话、行动来表现。本来情绪、心里的东西,体现得还不太准确,假如能更仔细一些就更好。行为上的复杂能看清而主要的复杂要表现在心理上。”
路遥说,“造成高加林悲剧的原因,社会和个人都有。在某种情况上,我就是高加林。陕甘宁地区有几个最贫困的地区,属黄河中游,旧社会大群大群的人外出讨饭;那里连地主也吃不饱。但也出了出类拔萃的,如李自成就是这个地区的人。高加林性格的形成,同地区环境有关。我上辈都是农民,我爷爷还在流浪。解放后革命成功,但贫困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我弟兄姐妹八个,我大妹妹饿死了。土地贫瘠,我七岁时父亲把我送给在外地逃荒的伯父,在那儿我勉强上了小学;高小的时候到了县城,尽管我成绩都是第一,但穷,每月仅十几斤的麦子,因此在心理上有种报复心理。我班上都是干部子弟,由于贫困受到侮辱和歧视,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养成了高加林的性格,要强大。高加林也许会在没有人的时候,躲在一边偷偷地哭,但在有人的场合绝不示弱。”
对于小说发表以后,有些舆论对高加林本人指责颇多,而对社会方面的原因没有充分展开讨论和研究,路遥说,“我认为社会有责任。为此,我愿接受审判,但希望问题不要太尖锐。”
说到这个戏,路遥又说,“我认为音乐很好,特别是高加林走的时候出现的拖拉机的音响效果,是否可以再延伸一些,让人带着想象,很有趣”……(秦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