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格里耶究竟跟你说过什么?” |刘心武


1988年 本文作者在巴黎与罗伯-格里耶合影
1985年10月初的一天,由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那年诺贝尔文学奖评给了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法国一般民众对这个奖项都是感兴趣的,也都对法国作家再次获奖咸与欣喜,但街头巷尾、路边咖啡座、地铁通道里的法国人,多在互相询问:“克洛德·西蒙是谁?”当然很快就有人通过报纸广播电视进行科普:克洛德·西蒙是法国一个小众的文学流派“新小说派”的成员,因之,瑞典学院给他颁奖,也意味着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一种肯定。但瑞典学院一直标榜,他们就是颁给作家个人,与机构、团体、流派无关,他们这一年把奖项颁给克洛德·西蒙,主要是由于他创作了《弗兰德公路》这部长篇小说,“在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描写中,把诗人、画家的丰富想象和对时间作用的深刻认识融为一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学界以及众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文青”,对诺贝尔文学奖十分看重。西蒙获奖三年以后,有个“文青”见到我,还对那年瑞典学院的做法耿耿于怀。原来他对法国“新小说派”“门儿清”,他跟我说,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首先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代表作是《橡皮》,另外还写电影剧本,其中《去年在马利昂巴德》由阿伦·雷乃执导拍成电影以后,反响强烈,瑞典学院就该把诺奖颁给格里耶,没想到却给了西蒙,引得舆论哗然,他也隔空发出嘘声,因为西蒙在“新小说派”里排位,勉强可列第四,排第二、三位的,是娜塔丽·萨洛特和米歇尔·布托。
那是1988年的冬日,那“文青”是亲戚介绍来到我书房的,因为我那时刚从法国回来不久,所以书架上摆了几张在巴黎拍下的照片,他见到其中一张,大惊小怪,口中呐出这样一句:“你居然跟罗伯-格里耶站在一起喝香槟!”我听了觉得刺耳,心中不快,口中不禁也蹦出一句:“是罗伯-格里耶跟我在一起喝香槟!”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他知无意中冒犯了我,忙拿别的话岔开,我也就心平气和,跟他聊些巴黎见闻。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十年,在那个节点上,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外文学交流上,是一种严重的入超状态。拿法国“新小说派”来说,出版他们作品的午夜出版社,在巴黎是一个门脸很小,甚至可以说寒酸,由一道窄梯通往的小阁楼的小出版社,当然这个出版社所出版的作家作品,除上面提到的以罗伯-格里耶为首的四位“新小说派”健将外,还包括另一些流派或流派外的先锋作家,如萨特、波伏瓦、玛格丽特·杜拉斯、罗贝尔·潘热、阿拉贡等等,“麻雀虽小”,岂止是“五脏俱全”,在某些人眼中心中,简直是鸿鹄般伟岸,是一处文学圣地。那“文青”问我,在巴黎是否去过午夜出版社,即使没有上楼,在那挂着小牌牌的门外拍照留念,也不枉巴黎一行啊。我告诉他,法国朋友陪我闲逛时,也曾路过巴黎六区贝尔纳巴里西街,给我指点过午夜出版社的那扇小门,我也看了几眼,却并没有靠近驻足留影的想法。那“文青”又注意到,我书架上有在巴尔扎克故居,巴翁雕像前的留影,他望了望,大概是心中浮出“此叔不可教也”的喟叹,便不再跟我讨论文学。
最近整理旧照片,找出这张与罗伯-格里耶并肩而立喝香槟的旧影,确也感慨万端。不免借此梳理一下自己在多年写作中,在阅读、借鉴外国文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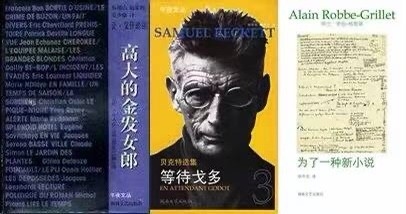
我少年和青年时期,主要是从苏联和俄罗斯文学中汲取营养,深受其熏陶。也从那时国家正式出版的欧美文学译本中获得审美愉悦。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知非常淡薄,那时候的《译文》杂志上也曾有卡夫卡作品的译文,但只是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这种角度来介绍,对其文本创新的意义不作强调,因此像我那样的当年“文青”,也就没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派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门窗大开,这才知道原来像巴尔扎克那样的古典作家,在法国已有罗伯-格里耶那样的“新小说派”作家直言不讳地宣布要予以“打倒”。罗伯-格里耶的论文《未来小说的道路》和《自然·人道主义·悲剧》被视为“新小说派”的理论宣言,他在论文中提出建立新的小说体系,认为这个世界是独立于人之外的事物构成的,人则是处在物质包围之中,因而主张打倒巴尔扎克,反对现实主义的小说传统,要把人和物区分开,要着重物质世界的描写。按照其创作理论写出的作品没有明确的主题,没有连贯的情节,人物没有思想感情,而作者更不表现自己的倾向和感情,只注重客观冷静的描写,取消时空界限。
在1978年底中国正式宣布改革开放以后的短短十年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流派及代表性作家作品,潮水般涌入中国,法国“新小说派”的前四位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全都被飞快地翻译成中文出版,罗伯-格里耶的全部小说,以及他的电影剧本,在中国不但翻译出版全了,还被邀请到中国出席文化活动,作专题演讲。到上世纪末,中国一家省级出版社,干脆和法国午夜出版社签下长期合作合同,编译出版了“午夜文丛”,中方出版社负责人和法国午夜出版社社长兼编辑热罗姆·兰东出任顾问,“午夜文丛”收录的既有老一代的“新小说”作家的作品,也出版了贝克特的选集和杜拉斯的作品,以及新一代作家,如艾什诺兹的《我走了》《格林威治子午线》《高大的金发女郎》,以及图森的《照相机》和《逃跑》等作品,到本世纪的2011年,“午夜文丛”再出发,推出罗伯-格里耶18卷集。12年间共出版图书38种。要感谢国内这些出版人和翻译家,他们在引进新奇的西方文学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我又不得不再感叹:这是惊人的入超。没有哪家法国的出版社,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重视到这种程度,而作为合作一方的法国午夜出版社,有没有出版中国作家作品的法译本呢?据我所知,数目为零,因为这个合作方案从一开始就是单向的。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得知有《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电影作为“资料片”内部放映,我也是想方设法跑去观看,我确实目瞪口呆,电影还可以这样拍?无所谓情节,无所谓人物形象,朦胧,晦涩,断裂的逻辑,牵强的结局……但是也确实学到几招,比如画面上忽然所有背景人物都静止不动,只有一两个前景角色还“活着”;又比如无人的空镜头,太阳明明在那边,按说树呀灯柱呀圆雕呀,阴影应该在这边,却分分明明地展现给观众:有排阴影齐刷刷地反自然,铺向太阳的那边……如果写小说,岂不是也可以这样地将角色与社会剥离?文本结构岂不是也可以反逻辑?总之,他那一路的美学追求,形式创新是最高价值,至于内容么,你可以理解为深奥,也可以完全不予追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形容,仿佛有条叫做西方现代派的狗在后面逼赶,一群中国作家则在前面狂奔。这个比喻刻薄。狂奔的中国作家怕什么?怕落伍,怕过气,怕被边缘化,以至于出局。那个时期,你如果跟人说你还在读巴尔扎克,读狄更斯,读契诃夫,还真有点说不出口,如果你说是正在读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则显得很先进,很在谱。那十年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全译本还没有出现,到如今,加起来,是“二卡四斯”,不会欣赏他们的大著,则难上台盘。
我一度也是努力地去读这些在中国显得格外时髦的作品,当然,我读的都是中文译本。说句大实话,“二卡”还觉得不错,“四斯”就真喜欢不起来。“四斯”中以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在中国影响最大,尤其是他那部《百年孤独》,其开篇: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被众多的中国写作者与阅读者激赏。我虽然也觉得颇为波俏,却怎么也感受不到震撼。难道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还有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不都是“豹头”吗?
若说必须开篇便写到人物心理及动作,则契诃夫早是高手,如《宝贝儿》:
“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勉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老是讨厌地缠住人不放。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就痛快了。”
但是,在三十多年前,我不怎么愿意公开我的阅读欣赏倾向。那倒不是自卑。我骨子里也是蛮自傲的。我跟罗伯-格里耶站在一处品香槟,我对他知之甚多,他对我不是知之甚少,恐怕是一无所知,大概只泛泛地知道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那是一个中法文化交流的酒会,我们被法方人士引到一起,他对我以礼相待,我对他既佩服,又不以为然。佩服,是我知道他乃二战后在法国崛起的“新小说派”的教父,不以为然,是我读了他代表作《橡皮》的中译本,觉得味同嚼蜡,故弄玄虚。他那打倒巴尔扎克的主张,我理解,却绝不赞同。从当年那位“文青”看到我们合影的本能反应,可知我们当时是不对称的,我属于“居然”,格里耶则属于“理所当然”。
从那时起,我不再掩饰自己对“新小说派”等现代派文学的“难以下咽”,也不再以依然热爱巴尔扎克那样的古典作家的老旧作品而觉得难为情。我四次去巴黎,两次特意去参观巴尔扎克故居和雨果故居,一次去参观马拉美故居,两次去参观罗丹博物馆还总觉得没看够,毕加索博物馆则去看了一次便觉饱足。重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开头细致描写屋宇陈设的文字觉得冗长沉闷,因为现在视听文化已非常发达,无需再借助语言描写去感受那个,但查理一出场,人物之鲜活,情节之涟漪荡漾,欧也妮春心的萌动,梳妆匣风波……直到“似乎无事”的结局:“这就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俗之中却不属于世俗,她是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家庭。”掩卷仍“到底意难平”。

雨果故居 图 / 新华社
我觉得自己还算得是一个平和、圆通的人。我习惯中餐,却也偶尔会特意品尝西餐。我不放弃对古典作家作品的欣赏,却也很愿意从先锋新潮文学,从现代派以至后现代派文学中借鉴写作技巧。我自己不喜欢那样的文学追求,不那样去写,但我在编辑岗位上的时候,总是尽量容纳大胆出格的文学尝试。我崇尚中庸之道,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既不保守也不颠覆,既书写反映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面面观与众生相,也力图在人道关怀与人性探索上能融进世界文学之中。
但是到头来,我更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用方块字写作,因此,我更应该从自己民族的老祖宗那里,从方块字原创的经典文本里去汲取营养,也就是从那次跟罗伯-格里耶并肩品香槟酒以后,我致力于细读细品《红楼梦》与《金瓶梅》,并努力在自己以后创作的《四牌楼》《飘窗》《邮轮碎片》等长篇小说中,融进我从中获得的活力。可喜的是,那以后,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大踏步地走向了世界,罗伯-格里耶没有获得的奖项,却有中国作家穿上燕尾服,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到了奖。虽然总体而言,在文学交流上,我们仍处于入超,但既然对这种局面有了清醒认知,那么,更主动、更积极地让世界知道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包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多姿多彩,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
2008年罗伯-格里耶谢世,享年86岁。之前2001年午夜出版社的灵魂人物热罗姆·兰东也去世。一晃,离与罗伯-格里耶合影也已经三十三年了。
那天的酒会是在巴黎协和广场的克里雍大饭店举办的,当时我和罗伯-格里耶经人介绍,站在酒店的露台上,朝协和广场望去,有人为我们翻译,我们有所交谈,1988年冬日到访过我书房的那位人士,也早已不可称为“文青”,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他,近日又与我谋面,他不改对格里耶的崇敬之心,仍觉得即使其人的咳唾,也全属珠玉,便追问步入耄耋之年的我:“那天,格里耶究竟跟你说过什么?”我就告诉他,让我忘不了的是罗伯-格里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奇怪。我在中国比在法国有名。”
2021年6月20日 温榆斋
作者:刘心武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来源:文汇笔会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